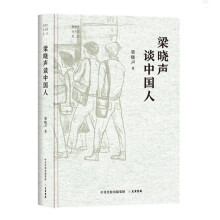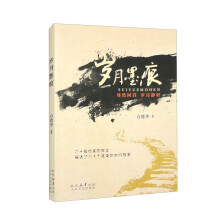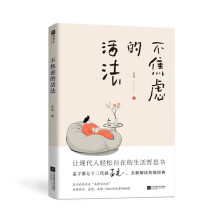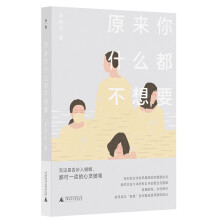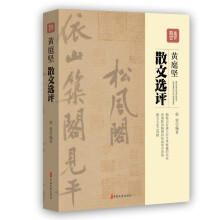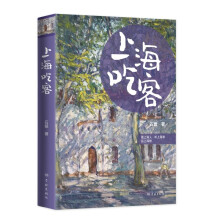潮汐之间
潮水在银色的月光下呼啸着,似乎注满了愤怒,又像是带着狂喜,无法抑制胸中的澎湃,不顾一切地向着海岸奔突。海风站立在潮头,海浪随即高声应和。月亮俯视着、倾听着风与浪的阵阵和鸣,如母亲与摇篮里婴儿的形态。
初秋的曙光,为锦州湾的海域泼洒下淡淡的墨色,海面清冷而透着期冀。几艘渔船开始驶离码头,发动机的声突突响飞几只海鸟。船体身后的每一排浪花, 如雪原上被马蹄卷起的飞雪。
渔家的炊烟徐徐消散,朝阳在海平线上探出半个脸来,海面被霞光浸染一片橘红。海浪由远及近,前后等距排列,如一道道彩色的墙体。一阵涛声消逝,又一阵涛声响起。浪花每次肆意绽放到沙滩,又瞬间被浪拾走。无论海浪的奔涌多么猛烈,海岸始终是不可逾越的终点。它们在一个仿佛不变的位置停下来,然后重复那个无奈的转身。
这像是世间的形态。情欲、繁衍、生长与死亡,日月轮转,周向夏始,生生不恳。
海水漫到礁石深暗的水线,隐没了沙滩上深浅和大小不一的人的足迹。此时,大海如气喘吁吁的大汉,满腹饱胀,且昏昏欲睡。
海潮奔走的行程到了极限,涛声渐渐停歇,阳光跃动在海面,海与天几乎相融一色,海平线变得模糊。在不远处一座岛屿上,光线覆满了葳蕤的草木,岛屿的色调现出淡淡的铅灰,看上去与海面的光泽有些突兀。海鸟的身影不停地闪动,白色的、灰色的,还有黑灰色的,它们既不飞在岛的上空,也不起落在接近水面的位置,却一直在岛的腰部环绕翻飞。
海鸥看来喜欢涨潮后的海面,从岛屿的石缝儿里、从停靠在岸边渔船的甲板下,纷纷而起,先是呜叫着翱翔,然后忽地俯冲下去,待海面溅起一朵朵细碎的水花,便将头向上高昂,用力扇动着翅膀。它们一定是啄到了可口的食物,或是鱼,或是虾,或是人们叫不出名字的生灵。它们完成了一次捕食的规范动作,然后又在离海面最近的天空盘旋开来。大海像是偌大的餐桌,供它们尽享一场盛宴。
也许因为没有狂风和乌云,所以一向戴着“勇士,,光环的海燕,似乎不屑于阳光下缺少险阻的空间。它们往往在涨潮时,嬉戏于涌起的波涛之上,并用犀利无比的目光寻找食物。面对风平浪静的情景,它们却不愿现身,似乎以为这样的空间毫无挑战的乐趣,进而辜负了高尔基先生很早就给予它们的称誉。在不明的近处或远处,它们向海面窥视,却不倾心于海上的美味,对海鸥的贪婪甚为鄙视。也许等到暴风雨到来,它们才会一跃而起,并以一种搏击的姿态,“像黑色的闪电,在高傲地飞翔”。似乎只有这样,它们才配做海燕。
没有谁与谁的承诺能胜过太阳和月亮。它们始终信守那个远古的约定,两颗星体相互轮值,彼此默契,分别在白昼和黑夜里,挥动着带有奇妙引力的指挥棒,为大海的潮汐奏响永无休止的乐章。
但如同世间的万物皆有兴衰,潮水奔跑到最后,终于陷入沉寂,停止了向海岸的冲锋。经过短暂的酝酿,犹如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潮水沿着原来的路线,以不变的节奏开始退却。像是一块魔术布被突然揭开,使沙滩重新袒露出来。沙滩湿润而明亮,鲜活的贝和无生命的光亮的贝壳,零落地镶嵌着,仿佛一袭金色袍子上华丽的点缀。无数个细小的孔穴,该是沙虫出入的洞口。沙蟹没有隐身的妙法,它们的身后总会留下一串弯曲的丸状的沙球。偶尔发现几只海蜇,它们显然是因为体态的笨拙,在海潮回退的时刻晚了一步,便平平整整地贴伏在沙滩上。海藻倒是喜欢漂泊,只是不知道漂泊到沙滩之后,翠绿的生命会很快变得像秋草似的枯黄。
这片海滩又恢复了原有的形貌,现出固有的生命和生命的迹象。
赶海的人渴盼潮退,渴盼刚刚结束的又一轮海潮,把更多的贝类、蟹类和藻类推送到金色的沙滩,以便翻检和拾进筐篮里,然后到附近的海鲜市场出售。他们俯下身后便没有喧闹,手中的铁铲在沙滩上飞快地翻动,唰唰的声音响成一片。P3-5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