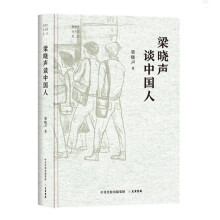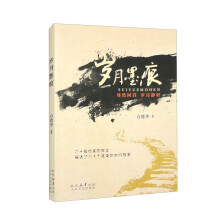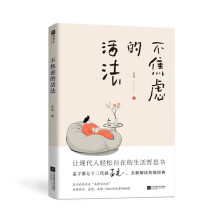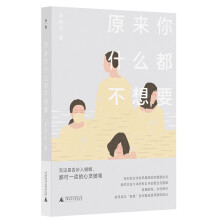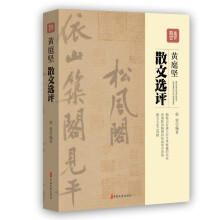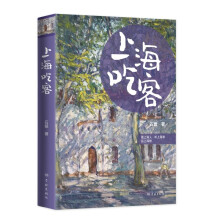《第101朵花开/当代著名作家美文自选集》:
倚窗
这是一座普通小城的一个带状公园。护城小河窄长窄长的,带子一样飘去,公园就把自己抻得瘦长瘦长的,一路厮跟着。
小河里,正结着冰;公园里,土山跟土山上的树们,秃着头。小桥上跟小路上,三三两两胖胖瘦瘦的人在走。小河跟公园共同的远处近处,间或,被长长短短粗粗细细的汽车呼喊声扯一下,空气一阵阵地紧。
随着公园,楼房们也抻拉着自己,一口气下去,把腰身抻得矮长矮长,把窗们拉成了一只只眼。
如果把自己放进这楼房里,倚一扇窗,让窗给自己充当眼睛,一切会是怎样?
土褐色的树们,如静穆的兵俑,从眼底下排开去。闪眼白的冰河,硬生生地,一线喝住,恰若棋盘里的楚河汉界。树秃着的头顶上,偶尔有片苟存的叶,风过时似一枚蝶,静沐里如一颗痣。树下的草,秃眉光眼的,把自己铺成一张旧毯。低洼处,散散落落地,穴着一撮一撮的叶。叶们,不管大小,一律卷紧身,脆着阳光、空气还有风。
树上草间,总是有鸟飞过的。灰黑翅膀的,红白眼圈的,蓝绿腿脚的,长缨短喙的……如果,如果从鸟的眼睛里看,一切会是怎样?
火炬树的炬,红呢,绒绒的,厚呢,里头的籽呢,籽呢?悬铃子,真炫啊,只一点点风儿,它就晃荡个不停,爹着通身的毛刺,顶盔挂甲似的挑战。合欢的豆荚簇,有风跟风唱,没风自己哼,所幸时有裂开的嘴巴,蹦出闪着亮光的豆儿,滚落草里……坡后的老柳,第二个大树卡的皮裂了一块,裂缝处,壅着一堆屑子。坡底枣树的表情僵着,黑魃魃的枝、r上,白底儿黑条儿的八角虫斗儿,闪烁地潜着……树边,一溜儿高的电杆,架着横的电线。楼房拐角戳着巨人似的电讯塔。塔梁中间卧着几只巢,塔尖儿顶上,一架银亮亮的、跟自己身形绝拼的飞机,正拖着扫帚一样的尾巴走。河里的冰上,小孩子们呼扇着胳膊,滑着跑。
地皮上的草也有眼睛的,尤其是这冬天看上去荒得发凉的草。这些秃了眉的光眼,看世界反倒更透亮了。如果,如果,如果从草的眼睛里看,一切又会怎样?
树是草的天。一条被雨水冲出的槐树根,巨蟒一样碾压了一大队草后,又自顾自地扎进土里。法桐枣树们的皮,旧衣似的脱下来,在草却是倾下的一堵墙,塌了的半座山。仰头,桃杏杨柳皮的龟裂,是待浚的沟渠江河,上了弦的箭一样悬在头顶。半大构桃树面皮倒很刮净,平润温善得像石雕佛的面颊。最趣的是长凳边上那桑,两株,麻花一样纠缠得彼此人肉人骨。一群青年男女们走来,双手合十,深深鞠躬,然后把红丝带系上枝条。阳光穿透了丝带,红色耀晕了草的眼……至于大远大远的天,那是树的,似乎不属于草。
一扇窗,一双眼;一双眼,一扇窗。每扇窗里,都是独自的一片天。阳光平等地洒下,但每扇窗不一定捕获到相同的温度。风,步频均等地走过,可是,每双眼捡拾起的脚印,只与自己的心频相应。
倚窗,同样牵了春天的衣袂,却走成了木长草短。倚窗,同样面对雷雨的鞭笞,却飞出了雀低鹄高。
就是倚窗,这个跟呼吸、眨眼、抬手、落脚一样简易的事情,在去年这个时候,对于我来说,却可望难即。病痛把我囚在屋里,把我涣在床上。几十天里,我不想问候日来月去,忘记了屋子还有一扇窗。直到有一天,一道光刺一样切切实实地,扎穿了我土墙皮一样厚的眼睑。把眼睛放出去,对面的墙上,我没有看到欧·亨利那片最后凋落的叶。
几乎高到半天空的楼檐子,是一格一格的水泥架。一格,两格,三格……七格一组,没等到数清一共有多少组,我就牵回了我的眼。它们分明地,把我窗外这片天切割成了混沌的碎片。有鹊一样的东西在上面起落,它们又在我脑子里,影出了《药》里夏家坟上的那只鸦。
终于倚窗了。心志较短了病痛,较长了腿脚。第一眼我发现,我站的十八楼高的窗下,泊着的一排汽车,黑白相间,特像一架钢琴。侧耳,似乎我昕到了自己在弹奏,最简单的和弦伴奏:哆索米索,来拉发拉……抬头,顿悟,这乐曲竟然来自对面水泥的楼檐,1,2,3,4,5,6,7,哆来米发索拉西——原来我脚下是琴,头顶也是琴,而且都硕大无朋。医院广场上,三面旗子在帅帅地飘:红的国旗,白的校旗,蓝的院旗。
还有比倚窗更能让人心魂澄澈的么?
瓦尔登湖面上,梭罗一铲一铲清除了以尺计算的冰雪,开启了一扇妙绝的窗。那不是湖里,而是窗外。倚窗,他的眼里,湖底变成了宁静的客厅,柔和的光沐下去,满是游鱼。游鱼们的鳞,一定片片都闪着金银一样的光。斑斓的光海里,恐怕梭罗自己也变成一条鱼了吧?在大自然的客厅里,他从来不是客人。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