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色蝉
我七岁之前身体健康,过了七岁那年生日,心脏会时不时地痛一下。当时年纪小,不在意,以为跑得累了,又或许是吃的东西不干净。总之难受的时候就找个地方蹲下,过一会儿又能追着同学满操场跑了。
同桌扎蝴蝶结的女孩奚某某,每次看到我痛得捂着肚子蹲在地上,会很狡猾地问我要不要报告老师,我总像做错事一样求她别跟老师说,并且答应之后给她买好吃的。女孩因为我的允诺而感到沾沾自喜,她的喜悦伴随着我身体的疼痛,显得格外突兀。
起初这种痛,一年会发生一两次。刚开始痛的时候会很沮丧,发展到后来,半年中会发生个几次,最后也见怪不怪了,甚至会在痛的时候看着地上的蚂蚁而分神。
十岁那年开学后,有一次,在家吃晚饭的时候心脏突然剧烈地痛了起来,感觉就要昏死过去一样,我强忍着痛蜷在饭桌前的椅子上,不让母亲看出我的痛苦。母亲看我捂着肚子,问我是肚子痛吗?我觉得我该把这种疼痛藏起来,就像藏好一份不及格的考卷一样。
我变得慌乱起来,撒谎说是肚子好像有点痛。于是母亲转身走出厨房给我去客厅倒热水。我痛得身子颤抖了起来,头磕在桌子上,桌子上自己最喜欢吃的菜,在眼里变成了敌人。也就是这一次,我强烈地感受到疼痛、忍受和撒谎的滋味,身体里翻涌着一种不知如何说起的痛楚,这种痛楚正在寻找路途一跃而出。
小学的自然课程里有学到蝉是怎么脱壳的,发育成熟的蝉从泥土中爬出地面,嫩黄,娇小。等到正午时,阳光强烈,幼蝉趴在灌木上,颜色逐渐变黑,等待全黑后展翅飞走。当它背上出现一条黑色的裂缝时,就意味着蜕皮的开始。它抓紧树皮,在一个小时内完成蜕皮羽化。当讲堂上五十多岁的老教师讲到“不完全变态”这个词语的时候,整个班级哄堂大笑,似乎这个词才是最能让人感到兴奋有趣的事情。
那么它这么痛,是为了什么?这是我当时在想的。
父母给我取名曹和平。我父母都是不爱看电影的人,但是他们年轻时在这家和平电影院外碰到,一见钟情,很顺利地,没有任何风波地结合在一起,与他们今后的生活一样,没有多少痛苦,也没有多少快乐。
所以我对这家电影院有着格外的亲近感。这个叫和平影院的电影院对当时的我来说是一座巨大建筑,在记忆里,到处洒满了阳光,两边种着仿佛延伸到云里的梧桐,还有不知名的鲜艳的花,气候永远都是湿热的。坐在长椅上的年轻情侣,互相害羞地拉着对方的手,突然被身旁小孩尖叫打闹的声音吓一跳。尖锐的鸟叫声,在树顶上响起,压低了小孩的声音。继续往前走,穿过红色砖头堆砌的矮墙,推着冷柜车的老人,让人莫名地喜欢。老人经常穿着白色的破T恤,配一条褐色麻布的裤子,上衣的字已经被洗得看不清了。让我惊讶的是,老人每次看见我都会问我,要不要来一根冰棍,我摇摇头,继续往前走。经过一个小花坛,来到一个铁栅栏前,栅栏后就是有着“和平影院”四个大字的巨大建筑。它太大了,你突然发现它的时候,已经站在电影院的门口了。电影院左边墙上的玻璃橱柜里,放着一幅幅电影海报,我饶有兴致地看着,这就是我来电影院的目的之一。很多电影海报就算放的时间太长,我也会不厌其烦地每次都重新看上一遍,我最喜欢看的是《侏罗纪公园》,恐龙锋利的牙齿让我想起我的心脏之痛。
对当时的我来说,能看上一场电影,那就和做上一场美梦一样让人开心。但是一张电影票要十块钱,还是太昂贵了。所以我经常提前挑选自己感兴趣的电影,记住开场和结束的时间,然后坐在电影院门对面小卖部的台阶上。听着电影院里头的声音,碰到外语片的时候,听不懂英文的我只能在电影结束的时候,睁大眼睛仔细地看着每个走出电影院的人。根据他们的脸部表情,来判断这部电影结局是让人开心还是让人难过。
P1-3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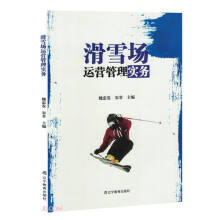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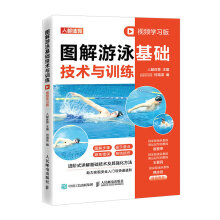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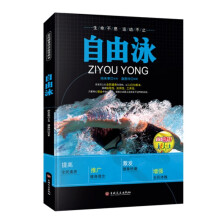


零后小说家的代表之一,他
继承了母亲的文学DNA,他
的天赋异禀、奇思妙想都在
小说这个文体中得到呈现。
——小海
叶迟生于一九八八年,
二零一七年开始写作,他写
作生涯不长,但甫一出手便
显才情。他的一系列中短篇
小说,人物灵动,故事有趣
,富有时代气息。
——朱辉
叶迟小说里的人物充满
犹豫,即使爱也是被动的。
他们就像蜗牛那样伸出触角
,慢慢地迟缓地探索这个世
界,感知自我与世界的关系
。当这种看上去不太坚定的
探索成为某种信念时,它打
开了小说的一个新的空间。
——吴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