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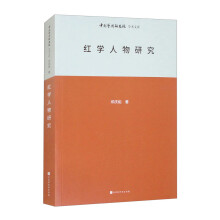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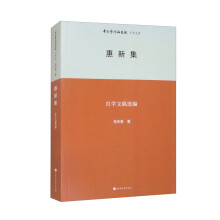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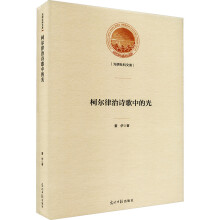

《小说风景》是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张莉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经典篇目如鲁迅《祝福》,郁达夫《过去》,沈从文《萧萧》,萧红的《呼兰河传》,孙犁的《荷花淀》,莫言的《红高粱》,余华的《活着》,铁凝的《笨花》等篇目的重读,既可读到张莉对于这些文本新的理解和观点,又可以串联出中国现当代百年文学发展史,文章通俗晓畅,处处机杼,兼具学术视野和通俗性。阅读,只有在重读中才能产生意义。回顾百年中国故事,进入文学现场,感受新的愉悦,重新去认识我们的文学生活。
《小说风景》源自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张莉在《小说评论》开设 “重读现代中国故事”专栏,发表时曾产生广泛影响。在此书中,张莉用随笔式的写作重读鲁迅的《祝福》,郁达夫的《过去》,沈从文的《萧萧》,萧红的《呼兰河传》,孙犁的《荷花淀》,莫言的《红高粱》,余华的《活着》,铁凝的《永远有多远》……从这些耳熟能详的篇目中,发现那些我们未曾窥见的小说微光;探索作家们的成长革新之路,思考他们如何在百年文学传统的脉络里确立自我风格。通过精微的文本细读,作者带领读者重新认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所关注的核心命题:小说文体的革命、爱情话语的变迁、中国美学风格的构建……呈现百年中国新文学发展的内在美学逻辑。
第一章通往更高级的小说世界
——关于鲁迅《祝福》
《祝福》是鲁迅作品中别具艺术光泽的一篇,也是小说集《彷徨》中的第一篇,写于1924年2月7日。作品发表于1924年3月25日出版的上海《东方杂志》(半月刊)第二十一卷第6号上,后收入《鲁迅全集》第二卷。
《祝福》虽然只有9000字的篇幅,但密度足够大,深具戏剧性和命运冲突感。九十多年来,关于这部作品的解读文章极多,几乎穷尽了各种角度。我希望在前人基础上重读,重新理解这部作品和祥林嫂这个人物。说到底,一部作品的经典性,是在后人的反复阅读和阐释中生长出来的。
祥林嫂的诞生
为什么会有祥林嫂这个人物,是什么触发了小说家写她,或者,什么是《祝福》的情感发动机?这是缠绕《祝福》研究的著名问题。不同研究者给过不同的答案。有一种说法是这个人物来源于现实生活。周作人有一篇文字叫《彷徨衍义》,里面指出过祥林嫂的“真实原型”。在他看来,人物原型来自鲁迅本家远房的伯母,一个因为“失去”儿子变得精神有些失常的女人。“祥林嫂的悲剧是女人的再嫁问题,但其精神失常的原因乃在于阿毛的被狼所吃,也即是失去儿子的悲哀,在这一点上,她们两人可以说是有些相同的。” 这篇文字里讲到关于再嫁女人死后的际遇,以及孩子被狼吃掉的传说等等,可以被理解为鲁迅写作《祝福》的一个背景。很可能,是现实中的某个人物引发了小说家的思考。
最近十年来,研究界有另一种说法,认为祥林嫂这一形象的诞生与佛教故事有关。因为读者发现这篇小说有些地方使用了佛教用语,也有地狱与魂灵的说法,而鲁迅本人,包括周作人,都喜欢读佛教故事。目前看来,第一篇关于这个说法的论文是甘智钢《〈祝福〉故事源考》。这篇论文发现《祝福》的故事与佛经《贤愚因缘经》中的《微妙比丘尼品》的故事有一定联系。“《贤愚因缘经》又称《贤愚经》,是一个影响甚大的通俗佛经,它与鲁迅钟爱的《百喻经》一样,是以故事的形式来宣传佛法,达到传教目的。这部书与鲁迅关系密切。” 甘智钢注意到,《鲁迅日记》1914年7月4日记载,他午后赴琉璃厂买书,其中有《贤愚因缘经》四册,后来他还将它寄给了周作人。《贤愚经》的微妙比丘尼的佛教故事,在中国流传很广,从敦煌莫高窟296号洞里可以看到。故事的主人公是微妙比丘尼。作为女人,微妙的一生不断遭遇不幸,后来佛祖出现,将这个集无数苦难于一身的女人收为了弟子,她后来反复宣讲自己受苦受难的故事,以此为众人说法。
刘禾在《鲁迅生命观中的科学与宗教——从〈造人术〉到〈祝福〉的思想轨迹》里认为,《祝福》这篇作品的出现,与鲁迅想回应当时的一些问题有关。因为鲁迅在当时对人类的灵魂问题有自己的困惑。他把自己的思考与困惑,以及现实生活中的经验,同时也包括阅读佛教作品的经历糅合在了一起,所以才有了这部作品,这一观点深具启发性。以上是关于为什么会有祥林嫂人物形象研究成果的梳理。其实,一个作家为什么要写这部作品,为何会有这样一个人物,原因肯定很复杂。很可能是许多原因许多感慨共同促成。
小说标注的写作时间是1924年2月7日,是那一年阴历的大年初三。在家家户户的爆竹声中,作为小说家的鲁迅想象了一个女佣的发问与死去。这一年离他读《贤愚经》过去了大概有十年,而他也离家很久。小说里所发生的一切,其实是来自一个小说家的创造性想象。他用这9000字的篇幅,构造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他创造了一个女人的鲁镇生存,也写出了她最后的走向毁灭。换句话说,无论脱胎于哪儿,祥林嫂这个人物都是被鲁迅创造出来的,他以不长的篇幅“无中生有”,给予这个女人生命和血肉,正如我们所知道的,九十多年来,这个女人从被创造之初就活着,活到今天。创作者的肉身已然离去,但是祥林嫂活了下来,她有人间气,有生命力,也活过了时间。
一个女人的“逃跑”与“自救”
《祝福》结构工整,开头和结尾呼应。开头是一个辞旧迎新的场景。“旧历的年底毕竟最像年底,村镇上不必说,就在天空中也显出将到新年的气象来。灰白色的沉重的晚云中间时时发出闪光,接着一声钝响,是送灶的爆竹;近处燃放的可就更强烈了,震耳的大音还没有息,空气里已经散满了幽微的火药香。”这是我们常见到的春节景象。这是理解这部小说非常重要的背景。春节的气氛中,小说写到三次下雪,而这三次下雪,与叙述人回忆祥林嫂的一生是相互映衬的。几乎所有研究者都不会忽略“我”与祥林嫂的对话。这是祥林嫂第一次出现在文本中,也是非常经典的片断,那应该视作“我”与祥林嫂的劈面相逢。
那是下午,我到镇的东头访过一个朋友,走出来,就在河边遇见她;而且见她瞪着的眼睛的视线,就知道明明是向我走来的。我这回在鲁镇所见的人们中,改变之大,可以说无过于她的了:五年前的花白的头发,即今已经全白,全不像四十上下的人;脸上瘦削不堪,黄中带黑,而且消尽了先前悲哀的神色,仿佛是木刻似的;只有那眼珠间或一轮,还可以表示她是一个活物。她一手提着竹篮,内中一个破碗,空的;一手拄着一支比她更长的竹竿,下端开了裂:她分明已经纯乎是一个乞丐了。
两个人见面了,怎么开口呢?小说这样写道:
我就站住,豫备她来讨钱。
“你回来了?”她先这样问。
“是的。”
“这正好。你是识字的,又是出门人,见识得多。我正要问你一件事——”她那没有精采的眼睛忽然发光了。
我万料不到她却说出这样的话来,诧异的站着。
“就是——”她走近两步,放低了声音,极秘密似的切切的说,“一个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魂灵的?”
这是小说中的第一个小高潮。一个“纯乎乞丐”的女人问出了一个非常有精神高度的问题:“一个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魂灵的?”她没有得到回答。而就在叙述人也觉得迷惑的时候,更大的震惊感马上到来,祥林嫂死了,并且被鲁四老爷指斥为“谬种”。至于怎么死的,没有人关心也没有人想提起,“怎么死的?——还不是穷死的?”——这句无情的、充满鄙夷的回答,立刻让人觉出祥林嫂命运的卑微。就在这样的回答之后,仿佛在回应“穷死的”这个说法,小说有一段抒情、伤怀但又很美的段落。
冬季日短,又是雪天,夜色早已笼罩了全市镇。人们都在灯下匆忙,但窗外很寂静。雪花落在积得厚厚的雪褥上面,听去似乎瑟瑟有声,使人更加感得沉寂。我独坐在发出黄光的菜油灯下,想,这百无聊赖的祥林嫂,被人们弃在尘芥堆中的,看得厌倦了的陈旧的玩物,先前还将形骸露在尘芥里,从活得有趣的人们看来,恐怕要怪讶她何以还要存在,现在总算被无常打扫得干干净净了。魂灵的有无,我不知道;然而在现世,则无聊生者不生,即使厌见者不见,为人为己,也还都不错。我静听着窗外似乎瑟瑟作响的雪花声,一面想,反而渐渐的舒畅起来。
在悲哀、寂寥又不无反讽的语句里,我们看到了祥林嫂的前史。最初,她是健壮的、有活力的女人。“她不是鲁镇人。有一年的冬初,四叔家里要换女工,做中人的卫老婆子带她进来了,头上扎着白头绳,乌裙,蓝夹袄,月白背心,年纪大约二十六七,脸色青黄,但两颊却还是红的。”但是,她很快被捉回,被逼着远嫁。命运发生逆转,第二次见时,“她仍然头上扎着白头绳,乌裙,蓝夹袄,月白背心,脸色青黄,只是两颊上已经消失了血色,顺着眼,眼角上带些泪痕,眼光也没有先前那样精神了。”而第三次呢,“不但眼睛窈陷下去,连精神也更不济了。而且很胆怯,不独怕暗夜,怕黑影,即使看见人,虽是自己的主人,也总惴惴的,有如在白天出穴游行的小鼠;否则呆坐着,直是一个木偶人。不半年,头发也花白起来了,记性尤其坏,甚而至于常常忘却了去淘米。”生命的活力从祥林嫂身上消失,她越来越苍白,越来越失神,直至变成“行尸走肉”。诸多研究者都论述过祥林嫂的受害和她命运的被动性。但是,她真的只是一个完全被动的承受者吗?
进入文本内部,站在祥林嫂的角度,我们会看到她不是束手就擒的人,她一直在反抗,一直在努力争取命运的自主权。《祝福》中固然可以看到鲁镇环境对祥林嫂的种种压迫,但也要看到一个女人的拼命挣扎,而正是压迫与挣扎所产生的巨大张力和碰撞,小说才有了一种内在的紧张感。
事实上,小说中给出了她第一次出门来做用人是逃出来的信息,这样的“瞒”与“逃”,便是这个女人的反抗。所以,也就是说,小说给出的第一次反抗便是逃离婆家,到鲁四老爷家来打工。这并非想当然,小说中有明确的信息:
新年才过,她从河边淘米回来时,忽而失了色,说刚才远远地看见一个男人在对岸徘徊,很像夫家的堂伯,恐怕是正为寻她而来的。四婶很惊疑,打听底细,她又不说。四叔一知道,就皱一皱眉,道:
“这不好。恐怕她是逃出来的。”
她诚然是逃出来的,不多久,这推想就证实了。
“她诚然是逃出来的”,“逃”到鲁四老爷家是祥林嫂的第一次反抗,而顺着这个路径,我们可以爬梳出小说内部祥林嫂反抗的整个时间线。第一次逃出来,被人捉回去再嫁,于是有了她第二次反抗。
目录
第一章通往更高级的小说世界
——关于鲁迅《祝福》 001
第二章“危险的愉悦”与“罕见的情感”
——关于郁达夫《过去》 034
第三章“女学生过身”与乡下人逻辑
——关于沈从文《萧萧》 064
第四章讲故事者和她的“难以忘却”
——关于萧红《呼兰河传》 090
第五章革命抒情美学风格的诞生
——关于孙犁《荷花淀》 119
第六章旧故事如何长出新枝丫
——关于赵树理《登记》 146
第七章唯一一个报信人
——关于莫言《红高粱》 177
第八章两个“福贵”的文学启示
——关于余华《活着》 202
第九章素朴的与飞扬的
——读铁凝《玫瑰门》《大浴女》
《笨花》 221
第十章三个文艺女性,一场时代爱情
——关于《爱,是不能忘记的》
《一个人的战争》《我爱比尔》 252
第十一章爱情九种
——短篇爱情小说里的爱情 272
除了随笔化、女性主义,张莉的评论有个明显取向:小角度进入。与死背经书的术语党背道而驰,她从最小的切口进入。她的X光眼知道哪里软肋,褒义词都点在穴位上,下刀之处也总是针对病灶,非常实战。有时,张莉会原汁原味地剪贴一小段引文:特别的场景、完整的句子——好多评论家都不这么做了,张莉之所以如此,除了态度上对写作者的尊重和欣赏,还因为那个片段像个横截面,像个内视镜里的影象,让我们得以窥斑见豹。角度新鲜而开放,她以小的手术完成大的疗效。——周晓枫(《有如候鸟》作者)
张莉“试图将我们时代生活中属于文学的‘微火’聚拢,使其成为心灵之光”。当张莉以“偏僻”为诉求,以“微火”为指认,那种我们司空见惯的“野心”与“抱负”便遭到了最为高贵的阻击,文学之事终于还原为一抹人性的光亮,使得我们能够与张莉一起,“看到此时此刻作为人的自我、认清作为人的自身”。——弋舟(《丙申故事集》作者)
即使在信息膨胀的时代,张莉仍以她有态度而不说教、有血有肉而无期刊味的作品确立了一位评论家的尊严,“优秀的作品,应该给一个黑夜中孤独的个人以精神意义上还乡,或者让我们感到作为个人的自己与作为社会的存在之间的血肉关联。”以一种谦逊优美的行文,她做到了。——绿妖(《我在故宫修文物》作者)
在平庸主宰着人们认知结构的时候,批评家的存在方显出自己的意义。张莉清醒地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应该拒绝什么。她常常不满于作家的单性思维,在一些文本里看到了时代的盲区。而这是其思考的出发点。——孙郁(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每个人身上都隐藏着世界的秘密。批评的动力既来自于认识自身,也来自于认识世界。在危机中实现主体性的确立与自我认同,这一体现晚期现代性存在焦虑的知识进路,或许正是以张莉为代表的70后批评家的代际特征。这一代人的暗疾、困境、挣扎与力量大抵来源于此。——孟庆澍(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