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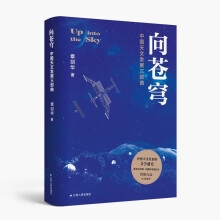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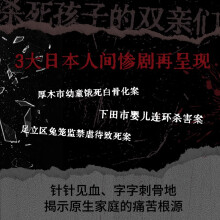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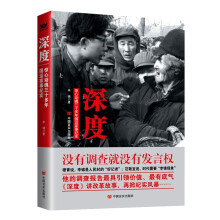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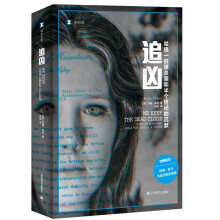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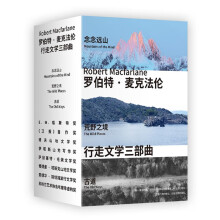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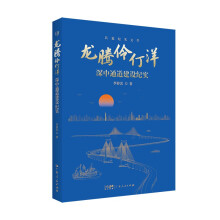
乱世父子
——英千里与英若诚
英千里(1900—1969)和英若诚(1929—2003)父子,翻译都非常出色。大概之前只有伍光建(1867—1943)和伍蠡甫(1900—1992)父子可比。两人志业都不在翻译,英千里志在教学,英若诚则是专攻戏剧,谦称翻译剧本只是顺便为之。但两人偶一为之的翻译,都让人为之惊艳。
英千里出身名门,父亲英敛之(1867—1926)是满洲正红旗人,满姓赫舍里氏;母亲更是出身皇族爱新觉罗氏。英敛之是天主教徒,创办《大公报》和辅仁大学,是清末民初的名教育家。英千里从小留学欧洲,回国后继承父业,主持辅仁大学校务。1949年1月,坐上最后一架“抢救”北平名教授的飞机来台,同机的还有胡适、钱思亮和毛子水。英千里只身来台,1950 年接任台大外文系主任,后来又协助辅仁大学在台复校,是台湾的名师。
英千里身体不佳,教学行政事务繁忙,译作不多。但翻译一出手就知道是不是高手,译作等身也未必就翻得好。下面录一小段英千里 1954 年节译的《孤星血泪》(Great Expectations),是孤儿主角的姐姐谈妥要他去陪伴有钱的老小姐:
我姐姐开口就说:“今天这孩子要不谢天谢地的高兴,那他可就太没有心肠了。”我就立刻在脸上做出一个“谢天谢地”的笑容,但是心中莫名其妙。
我姐姐又说:“我就怕把他给惯坏了。”
彭老伯说:“你放心,不会的。她不是那样的人,她也不会那么糊涂。”
我同姐夫互看了一眼,丈二和尚摸不着头,怎么也猜不着他们所说的“她”是谁。我姐姐看了我们这种神气,说道:“你们两人怎么都像吓傻了呢?难道房子着了火吗?”
我姐夫连忙答道:“没有!没有!可是我刚听说‘她’……‘她’……”
短短几句对话,姐姐的跋扈和主角的配合跃然纸上,的确是高手。姐姐说的那句“我就怕把他给惯坏了”,另一个译本作:
“我希望毕普不会被过度宠爱,”姊姊说道,“但是我总有点担心哩。”
高下立判。可惜英千里大多编译英文教科书,很少翻译文学作品,只留下了三册英汉对照的节译,即《苦海孤雏》《浮华世界》和《孤星血泪》。
再说留在北平的英若诚。1949 年英千里到台湾时,英若诚还是清华外文系的学生,后来考进北京人民剧院,当了话剧演员。“文革”时入狱三年,出狱后重返舞台,后来官拜文化部副部长,还在电影《末代皇帝》中当过男配角。他的译作比父亲的多,几乎都是剧本,曾把老舍的《茶馆》译为英文,还译有美国剧作家阿瑟·米勒(Arthur Miller)的《推销员之死》。1983 年该剧在北京首都剧场上演时,阿瑟·米勒不但亲自导演,还指定由英若诚出演主角威利。
作者亲自导戏,译者主演,真是无法超越的明星组合。英若诚自己是演员出身,翻译的又全都是演出本,经过舞台检验;他译的剧本都是能演的。以他自己的话来说:“语言存在着强烈的时代感和地方感,这种时代感与地方感又往往能赋予语言以生命。(翻译的)难点就在这里。我们必须创造一个有说服力的语言环境,才能把观众带进我们希望的境界。”在翻译《推销员之死》时,“因为原剧用的是 40 年代末纽约的中下层社会的语言,其中不乏土话,因此译文中也大胆地用了不少相应的北京俗语”。请看剧末威利自杀后,威利的儿子比夫批评父亲,朋友帮威利说话的一段对话:
比夫:他错就错在他那些梦想。全部,全部都错了。
查利:可不敢怪罪这个人。你不懂啊,威利一辈子都是个推销员。对推销员来说,生活没有结结实实的根基。他不管拧螺丝,他不能告诉你法律是什么,他也不管开药方。他得一个人出去闯荡,靠的是脸上的笑容和皮鞋擦得倍儿亮。可是只要人们对他没有笑脸了……那就灾难临头了。等到他帽子上再沾上油泥,那就完蛋了。可不敢怪罪这个人。推销员就得靠做梦活着,孩子。干这一行就得这样。
我想演员若能演到这么口语自然的翻译剧本,应该会很高兴吧。对比一下 1951 年香港的予同译的《淘金梦》,这几句话是:
他是一个生存在幻境里,穿漂亮的衣服,笑着周游各地的人。但当人家开始不笑的时候,那可不得了,到了头上出现几点白斑,便宣告完结。没有人会说他不好,一个售货员总会做梦,孩子。这和他的职业一起俱来的。
“他是一个……的人”长达二十六个字,又有“当……的时候”这样的句型,虽然整体表现不算差,但跟演员出身的英若诚一比,就明显有翻译腔了。1992 年杨世彭执导的《推销员之死》在台北戏剧院上演,就是用英若诚的译本,由李立群扮演主角威利。
1949 年父子匆匆一别,竟成永诀。1969 年,英千里在台过世,葬在大直天主教公墓,墓志铭是在大陆就熟识的同事台静农写的,把英若诚兄弟的名字都刻上去落款,其实当时两岸不通,他们连父亲过世都不知道。而且大陆正处于“文革”时期,英若诚入狱,当过图书馆馆长的妈妈被派去扫公厕。“文革”后英若诚重返舞台,但台湾还在戒严,仍无法来台为英千里扫墓。1983 年,英若诚到香港演出《推销员之死》,香港话剧团的名导杨世彭曾在台大受教于英千里,于是到后台探望英若诚,还送给英若诚一本当年英千里批改过的笔记。
1986 年,英若诚出任文化部副部长,有了官职,来台更难。一直到 1993 年,他已卸下官职,才有机会在新象邀请之下随演出团体到台湾,一偿扫墓心愿。
翻译与政治
短命的台湾省编译馆
沾血的译本——春明书店与启明书局
官逼民作伪——《查禁图书目录》
吴明实即无名氏——用假名的始作俑者是美新处
一桶蚵仔,两种翻译
外国的月亮比较圆? ——《蒋介石秘录》也是译本
老蒋棺材中的《荒漠甘泉》,跟市面上卖的不一样
一本真正的伪译——《南海血书》
偷天换日
树大招风—— 揭露几本冒名林语堂的译作
小毕偷看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原来是朱光潜译的?
耿济之在大陆失传的《罪与罚》在台湾重现?—— 空欢喜一场
一代不如一代?台湾的三种《红与黑》
十本《茵梦湖》,六本源头
也算是翻译界的天方夜谭——一个曲折离奇的译本流传史
梁实秋和朱生豪以外的莎剧译者们
生物学家译的《茶花女》,风行台湾半世纪
踏破铁鞋无觅处 ——《鲁宾逊漂流记》奇案
功过难论的远景世界文学全集
高手云集
也是人间悲剧?—— 寻找“钟宪民”
两岸分飞的译坛怨偶——沉樱与梁宗岱
两个逃避婚姻的天主教译者——苏雪林和张秀亚
译者比作者还重要——殷海光的《到奴役之路》
乱世父子——英千里与英若诚
父债子难还——郁达夫和郁飞的《瞬息京华》
惺惺相惜的隔海知音——《柴可夫斯基书简集》
译者与白色恐怖
译者血案——冯作民的故事
大师对面不相识——巴金译作在台湾
生平不详的童话译者许达年原来落脚台湾
十三国童话皆格林——丰子恺和丰华瞻父子
追忆再启
人生的开始——《摇篮曲》
本来无话,何劳翻译?——《小亨利》
三十几年还没落幕的大戏——《千面女郎》
隐形的日译者——黄得时的《小公子》和《小公主》
飞吧!海鸥岳纳珊!
麦帅的儿子怎么了?——《麦帅为子祈祷文》
少见的西班牙语漫画——《娃娃看天下——玛法达的世界》
冷战时期的政论常青树——包可华专栏
西洋罗曼史的兴衰——《米兰夫人》与《彭庄新娘》
流行歌曲——《爱你在心口难开》
娱韵绕梁
闽南语的《伊索寓言》
台湾最早的莎士比亚故事——《丹麦太子》
安徒生的第一个中文译本在日据台湾——《某侯好衣》
亚森·罗苹在高雄犯案!——《黄金假面》
《拾穗》最香艳的一本蕾丝边译作——《女营韵事》
好大的面子!皇帝来写序——《紫禁城的黄昏》
七种译本全成禁书——《毕业生》
爱是不做害羞的事?——《爱的真谛》与《圣经》翻译
假作真时真亦假——华生的遗作《最后的难题》?
中皮洋骨的“神探狄仁杰”
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