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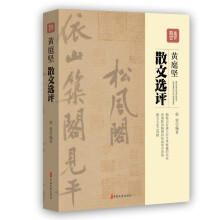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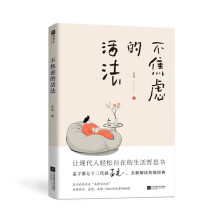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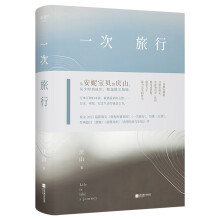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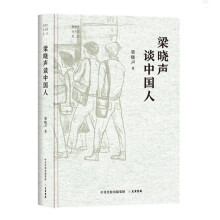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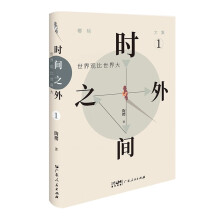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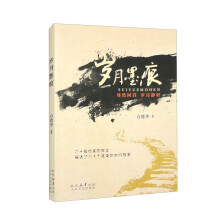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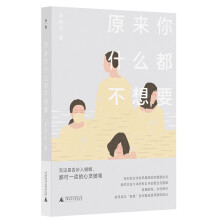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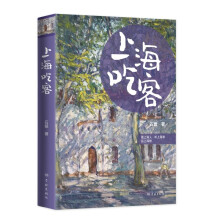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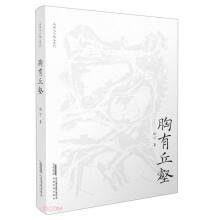
索尔·贝娄
197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获奖理由:“因其作品中结合了对人类的理解和对当代文化的精妙分析”
《巴黎评论》访谈发表时间:1966年
索尔•贝娄
(Saul Bellow,1915—2005)
美国小说家,迄今唯一一位三获长篇小说类美国国家图书奖的作家。其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奥吉•马奇历险记》(1953)、《雨王亨德森》(1959)、《赫索格》(1964)、《赛姆勒先生的行星》(1970)、《洪堡的礼物)(1975)、《院长的十二月》(1982)等。
2005年4月病逝于美国马萨诸塞州。
索尔•贝娄访谈
杨向荣/译
对贝娄的访谈陆续“发生”了若干个星期。从一九六五年五月的一些探索性讨论开始,夏天时又被搁置,实际完成已在九、十月间。期间进行了两次录音访谈,总共花了大约一个半小时,但这只是贝娄先生为这次访谈所做努力的一小部分。在五个多星期的时间里,我们做了一系列面谈,专门对原始材料进行了极为仔细的修改。从一开始他就意识到自己将为这次访谈付出不小的努力,所以对于开始做这次访谈,他其实是非常不情愿的。然而一旦做出决定,他就无所顾忌地将大量时间投入这项工作——在为期整整五周的时间里,每天多达两个小时,每周至少有两次,经常是三次,投入其中。正如他所说,这次访谈已经成为某种机会,他可以借此说出一些重要却未曾被说出的东西。
某些类型的问题在早期的讨论中即被排除在外。贝娄先生对那些他认为对自己作品所做的无聊或愚蠢的批评没有兴趣回应。他引用了一句犹太谚语,说一个傻瓜把一块石头扔进水里,十个聪明人都找不回来。他也不想讨论他认为纯属自己个人写作习惯的问题,是用笔还是用打字机写作,他在纸上按压的力度有多大之类。对于艺术家来说,如此关爱自己的鞋带是危险,甚至是不道德的。最后,有些问题会使这次访谈的“空间过于宽泛”,需要在其他场合做更为充分的处理。
两次录音访谈都是在贝娄所在的芝加哥大学社科楼五楼办公室进行的。这间办公室虽然很大,却是那种相当典型的正四边形格局:大部分地方相当黑暗,只有一块明亮的区域,被他的桌子所占据,桌子紧挨并且正对一组三扇的屋顶窗;靠墙壁排列着几个深绿色的金属书架,偶尔被用来充当存放各种书籍、杂志和信件的地方。一套《鲁迪亚德·吉卜林全集》(“这是送给我的”)与几本新小说的试读本以及贝娄本人的书放在一起,包括最近刚出的《赫索格》法语和意大利语译本。一张桌子,几个打字台以及各种破旧和不匹配的椅子,以明显随意的方式散落在整个房间里。门里面的一个墙架上挂着他那顶漂亮的黑色毡帽和手杖。成堆的纸张、书籍和书信扔得到处都是,总的感觉是凌乱。当你走到门口时,会看到贝娄经常坐在他的打字台边,快速地用一台便携式打字机敲打着,回复他每天收到的众多信件中的几封。偶尔会有一位秘书走进来,在房间的另一边继续打计划之类的东西。
两次访谈期间,贝娄坐在他的桌边,在明显伸进房间的屋檐投影之间,室内反射着从南面的屋顶窗透进的午后阳光。往下四层就是五十九号大街和米德路,大街上汽车和行人发出的噪声不绝如缕地扎进办公室。提问时贝娄总是仔细聆听,而且回答得也很缓慢,频频停下来琢磨他所能想到的精确说法。他的回答都很严肃,但充满自己的幽默特色。显然这种愉快的思想兜转游戏让他感到很开心,往往在这样的兜转中问题已经作答。为了把自己的想法向记者解释得更清楚,他在整个过程中可谓备受辛苦,反复询问这句话是否说清楚了,或者是否应该就这个话题多讲些内容。访谈期间,他的注意力高度集中,这足以让人感到疲惫,两次录音都以他坦承自己精疲力竭而结束。
每次录音访谈结束后,都会打出一份谈话的文字稿。这些打印稿上处处都留下了贝娄用钢笔和蘸水笔修改的痕迹,完成这样一次完整修改需要花费多达三次的面谈时间。然后再打印出一份修改稿,整个过程重新开始。这项工作是在访谈者在场时完成的,相关改动会被反复斟酌。这些工作通常在贝娄的办公室或者他的寓所进行,从他的寓所可以俯瞰奥特尔大街和密歇根湖。不过,有一次修改工作是贝娄和访谈者坐在杰克逊公园的一张条椅上进行的。那是一个美丽的十月的午后。其中一份录音打字稿是在当地一家酒吧,在啤酒和汉堡的款待中完成的。
修改的内容可谓形形色色。经常会有意思上的微妙变化:“这才是我真正想说的。”其他变动不是让语言更简练,就是涉及风格性质的改进。任何他认为偏离主题的片段都会被删除。访谈者最为后悔的就是修修剪剪,这种修剪让好多极具贝娄特色的机智不见了踪影:有几个地方,他开始觉得完全是在“展示”自己,然后这些地方便被抹去了。另一方面,只要他能用一种意想不到的口语化措辞——在语境中往往证明是很幽默的——来代替传统的文学术语时,他都会尽量那么做。
——访谈者:戈登·劳埃德·哈珀,一九六六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