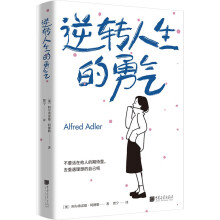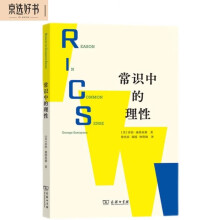《不委屈自己、不伤害他人的说话之道》:
憋出来的抑郁症
25岁的丹尼斯是个性格开朗的新英格兰年轻人,他刚搬到纽约并在一所法学院求学。在开学前,他来咨询如何应对从小城镇搬到大都市所面临的变化和挑战(是他从事临床医学的妈妈要求他这么做的)。丹尼斯大学生活的最初几天过得非常糟糕。首先,他的助学金出了问题(那需要一大堆的书面文件,但最终能够解决)。另外,他的室友喜欢在深夜看血淋淋的恐怖片,而这类电影一向是丹尼斯最受不了的。然后,他去书店,却发现银行把他的信用卡额度限得太低,使他无法买齐所需的书。而雪上加霜的是,他两周前订购的手提电脑还没送到。
无比烦恼的丹尼斯来到助学金办公室,那里一个“不耐烦且超负荷工作”的员工叫丹尼斯提供一些本已经提交过的档案材料,可丹尼斯已经没有副本了。接着,他又去了银行,想申请调整信用卡额度,但这需要老家银行的资料证明,他也没有。沮丧的丹尼斯回到宿舍倒头就睡,深夜他被令人毛骨悚然的尖叫吵醒。他冲进客厅,室友又在那儿入迷地看《猛鬼街》。丹尼斯的忍耐到达了极限,对室友咆哮起来,指责他太自私,不为他人着想。他的室友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因为他不知道丹尼斯已经睡着了。据丹尼斯的说法,他们的争论声很大,甚至都可以压过《猛鬼街》里受害人的惨叫声了。第二天,丹尼斯的新手提电脑终于送来了,但每次他打开网络浏览器时系统都会崩溃,他用尽了办法,似乎都不能解决问题。丹尼斯不得不最终放弃,拼命跑到学校,此时他上课已经迟到了。
丹尼斯那天下午来和我会面时,已是极度沮丧。他先号啕大哭,接着说他承受不了法学院的压力,决定回新英格兰去。我很震惊,安慰他说他碰到的所有问题都和他的学业无关。但那时,丹尼斯已经感到身心俱疲,他觉得哪怕是再小的问题他也无力解决了。
我意识到丹尼斯已经一步步走向抑郁,貌似他已完全被打击得绝望了。情况变化之快令人震惊。一周前,丹尼斯虽对开学有些担忧,但他的言谈举止都流露着积极自信。我费尽办法想让丹尼斯重新考虑一下他的处境,但都失败了。他觉得考虑留下这个念头都让他无法忍受。一周后,他就离开了纽约。
丹尼斯的不幸给我们展示了习得性无助所隐含的真实威胁——而更可怕的是,习得性无助能在各种情况下滋生。丹尼斯第一次解决问题失败产生的无助就慢慢演变成一种对象广泛的无力感和无用感,最终导致他做出冲动不成熟的决定。他确信自己无法达到法学院的要求,尽管他从没在同学、课程或是与教授关系上遇到过问题。
马丁·塞利格曼和其他研究者通过众多的实验总结出了习得性无助是怎样从一个事件传播到其他事件中的。但随着进一步的思考,马丁·塞利格曼意识到了他们的逻辑中有一个大问题。基本上我们所有人都会和丹尼斯差不多,遭遇令人沮丧的抱怨。如果习得性无助真的那么轻易就发生作用,如果抑郁通常会随之产生,那为什么不是所有人都感到无助走向抑郁呢?塞利格曼复查了他们的数据,并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见解。
并非所有的老鼠和狗都会在无法回避电击后变得无助,在面对无法解决的问题时也并非所有人都会无助。不管做什么,有1/3的人是从不放弃的,同时1/8的人从一开始就感到无助。为什么有的人能不断奋斗不屈服于无助,而另一些人却在麻烦一出现时就崩溃了呢?
30年前,塞利格曼就提出了这个具有深远意义的问题。难道真的存在什么因素或特性让一些人对习得性无助免疫,并且快速从抑郁中复原?为什么另一些人却无法抵抗习得性无助而更容易陷入抑郁的罗网呢?我们又能从这些特性中学到什么,让我们可以避免习得性无助?
这些问题的答案与我们最初是如何看待遇到的困境紧密相关。具体来讲,它可归结为一个重要的因素——到底我们认为什么人或什么事该对我们的问题负责。
谁该对问题负责?
当我们发现自己的境地不那么尽如人意,并且有理由相信做任何事情都无法改变情况的时候,我们最惯常做的事情就是试图弄清我们为什么会沦落到这种境地。我们总是倾向于把责任归咎到外在而不是我们自身,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老是抱怨家具“挡路”的原因。塞利格曼和其他研究者发现,我们怎样归结责任,把无法控制的因素归咎到谁或者什么事物,对我们是否会变得无助和我们的整个心理健康都有重大影响。
那么,比尔该把他的机顶盒问题归咎于谁呢?令他陷入窘境的罪魁祸首又是谁呢?比尔认为过失是有线公司的无能造成的(外部因素),而不是他自身的不作为(内部因素)。塞利格曼的研究表明,如果我们觉得造成失败的原因来自外部,那么我们就会想当然地认为那不是我们所能控制的,而这种想法非常有可能使我们陷入习得性无助的危险。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