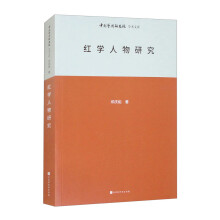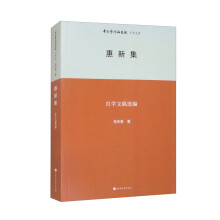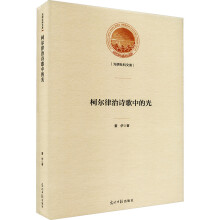《李泽厚历史本体论研究》:
李泽厚的哲学文本可以清晰地划为三个方面,即纯哲学、美学和思想史,然而这三者在文本中又是互相交融的,这是由于他不同时期虽然研究领域各有侧重,但总体说来,仍是三方面互补并互相支撑的结果。首先我们先来看李泽厚这三方面中相对影响较小的思想史部分,李泽厚的三部思想史著作,1979年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论》,1985年的《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及1987年的《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从古至今地从其本人的思想出发,阐述了他对于从先秦到现代新儒家的见解。这三本《史论》,与我们通常所见之教科书有极大不同,他们都是李泽厚用以论证自己思想体系的一个工具,一个旁证。例如在这三本书中,《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的篇幅为最多,而《中国古代思想史论》的篇幅为最少,在不多的篇幅中,先秦部分就占了三分之二还多。其中的重点又在研究孔孟的部分,原本任何一部中国古代哲学史或思想史都会将这一部分作为重要的部分,但是在李泽厚的《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孔孟、荀子、董仲舒的部分格外重要,是“六经注我”的部分,而其余的部分,则更多的是带有“我注六经”的意味。也就是说,作为李泽厚哲学中的伦理学部分,是以先秦儒家思想为核心来建构的,而又着重提出了董仲舒作为汉儒在儒学世俗化和制度化,并最终使伦理走向政治的过程中起到的决定性的塑造作用。而关于庄禅思想,一方面用以说明“人的自然化”也即审美境界,另一方面则重申“儒道互补”,总体在于对美学方面的把握。
《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和《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也有类似的情况,如前所叙,前者成书最早,篇幅最多,是因为李泽厚前期一直关注的,是从康有为、谭嗣同到整个近代时期的维新、改良、启蒙、革命的命题,这种起源于对社会关注的视角投射到历史中,首先影响的便是近代史。同样与其他近代史有所不同的是,洪秀全和太平天国思想被放在开端的位置,除了历史的原因外,还有一个对于李泽厚自身体系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中国传统儒家思想与外来的基督教的关系问题。太平天国运动作为近代以来西方基督教在中国影响力最大的一件事情,二者之间的结合显示了一种怎样的文化冲突,结果又给我们以怎样的启示,对李泽厚理论中儒家的包容和同化性,有着历史现实的支撑。而后大篇幅的维新派思想研究都可以视作对他“新启蒙”“救亡压倒启蒙”“要改良不要革命”“告别革命”等思想的理论支撑和历史依据。在后来对于李泽厚的批判中,之所以很多毫无根据,根本站不住脚,也恰恰是由于李泽厚的这种深厚的近代史的积累和储备,并且同他的思想已经形成了一体化的表里结构。
而最后的这部《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则可以看作李泽厚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那种相对宽松的学术氛围中的登峰造极之作,与《中国古代思想史论》的“六经注我”,托古喻今不同,前者则是直接从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开始,论证“救亡压倒启蒙”,提出“转换性的创造”。继而通过现代三次学术论战,经由胡适、陈独秀、鲁迅——尤其是鲁迅,作为唯一在近现代史论中都有涉及的人物,李泽厚认为他在启蒙中的作用是不可比拟的——到毛泽东和马克思主义,从二十世纪中国文艺这样一个美学问题,到纯哲学的现代新儒家和最终的西体中用,这本书看似异常繁杂,完全不似以往两部史论,颇有仓促之感。然而结合作者当时的历史情境和思想阶段,又不难看出,从近代到现代以来,虽然从哲学分期上已然进入现代的领域,然而在经济上,在社会生活上,在前提性的工艺一社会结构的层面,我们还处于前现代化,或者至多是现代化刚刚开始的时期。思想的前进和领先的状态、已经过去不久的“文革”对于思想领域的冲击、“文革”后对于“文革”思想的一种清算,都复杂地体现在了当时的学术思想中。笔者认为,这便是造成这部《中国现代思想史论》有如此结构和表现的原因。从启蒙与救亡,最终到“西体中用”,看似是一个伦理—政治的问题,实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或者说传统儒学马克思主义化的过程。所以,所有的三部思想史论,都是在为李泽厚的纯哲学、美学和中国传统文化服务的,而在这三者中,又以中国传统文化为重中之重。即本书的第5章,李泽厚历史本体论是如何渗透儒家思想,以最终达到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吸收、理解和“转换性的创造”。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