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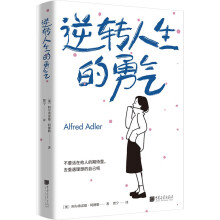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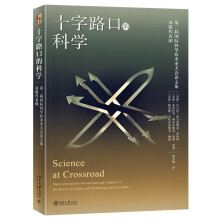

★ “只有正义是可能的,良好生活才是可能的。”学者周濂公共写作力作全新增订版。
作为以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为研究方向的学院派知识人,作者周濂不仅有深厚的哲学学术功底,也具备健全的现实感,关注公共事务并实践着公共写作。继《你永远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后,作者再次从哲学概念辨析视角切入现实问题,为致力于过清醒而值得过的生活的读者呈现2001—2021年思考力作《正义的可能》。
★ “正直的生活有代价,不正直的生活代价更沉重。”以概念辨析去看清现象背后的关键。
从现实问题引入,进而抽身后撤,将抽象的概念与日常的所感相联系,脱离特定事件和背景去思考背后的观念,带读者将所见、所读及亲身经历陌生化,逐渐掌握一种柳叶刀式的辨析能力,去看到不同现象背后的关键,呈现哲学思考融于日常所感的一面。
★ “用会心会意的语言去表述复杂深刻的差异。”将政治哲学概念融入日常,后退一步看现实。
“正义如何可能?”“勇气从何而来?”“如何做一个正派的人?”“如何实践德性?”在有意义的科学问题都已被解答而不确定性依然是日常的当下,作者带我们回归政治哲学的核心概念“权力”“自由”“平等”“正义”,提供“我应该如何生活”的另一种选择。
★ “正义的可能”首先是“成为正义的自我的可能”。以自身做标本,一次自我彰显的历程。
通过一次次自我诘问,作者将写作首先指向了自我,去探究在当下如何真诚地为人,怎样才是一个勇者,如何实现卓越。通过自我探究与剖析,作者将自身作为标本,向我们展示了“正义的可能”首先是“成为正义的自我的可能”。
★ “没有人是荒岛上的鲁滨孙,原子化的个人只是一个想象。”以共同体的生活通达幸福人生。
“我如何才能过上一个幸福美好的人生?”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共同体的生活予以保障的。人生而自由平等,但与此同时,我们还有社会属性,与朋友、爱人结成某种共同体,才能摆脱孤独、焦虑,找回归属感、安全感。唯有如此,才能过上幸福美好的人生。
★ “我们反复做什么样的事情,我们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以理性的力量,过良善的生活。
不停追问意义恰恰意味着处于意义缺失状态。所有的生活都是一场实验,但是生活不应该发生在化学实验室里。不妨放下成见和偏见,尝试打开全身毛细孔,去感受、倾听、体验、理解可能遇到的各种人和事,去真实地生活,沉浸于所做事情中,完成“自我确证”。
每当有人语带嘲讽地问我:“你们学哲学有什么用呢?”我就会回答说,我们学哲学虽然看似无用,其实是有大用,所谓“无用之大用”。现在张维迎老师给我提供了另外一个说法,就是理念的力量。
说到理念的力量,我经常会举一个例子。法国大革命的时候,当民众攻陷巴士底狱的消息传到巴黎南郊的凡尔赛宫,路易十六惊慌失措之下问道:“什么?造反了吗?”当时的波尔多公爵回答他说:“不,陛下,是革命。”造反与革命,一词之差,不仅是语词的转换,更是观念和理念的革命。
还是这个法国国王路易十六,当他身陷囹圄的时候,据说在夜半人静之时,他说了一句话:“是这两个人消灭了法国。”他说的这两个人,一个是卢梭,一个是伏尔泰,都是哲学家。
所以,改变观念就是改变世界!
大家都知道,马克思死后葬在伦敦北郊的海格特公墓,在他的墓碑上刻有两句话,第一句话大家耳熟能详:“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第二句话大家同样耳熟能详:“从来的哲学家都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改变世界固然重要,但解释世界同样重要,因为马克思本人正是通过解释世界来改变世界的,如果不是因为他发明了“剥削”“剩余价值”这些概念,全世界的无产者怎么可能会联合起来去推翻这个旧世界,建立一个新世界?当然,正因为理念具有摧枯拉朽的力量,正因为理念可能让我们上天堂也可能使我们下地狱,所以就不应该让某一种特定的理念去占据讲台、电台、电视、报纸或者网络,而是应该充分借助思想的自由市场,让每一种理念和观念在公平、公开和自由的环境下进行竞争,进而减少语言的腐败、思想的腐败。
说到语言腐败,我特别认同张维迎教授《理念的力量》第17章“语言腐败及其危害”中所传达的观点。什么是语言腐败?用张老师的话说,指人们出于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的目的,随意改变词汇的含义,甚至赋予它们与原来的意思完全不同的含义。语言腐败至少有三种严重的后果:首先,它严重地破坏了语言的交流功能,导致人类智力的退化。其次,它导致道德的腐败。张老师引用了托马斯·潘恩的话,我非常认同:“当一个人已经腐化而侮辱了他思想的纯洁,从而宣扬他自己不相信的东西,他已经准备好犯其他任何的罪行。”再次,它导致社会走向高度不确定和不可预测性。
对于以上观点,我无一字不赞同。如何避免语言的污染,作为一个哲学工作者,我首先想到的是保持智者的审慎,避免误用或者滥用超级概念或者宏大概念。
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1939年秋天,当时二战激战正酣,维特根斯坦和他的学生马尔康姆在伦敦的泰晤士河畔散步,两个人闲聊的时候说起一则八卦消息:德国政府正在谴责英国政府煽动一起谋杀案,谋杀的对象是希特勒。维特根斯坦评论说,如果这个消息是真的,我也不会惊讶。马尔康姆反驳他说,这种行为跟英国人的“民族性格”是不相容的。这种争论本来是无伤大雅的,但是维特根斯坦却非常生气,他们本来是好朋友,但是从此之后,维特根斯坦跟马尔康姆割袍断交了。五年之后,马尔康姆已经离开英国,到美国的太平洋舰队上服役,这时候他收到维特根斯坦的来信,终于了解了维特根斯坦为什么会生气。在那封信里,维特根斯坦是这么回忆他们的争论的,他说:“你关于民族性格的议论,它的简单幼稚使我吃惊,我因而想到,研究哲学如果给你带来的只不过是使你能够似是而非地谈论一些深奥的逻辑之类的问题,如果它不能改善你关于日常生活中重要问题的思考,如果它不能使你在使用危险的语句时比任何一个记者都更为谨慎,那么它有什么用呢?”我对维特根斯坦这句话印象极其深刻。在我们这个时代,因为知识的普及和资讯的发达,越来越多的人能够毫无门槛地接触到各种各样抽象的、玄奥的哲学理论和莫测高深的超级概念,用维特根斯坦的话说,就是那些“危险的语句”。但是,正像维特根斯坦所说的,如果人们非但没有因此养成谦卑的习惯,学会鞭辟入里、小心谨慎地分析,反而借此赢得了知识上的骄矜,随心所欲地滥用这些危险的语句,那将不只是对哲学的践踏,而会戕害公共讨论的品格和日常生活的常识感。
除了要警惕超级概念的滥用,还要警惕政治语言、军事语言以及网络语言的滥用,我们的生活世界正在充斥着各种各样暴力的语言。暴力的语言、粗糙的语言必然会导致暴力的思维、粗糙的思维。奥威尔说:“思维的浅陋让我们的语言变得粗俗而有失准确,而语言的随意、零乱又使我们更容易产生浅薄的思想。”在我看来,这种僵化、暴力、粗糙的语言表达出来的是对思考的仇恨,是对思想者本身的恐惧。如果说清晰、准确、有逻辑的思维是走向观念革新的第一步,观念的革新首先就表现在语言和表达上。还是奥威尔的原话:“抵制不良英语并不是一件无足轻重的小事,也不只是职业作家所应该关心的事情。”那么同样,在我看来,抵制不良中文也不是一件无足轻重的小事。因为语言是存在的家,我们是通过语言来定型我们的思想,通过语言来塑造我们的情感。
在谈完理念的力量、语言的腐败之后,最后我想谈一下情感的教育。
我笃信理念的力量,但我并不认为理念是万能的。大卫·休谟说:“理性是激情的奴隶。”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经常会发现让我们感到有些沮丧的事实,哪怕你费尽口舌,试图通过理性的论证去说服或者改变一个人,但你会发现,即便你把他说得哑口无言,你仍然无法真正地说服他或者改变他。
有一个道德心理学家叫乔纳森·海特(Jonathan Haidt),他在《正义之心》中指出,我们大脑存在类似于照相机的曝光反应,它会把你熟悉的词汇和事物自动标识为好的、坏的、喜欢的、厌恶的。这种曝光反应的速度非常非常迅捷,过程只有200毫秒左右。这是什么概念?1秒有1000毫秒,可想而知这是一个多么短暂的过程。换言之,当你看到俞敏洪老师的时候,你立刻产生了好感,然后你才会通过理性去寻找喜欢他的理由。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理性是情感的慢动作,理性是情感的马后炮,理性是情感的奴隶。
海特说,我们的社会和政治判断尤其出于这种直觉,出于情感的曝光反应。对于这一点,我深有感触。我现在还记得7岁那年的一天,我们三线厂的喇叭突然暂停了红色歌曲的播放,用沉重、悲痛的声音开始播发悼文。大家可能太年轻,不知道“三线厂”是什么意思。为了备战设想中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我们国家当年在一些偏僻的山区建立了各种各样的国防工厂,我从小长大的那家工厂对外号称是生产化肥的,其实可以随时转产炸药。我当时坐在门口跟小伙伴在玩儿,我妈把我一把抓进屋里,跟我说:“从今天开始,三天之内不准在公共场合大声说笑。”“为什么?”“因为我们慈祥的宋庆龄奶奶去世了。”我当时不明就里,但是很快接受了我妈的解释。多年以后,我才认识到,严格来说,我妈给出的这个解释并不是一个道德上的理由,而是直觉上的锻造和情感的规训。“慈祥”的宋庆龄奶奶去世了,嬉笑玩闹当然是错误的行为,这是一种无须任何推理的直觉判断,就像我们看见鲜花会愉悦,听到“癌症”这个词会心悸。从小到大,我们都是在各种各样情感曝光反应中接受了一套黑白分明、爱憎分明的情感教育,最后建立起了一一对应的情感反应。比方说,旧社会是“万恶的”,农民起义是“可歌可泣的”。语言和情感就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被加工,被消毒,被驯化,哪怕多年以后,我们知道农民起义不一定是可歌可泣的,旧社会不一定是万恶的,可能还有温情脉脉的一面。但是,那种深入骨髓的情感反应仍旧挥之不去,以至一旦有人想挑战我们根深蒂固的情感反应,就像在根本上否定我们自己,这是自我认同的一种东西。
所以,在这种意义上,我认为,我们不仅应该重视理念的力量,还应该关注情感的力量,应该关注情感的教育。因为情感教育可能是改变一个人的根本路径。《正义之心》这本书中说,我们存在的六种道德基础的知觉,分别是两两对应的十二个概念:第一,关爱和伤害;第二,自由和压迫;第三,公平和欺骗;第四,忠诚和陪伴;第五,权威和颠覆;第六,神圣和堕落。海特认为,在美国的政治光谱中,自由主义更在意的道德基础是前三组,反映在社会公共政策上面就是关心弱势群体,反对强权压迫,强调对穷人同情。对比可知,专制主义更关心的道德基础应该是后三组:忠诚和背叛,权威和颠覆,神圣和堕落。
……
英国哲学家怀特海曾经说过一句话:“在任何理解之前要先有表达,而在任何表达之前,先要有对重要性的感受。”什么是重要性的感受?重要性到底寓居在何处?这个看似非常深刻的哲学问题,其实有一个非常浅俗的答案,重要性寓居在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经验之中。当然,这里所说的日常生活经验,首先是健康的生活经验、真实的生活经验,尤其是免于恐惧的生活经验。用哈维尔(Václav Havel)的话说,就是生活在真实中。
真实地生活,真实地说话,真实地思考,真实地写作,做正派的人,成就正派的社会。就像我们的古人所教导我们的那样,堂堂正正、自尊正派、慎言笃行、有耻且格。不久前,有一个朋友给我留言说,正直的生活是有代价的,而且很沉重,太沉重了。这句话让我沉默了很久,我当然同意他的说法。但另一方面我想说,其实不正直的生活同样是有代价的,同样很沉重,而且甚至更沉重。张东荪先生在几十年前说过一句话,他说,专制之恶不仅在于政客贪赃枉法,肆意妄为,更在于“人民多恐惧之心、伪诈卑贱之习”。
有人曾经这样总结我们当下社会存在的一些现象:第一,为了一点点利益害人而无底线;第二,有权的没权的都不看长线,只看今天,仿佛没有明天;第三,太多人只关心结果,而不论是非;第四,很多人幻想甚至崇拜不劳而获;第五,遇事要么冷漠逃避,要么阴阳怪气;第六,民族主义比色相更好卖。如果这是对我们所置身的生活世界的真实刻画,那么我们为此付出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
我经常向我的学生推荐一本书,那是一位著名的古典学家依迪丝·汉密尔顿(Edith Hamilton)写的,书名叫《希腊精神》,里面有一段话我非常喜欢,愿意跟大家分享一下。她说:“文明是一个用滥了的词,它代表的其实是一种高远的东西,远非电灯、电话之类的东西所能包括。文明给我们带来的影响是我们无法准确衡量的,它是对心智的热衷,甚至是对于美的热爱,是理智,是温文尔雅,是礼貌周到,是微妙的情感。如果那些我们无法准确衡量的事物变成头等重要的东西,那就是文明的最高境界。如果人没有因此变得优柔寡断,人类的生活就达到人们很少能够达到的、根本没有人能够超越的东西。”这种对心智的热衷,对美的喜爱,对荣誉、对温文尔雅、对礼貌周到、对微妙情感的珍视,我们曾经并不陌生。
我最近读到沈虎雏怀念父亲的一个访谈,说到沈从文在一次闲聊中提到《水浒》当中武松出差前细致安排武大郎生活的场景。沈从文说,《水浒》这些地方写得好,家常、有人情。他又聊到古典名著当中写过很多刚烈鲁莽的人物,但是只有几个能给普通读者带来深刻的影响。为什么?因为除了故事曲折动人,更成功的地方在于这些粗人被作者写得非常的妩媚,非常的动人。用简单的语言谈论复杂的文艺,用日常的语言描绘微妙的情感,对任何美丽的、纤细的事物充满敏感和敬意,这就是文明最高的阶段,这也是我所向往的生活。
不久前,朋友圈在传一位大姐的文章,印象最深的是这句话:“谁爱得最多,谁就注定了是弱者。”我想接着这句话往下说,我们不怕爱得更多,我们也不怕成为弱者,我们怕的是为了避免成为弱者而失去爱的能力。那篇文章的题目叫作《弱者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