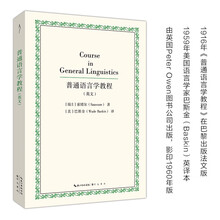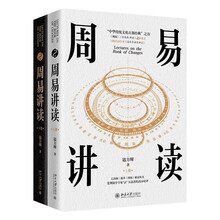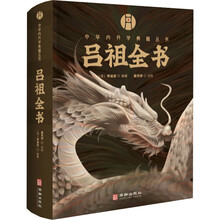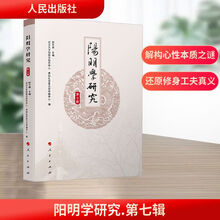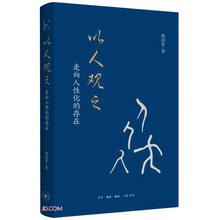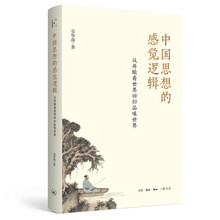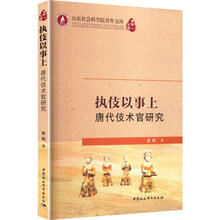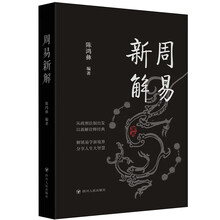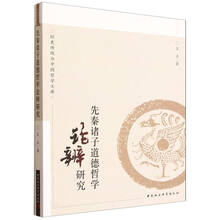《阐释学五辨》:
任何学科的进步都依靠应用。无论如何抽象的形而上玄思,若非上升为系统科学的思维方式,若非找到更重要的解决问题的方法,都无从成立和发展。所谓阐释学,无论本体论还是方法论,若不能为各学科广泛应用,重归冷宫以至湮灭是必然结果。公羊高以今文为立场和方法阐释先秦经典,为其所处时代政治文化发展所用,中国古代阐释学也因此而有早期的系统规则与方法;海德格尔以存在论为立场和方法阐释荷尔德林的诗作,其本体论阐释学因此而发扬光大,并因此而丰富和发展了其本体论阐释学思想。中国古代缺少系统的阐释学集合,但阐释的方法应用于深厚的经学阐释,阐释学在应用中逐渐累积成长出中国独有形态。西方由古希腊的哲学对话始,再有圣经阐释与法律阐释在应用中成学,经两千年积累方有施莱尔马赫的一般阐释学出世。首先应该扩大阐释学在人文学科中的应用,已引起关注的是文学阐释研究。文学阐释的特殊性被突出强调,其前见的不可避免与适度消解,文本的自在意义与阐释者动机诉求,无限意义与有限约束等诸多原点问题被讨论。虽无共识,但讨论本身的建构价值充分显现。历史阐释学亦有起步迹象。特别是对西方史学理论的反思,对事实尊重,对意义发挥的根据与限度,以及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批判,在历史阐释学的建构过程中贡献颇多。哲学阐释学最弱,这里是指哲学的阐释方法,即对哲学阐释的一般方法研究缺失。本体论阐释学是对阐释学的存在意义研究与定义,不是哲学研究方法论的讨论。哲学研究同样需要阐释学的辅助以至引导。本体论阐释学的实际阐释方法本身是突破点。
传统的人文学科以外,在法学研究及司法实践中阐释始终在场。法律阐释学是阐释学的重要起点。各个国家的宪法修正或法律解释,是阐释学的最直接应用。理论上讲,对一切社会科学研究而言,方法论的阐释学具有一般性意义,只要是在表达,意即将对现象的认知和理解表达于人,阐释就在展开。如此,阐释目的、路线、标准、规则等等,阐释学的全部问题都将以其特有形态呈现出来,发生作用,决定阐释的质量与水平。理性的阐释主体,努力掌握和自觉运用阐释学原理,其学术阐释会有新的面貌。更重要的是,各学科的创新与创造,新的学术思想及其表达与呈现方式,可为阐释学的构建与发展供给生动活跃的思想资源,是阐释学得以成长的生命之源。不断前进的实践创造,永远高于停滞原地的历史经验。
六、形态的系统与完备性
当代中国阐释学应有其完备形态。有一种意见是,阐释是独立主体的实践行为,因为主体动机与方法不同,以确定对象为目标的阐释,从行为到结果差异深刻。西方后现代文化主潮,就是反对普遍性追索,摒弃一般方法论的集合与描述。伽达默尔就认为阐释学“本来就不是一个方法论问题”,“不是为了构造一种能满足科学方法论理想的确切知识”。①这里的要害是,中国阐释学之学到底为何意?我认为,它包括两个层面的义与意。其一,此学为学问之学,是实践与经验的累积和增长。这种实践与增长无系统总结,为学术共同体所默认,为传统所容纳,诸如我们所认知的中国古代的阐释实践,就以离散的经验呈现,无体制性规定,其散漫的、实用的,或者可称为实践理性的展开过程与成果,集合为阐释之经验和学问。其传承方式是教化,在实践中体验、感悟,无条条框框规定和约束。其二,此学为学科之学。在此意义上,阐释学作为与其他学科,包括紧密联系的哲学、语言学、心理学相区别的独立知识体系,对理解与阐释,具有普遍指导与应用意义。一切学术研究无一例外地以阐释开显,阐释因此而有一般本体论和方法论的意义,也因此而区别及高于其他各学科的存在。可以提出的疑问是,阐释既可以离散的实践方式存在和展开,中国古代阐释学就以此为长,构建系统、完备的阐释之学为何必要?如此就要讨论学科以及整个科学建构的必要性。人类的实践经验由个别、具体而起,个别与具体的经验必须上升为一般知识,才可能传承和推广,无知识化的科学建构,人类的实践包括精神活动的实践在内,其行为是盲目的,是要耗费无尽资源,持续无效重复的。学科的建设,将个别经验上升为一般制式,用于规范实践,实践才是有指导的实践、自觉的实践。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