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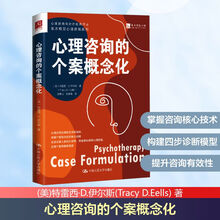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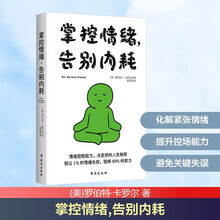


当我们尝试与一个独特生命面对面互动、靠近与理解,当直觉与分析准则的边界再次接触,我们如何建立对自己工作的信任?超出准则范围的直觉之地是否存在?
《与病人谈话:自体心理学视角下的创造性直觉和分析准则》作者从专业角度,提供了一个温暖的视角,解读精神分析中直觉的力量。本书除了呈现技术层面上的知识,还是一份关于如何信任自己及如何使用对自己的信任的指南。它指引咨询师从僵化的规则束缚下解放出来,发展自己对工作的信任、对自身直觉的自在使用,从心所欲不逾矩。
当我们尝试与一个独特生命面对面互动、靠近与理解,当直觉与分析准则的边界再次接触,我们如何建立对自己工作的信任?超出准则范围的直觉之地是否存在?
《与病人谈话:自体心理学视角下的创造性直觉和分析准则》作者从专业角度,提供了一个温暖的视角,解读精神分析中直觉的力量。本书除了呈现技术层面上的知识,还是一份关于如何信任自己及如何使用对自己的信任的指南。它指引咨询师从僵化的规则束缚下解放出来,发展自己对工作的信任、对自身直觉的自在使用,从心所欲不逾矩。
第十一章 和病人在一起
存在是伟大的解释者。
——亨利·大卫·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
和有些病人工作中最大的挑战,在于找到与他们相处的方式。珍娜(Jenna)是一位43岁的商人,在成长的过程中受到父亲的严重虐待。当3年前双胞胎兄弟去世时,她觉得自己的一半生命也随之而去了,生活似乎不再值得继续。
她在治疗中感到不舒服,抱怨我看着她的样子让她觉得自己很容易受到我的攻击,谈论感受也令她大为不安。我想让她舒服些,所以我们尝试了各种摆放座椅的角度,最后发现如果把座椅摆在面对着窗口的位置,她坐在我后面,背靠着墙,会是她可以忍受的和我在一起的最佳方式。当我说看不到她让我不舒服时,她说那是我的问题—她说得对。
她讨厌冲突,但当我试着去理解她与下属争吵时感受到的痛苦时,她说讨论那些冲突会给她带来更多痛苦。我想如果我能安静地和她一起坐一会儿,就会对她有帮助。但是,当我听到她的叹息和看到她烦躁的举动,我意识到她感觉被我抛弃了。我和她说我感到绝望,不知道这是否也反映了她内心的状态。她表示同意,但是不想和我谈论这些感受。有时她每天都来,有时她说过来见我让她太痛苦了,要请一周假。
咨询就这样展开着,一周又一周,一月又一月。珍娜在感情上受过伤,非常脆弱,但我相信如果我能设法和她在一起待着,治疗最终会自己走上正轨。
内 隐 记 忆
弗洛伊德认为,潜意识的内容能够影响意识功能。这些内容曾经是在意识层面的,后来被压抑起来。内隐记忆的概念来自神经科学的贡献,它拓宽了我们对潜意识内容的思考(Pally,1997)。内隐记忆是指在没有意识觉察的情况下储存在记忆中的体验,可以包括各种技能,如骑自行车、情绪反应—比如在某些经历中产生或在某些条件作用下习得恐惧感。斯特恩(Stern,1985,2004)认为婴儿和照顾者之间的互动会泛化为期待,他描述了一个12个月大的婴儿在与母亲短暂分离后重聚时,婴儿“知道”是要张开双臂接近母亲,还是要假装看不见母亲—夸大对母亲的需要或无视母亲。这种在关系中习得的做法不是有意识的,也不是潜意识的动力(压抑),而是存在于内隐认知的领域;它影响着日后生活中的所有关系,包括治疗关系。
随着语言的发展,如果孩子的生活环境允许他安全地谈论情绪事件,他就可能会对情绪事件有所意识。如果创伤经历发生在孩子习得语言之前,或者如果孩子从来没有机会谈论这些经历,那么它们就会被编码在内隐记忆中,无法诉诸讨论,甚至可能永远不会得到有意识的觉察。早期创伤可能不会被有意识地记住,但它可以通过关系被重新体验,包括病人与分析师的关系。这种体验无法用语言表达,只能被展现出来(Benjamin,2006),治疗师通过对自己身体状态的觉察来“绘制地图,穿越雷区”—一个具有潜在爆炸性的、令人晕头转向的移情—反移情活现的雷区(Davis,1994)。换句话说,我对待病人的方式可能比我说些什么更重要。
因为我的性格中天然具有内向、保守的倾向,所以在病人所说的话触发某段记忆时,这种新的思维方式让我得以更自由地谈论自己的体验。有时我会分享我的回忆,有时不会,这些都要依靠直觉来判断。但无论我做不做自我袒露,我都会密切关注病人,留意他们是富有活力的,死气沉沉的,还是焦虑不安的。当病人明快起来时,我就会感到安心,知道我们走上了正轨;但如果病人感到焦虑或退缩,我就知道我错过了一些东西,需要重新思考正在发生的情况。
人们会问:“如果你考虑错了怎么办”。我会说,在这种思维方式的指引下,只有忽视病人当下的情绪反应才是错误的。如果我做出了某种诠释,病人看起来很困惑或者有点焦躁不安,我会补上:“也许这样的解释不适合你。”可能是我诠释错了,也可能是病人需要一些时间来思考我的看法,不论哪一种可能,都表明我在那一刻是偏离了轨道的,要往后退一退。我想让病人把我的看法当作一个讨论的机会,而不是定论。当他们可以自由地说出什么样的诠释不适合他们时,我也就可以自由地提出我的看法。分析师和病人总是在协调着与对方相处的方式,治疗中有一个部分就是学习何谓自由、学习把握机会、学习如何从彼此身上学习。正如布卢姆伯格(Bromberg,1996)所说:“分析关系是……在同调与对质之间……或在共情与焦虑之间的辩证协调”,这段话很好地描述了我和珍娜的关系,我和她一起慢慢地了解了她编码在内隐记忆中的经历和体验。
内隐记忆与关系性分析
病人对分析师功能的影响可以成为了解病人内隐记忆的一个窗口。分析师在治疗过程中关注自己的体验,可以为病人提供一个额外的改变机会。露丝(Ruth)是一位46岁的博士研究生,已婚,有一个6岁的女儿,接受治疗期间正在写博士论文。她在童年时经历了严重的虐待,与之前4位分析师的治疗都“失败”了,我是她的第5位分析师。在我们的工作中,她经常抱怨我的工作方式是“罐装的”,我不真诚。我不得不一再努力寻找与她相处的方式,好让她感受到我的真实和真诚。
露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精神昂扬、决心满满,会坚持满足自己的需要。过去我的工作方式更偏经典精神分析,如果是那个时期的我,一定不会喜欢她那样得坚持主张、不顺从—我怀疑其他几位分析师就是这样。现在我能从她的抱怨中听到一个小孩子绝望的恳求,尽管她是想要联结,但也不愿意为了获得联结而放弃自己的个体性。我的指导思想是:病人知道自己需要的是什么,而我的工作是推断他们在好转的过程中需要如何使用我。
露丝在我这儿承受着痛苦,她抱怨我的工作风格,批评我的技术。比如有一天她女儿放学回家,抱怨班里其他小女孩不跟她玩,让她很不高兴。露丝感到内疚,认为女儿经历的社交困难是因为身为母亲的自己没有照顾好她所导致的。露丝指望我帮助她成为一个更好的母亲,她需要的是我的建议,而不是理解。
我回应着她的焦虑:“你担心你的女儿。”这让她很生气,她说:“你很有同理心,也把同理心当作一种技巧,可以,但这不是我需要的,对我没有帮助。”
我大吃一惊,说不出话来。我试着想象她对她女儿的焦虑,意识到我偏离了正轨,想了一会儿,我说:“你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信念,认为自己的身上有些有毒的东西。任何接近你的人都会受到伤害,而现在女儿遇到的困难就是你有毒的证明。无论我或者任何人说什么,都不会改变你的这个信念。”
她明显地放松了,然后带着一丝微笑用柔和的声音说:“有时候得到理解会有些帮助。”
她早年的受虐经历使她觉得自己不讨人喜欢,觉得一定是自己做了些错事,应该受到这种虐待。当她和我一起经历这一切时,我感受到了她的这个信念,并用语言表达了出来。她觉得女儿的抱怨反映出了自己作为母亲的不足。她不相信女儿能解决和朋友之间的问题,觉得必须得由她来出面修复,而现在她想要我修好她。我的回答表明我理解她,也并不需要修好她。我信任她,她也开始信任她的女儿。当我经受住了她给我们关系带来的狂风暴雨,并且继续给予她关心时,她开始相信她是可爱的;看到我没有受到伤害,她也开始相信她没有“毒”。
有一天,她和一位论文委员会的教员发生了激烈争执。这个人不尊重的态度激怒了她,她想要他道歉,而我担心她这样做会破坏获得学位的机会。她觉得这件事情攸关尊严,我提出的任何圆滑处事、实用主义的建议,都被理解为希望她屈服于虐待。然而,她仍然想要我来告诉她该怎么做。
我想起了一次个人经历,决定和她分享。我告诉她,在我身处的文化当中,人们对没有妥善解决的事情怀恨在心是很常见的。在我家里,有时人和人会一连好几天不说话。她笑着说,她家人很多年都相互不说话了。
然后我说我和妻子生长的文化不同,她从小就是天主教徒,天主教的文化强调当有人伤害你时,要学会原谅别人。“我花了很长时间才学会原谅别人,”我说,“但是当我学会了,我们的关系也就大大改善了。”
通过我的例子,她意识到自己可以在妥协的同时依然保有尊严,也不用感到被人虐待。她解释说,她成长的文化背景是如果有人侮辱了你,你必须杀掉他们。我们现在可以理解为什么她经常和身边的人争吵了。她邀请那位教员一起吃了顿午饭,进行了一次建设性的对话,通过谈判解决了冲突。虽然过去的人际关系模式并不会就此消失,但与我以及与教员一起经历的这些新的人际关系体验拓宽了她的选择。
通过分享个人经历—这对我来说很舒服—我成为一个榜样,一个她可以效仿的人。我没有告诉她该做什么,选择权在她,但我向她展示了一种新的交往方式。通过观察她的即时反应,我能够更开放地谈论自己的内在过程,避免程式化的反应,并以更真诚的方式给予回应。这些新的联结方式最终被编码在她的内隐记忆中。
33岁的工程师梅尔文(Melvyn)从另一个城市升职调来本市,他想念过去的朋友和同事。新同事对他的要求更高,给他的支持却更少。他的工作时间很长,感到孤立无援,每天下班都有想参加派对的冲动。
去酒吧和女人约会是很快乐,但是酒吧关门以后,他还是不想回家。为了保持快乐的感受,他开始使用可卡因,并且经常熬夜,第二天上班时往往疲惫不堪。周末的狂欢变本加厉,周一的宿醉也更折磨人。
我聚焦在他每次去参加派对前的情绪体验上,他逐渐意识到自己内心的紧张不安。我向他解释说,他在自我调节方面有困难(Lachmann & Beebe,1996)。他很难维持人际关系,所以常常独自一人,拥有的资源也有限,无法自我安抚,也无法在长时间的辛勤工作后自我恢复。他把酗酒和吸毒视为自己有缺陷的证据,并且为此羞愧。
我想,如果他能理解这是他在努力地进行着自我调节,就会找到更健康的方式来获得安慰。但是他感到越来越绝望,我也开始觉得我们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他谈到了自己在工作中体会到的气馁,我也想知道他在和我一起的治疗中有没有感到气馁。他说:“所有这些理解都无济于事,感觉像是你在认可我的所作所为。”
我意识到他在寻求一种结构化,寻求我的指导,但我也知道他对别人的指手画脚非常敏感。我突然想起了我的一次培训经历,并决定和他分享。我说:“我记得拉尔夫·格林森(Ralph Greenson)谈到过他在玛丽莲·梦露(Marilyn Monroe)去世前为她治疗抑郁症,那时他遇到了困难。每个人都认识梦露,他在工作中遇到的挣扎无人可讲。最后,他打电话给一个朋友—一位在另一个城市的分析师—让这位朋友光听着什么也不要说。他每周和朋友倾诉上一个小时,最后说声谢谢,挂断电话。这就是他遇到困难时进行的自我调节。”
梅尔文表示听说过玛丽莲·梦露的抑郁症和最后的自杀;他看起来似乎更轻松了,我也觉得我们重新联结上了。我说:“有时候很难找到一个只倾听和理解而不主动提出建议的人。”
“这就是我父母的问题。”他突然变得鲜活起来。
我又想到了另一次经历,决定与他分享。我说:“有时在漫长的一天结束时,我看起来很疲惫,我的妻子会说我看起来需要一个拥抱。我觉得这样的拥抱很能给我带来安慰,但有时她不在家,我就会去冰箱找些东西吃或找些饮料喝。”我想让他知道,有很多种自我调节的方法。
在下一节治疗中,他说他的周末过得很愉快。他出去喝酒,但没有喝醉。当回到家感到有些不安后,他就去慢跑,而没有使用可卡因。他还与一些老朋友取得了联系,并约好了见面的时间。他说:“我过去对这些事都太被动了,得找到一种更加健康的方式来照顾自己。”
在进行这些自我袒露的时候,我并不知道在治疗室中激活的究竟是哪种动力,我想信任他的即时反应以及我的直觉。后来我们才明白,在成长的过程中,梅尔文聪明而早熟,他的父母对此很受伤,抱怨儿子不再需要他们了。他们把注意力转向了弟弟,并且开始依赖梅尔文,让他来倾听他们的问题。梅尔文过早地感到孤独,同时又很窒息。在最开始的治疗中,我向他传递出这样一个信息,即他需要的是理解而不是我,我没有意识到,其实他需要一个为他指路的人—一个导师。我帮助他扩大自我调节的选择范围,让他发现自己可以去慢跑而不是使用可卡因。
病人带着设想前来治疗,我的工作是推断他们需要怎样来使用我。病人的设想每天都在变化着,所以当工作偏离正轨时,我需要对他们发出的信号保持觉察。关注联结和联结中断的那些片刻,有助于让我继续待在正轨上—继续和病人在一起。随着时间推移,病人获得了联结的体验,或者联结断裂后重新修复的体验,这最终转化为新的人际关系模式,成为新的内隐记忆。
第一章 两个理论的故事
第二章 理论的作用
第三章 精神分析的角色
第四章 倾听病
第五章 技术指导
第六章 阻抗
第七章 控制掌握理论
第八章 与绝望联结
第九章 幸存的代价
第十章 毫无悲悯的病人
第十一章 和病人在一起
第十二章 伴侣治疗
第十三章 梦的工作
第十四章 督导
第十五章 风险和回报
参考文献
在阅读桑迪(Sandy)博士这部著作到一半时,我立刻觉得要尽力向国内精神分析取向的同行推荐,因为这真正是一部近年来少有又优秀的精神分析临床经典之作。在这部著作中,桑迪博士真诚勇敢地还原了临床工作中各个方面的困难,包括自己在临床工作中遭遇的难题以及与来访者的共同挣扎、突破、思考,也分享了治疗与转化的临床实践经验,这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很少有著作能够如此贴近咨询师和来访者,启发精神分析临床工作实践。
——徐钧
国际精神分析自体心理学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