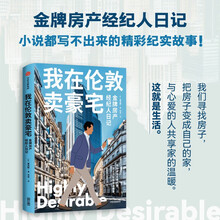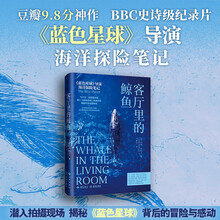张树碑:这可是法治国家
英国地方不大人也少,一共才六千万左右的人口,牛津城大约也只有十五六万人,有来自世界各个国家的各种肤色的人们生活在这里,而大部分本地人都住在市中心以外的地方和乡村里。
像陈先生这样的专业中国二房东,在牛津不止十个八个,光我见过面的就有四个。这些年来,中国人越来越有钱,中国留学生越来越多,访问学者也越来越多,政府派来的各类留学和交流访问人员的数量也不断增加,还有很多家长陪着孩子来牛津游学短住抑或干脆定居长住,所有这些人的住房需求都给了中国二房东越来越大的市场空间。
其实,在牛津,至少一半以上的房客都是从二房东那里租到房子的,做二房东也不是中国人的专利,除了中国二房东,还有西班牙二房东、印度二房东、巴基斯坦二房东、罗马尼亚二房东等等,反正都是些愿意忙活的民族。英国人做二房东的就几乎没有遇到,因为二房东的确是个操心费力的活儿,即使赚钱多他们也不愿意受这份累。
二房东们给留学生解决了很多实际困难,比如我们很多人就是在网上查到陈先生的出租广告的,然后打电话找到他,再见面签合同,从学校的宿舍搬出来,换到海德里道的这栋房子里来的。
有的学校规定,第二学期开始,学校就不再无条件提供宿舍了,学生必须自己出去找地方住,除非,你是个残疾人。原因是学校的宿舍供不应求,无法满足所有学生从入校第一天开始一直住到念完所有课程。再者,自己外出租房住,“有助于增强个人的社会交往和实践能力,可加深个人对英国现实社会的了解”(此言出自某学校后勤部门的告示)。
而第一学期在学校住宿舍也并不免费,房租是一个月五百多英镑,including bills(所有水电煤气等开支账单全包),可是如果不住学校,能租到陈先生转租的房子,只需要花费三百多英镑就能租到一个小房间,再平摊一些水电煤气的费用,一个月再多也不会超过三百六十英镑,当然大房间,像白老师和他太太住的那种就贵些,要四五百英镑,而我租的小房间全部算起来也只有三百六十镑,这样,和以前比,我每月手里还多出来一百四十英镑的零花钱呢。
如果不租二房东的房子,我也不可能单独去租当地人的一整栋房子来住。租整栋房子需要找好几个人一起合租,合租住久了往往是矛盾重重纠纷不断。首先,你几乎没有可能找到一个和自己同一天开始租房,又和你在同一天结束租期的人。其次,交给房东的押金往往是两千英镑(最少一个月或者两个月的整栋房子的租金,一千到两千英镑大约一万二到两万四人民币之间),这对我们这些留学生来说,风险太大,万一和房东闹了纠纷,这个押金就很难全部拿回来,要是因为一点小事闹上了法庭,更是没完没了。
曾经就有台湾同学,因为租住的房子厕所地板塌陷,被房东告到法院,要扣他们的全额押金。他们几个人在英国多留了十个月,准备各种文件、提供证据、等待开庭,一直没法离开,最后也还是赔了三分之一的押金才算了事。
“耽误多少事呀?十个月连小孩都生出来了。”白老师听说这事后,无比感慨。“别管中国还是英国,无论在哪里,打官司都不是好事,不到万不得已,千万别打官司!这是真理!一旦打起官司,就跟我们老家人说的'撂起块石头打天',你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有个结果!”
的确,万一出现这种麻烦,不得了,费财费力、没完没了。我们每天都要写作业、赶论文,去图书馆查资料,找老师和同学做讨论,还要上课,要自己考虑买菜做饭,弄一日三餐填肚子,怎么可能有时间和精力搞这些?所以找个陈先生这样的二房东,只要他不是太苛刻,其实还是省心省力的。
而张树碑的算法则是从他自己的某个角度考虑的,他认定了陈先生就是个二道贩子,投机倒把赚了他的血汗钱。张树碑每个月可以从政府拿到七百多英镑的外派访问津贴,如果陈先生肯少赚他一百英镑,他就可以多出一百英镑用来体验英国生活呀,比如,多去几次酒吧,多去几次伦敦,多尝尝意大利餐厅的饭菜,多打几个国际长途,攒上两个月还能到其他欧洲国家转转,至少去趟巴黎是绰绰有余……谁叫人家英镑抗花呢,算算,这一百来镑还真能干不少的事儿。
可是话又说回来,张树碑也是从网上查到的陈先生出租房子的信息,大家都是中国人,用中文交流,也相互信任,省了他很多麻烦,一个在中国云南,一个在英国牛津,隔着十万八千里,房子就在邮箱里你来我往地搞定了。陈先生还给他提供了很多有关在牛津生活的实用的信息,比如如何从伦敦希思罗机场坐车到牛津,比如牛津当地近来天气如何,穿些什么衣服合适,还需要带几件什么衣服,以及海德里道28号这座房子距离他经常要去的几个地方有多远,周边的交通路线,如何外出购物等等。
正是因为这个房子位置合适,房租与它附近的房子在网上晒出的价格相比还略低些,张树碑才很快抢下它,在电子邮件里和陈先生敲定了要租这个房间,并且用网上银行账户预付了一个月房租作为定金。
如果真是要正正规规地通过当地房屋出租中介,或者是排队申请学校某个校区的宿舍,那张树碑不知道要受多少罪,经历多少麻烦,花费多少时间才能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呢,即便找到了也不一定满意。可是通过陈先生就不一样了,陈先生不仅亲自到车站去接他,还帮他搬行李,甚至提前在家里准备了热面条,并且嘱咐其他房客都给刚来的人一点关心和方便,这也是这临时的家里的习惯。我给他准备了两份实用的最新地图,白老师专门炖了鸡汤等新来的室友,李若诗送给张树碑一个漂亮的手绘英格兰古堡花园图案的马克杯。看看,这多温馨呀!
但是张树碑像是铁了心要在这个“法治”国家里维护一把自己的“权利”。他专门跑到牛津市政厅去查了相关规定,又张罗着找大房东奥兹来家里和其他人开会。一旦张树碑和奥兹他们认真搞起来,陈先生倒真的有些理亏了。
奥兹一头天生的小卷发,小得大概只有平均尺寸的中国女人的小拇指勾起来那么大,专门烫都烫不了那么均匀。奥兹比黑人白,比黄种人黑,大胖脸,大肉腮,大鼻子,除了嘴巴又薄又小巧,再就是眼睛小得不合乎比例。这样的一张脸上,外面罩着一大圈深咖啡色的小卷发,小眼睛上又架上一副斯文无比的金丝边眼镜,跟人打招呼的时候至少脸上的表情绅士得不得了,这就是奥兹给我的印象:仿佛一个3D动画片里的绵羊,喝热朱古力的时候不小心埋进去了整个脑袋,抬起头,变成了浅巧克力色的脸和深巧克力色的头发。
第一次来“开会”,他就带着三个朋友,都是在当地开出租车的,长得人高马大,满脸横肉一个比一个壮。我放学回家一看到饭厅里坐着四条大汉,心里先吓了一大跳,一问才知原来是讨论换租房协议的,我就一声不响悄悄回到楼上自己房间了,白老师也不想和奥兹交流,李若诗黑白颠倒地做论文,除了吃饭和上厕所,连房间都不出,当时正在屋子里睡大觉。过了一个多小时,下楼喝水的时候,我悄悄走到厨房,侧身一看,餐厅里张树碑正在和奥兹认真地讨论什么,还在本子上记了些东西。我隐约看到,有的地方还使彩色荧光笔画了圈,大概属于重点商量的内容。
张树碑的多次咨询和投诉都得到了牛津市政厅住房管理和服务部门工作人员的热情接待与鼓励,也正因此,他回来后满怀信心,坚决主张我们全体房客与陈先生反目,与奥兹一伙儿去打官司。
白老师、何老师、李若诗和我商量了一下,还是决定先站在陈先生一边。因为陈先生只是钻了点小空子,并没有违反法律。白老师也打听了他实验室里的各国同事和朋友,了解到这种二房东在英国事实上是存在了很多年的,尤其是在牛津这种大学城里,根本不是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事情,也谈不上违法乱纪。市政厅和法院之所以一次又一次礼貌地接待张树碑他们,完全就是个工作流程。
“这就和我们国内有些地方依然会给市民甩冷脸子和翻白眼儿一样,就是个工作态度和习惯而已。并不能因为人家热情接待你,耐心听你说事儿就以为自己的理大过天了;同样的,在国内即便人家给你翻了白眼儿,甩了冷脸子,你也不能自暴自弃心灰意冷呀,一定要学会自己判断,有理就是有理,没有理就是没有理。”白老师喜欢辩证地谈问题,并且自己承认:哪怕就是扯皮呢,也喜欢用这种方式扯。
陈先生去了剑桥后,一直也没给我们打电话,白老师给他打电话他又不接听,无奈,白老师给他发了一封电子邮件,简单说了说事情的来龙去脉,让他“抽空回一次牛津,最好单独去和奥兹见一面,把事情处理了,好让大家安心学习和工作,不然小卷发的奥兹带着那几个将近一米九高的印巴大汉隔三差五到家里来晃悠,姑娘和若诗都不敢下楼喝水了。”但是陈先生两天后才看到邮件回了封信,可是就在这两天时间里,张树碑和奥兹接触得越来越深入,已经联手将诉状送到法院了。
陈先生得知消息慌忙从剑桥赶回来,正是个傍晚,他掏出钥匙开门,却怎么也打不开房子的大门,他蹲下、起身,站起来又蹲下,又起身,平视着看锁眼是不是堵住了,又仰头朝上观察锁眼,双手把住钥匙,左拧拧,右转转……可是折腾来折腾去还是打不开房门。
这时,我正好背着书包放学回来,从马斯丁路和海德里道交汇的拐角转过来,看到陈先生一直在忙活,我赶紧快步走近了,对他说:“别开了,陈先生,他们把锁给换了!我们每个人都配了一把新的大门钥匙!”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