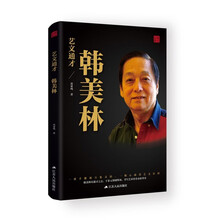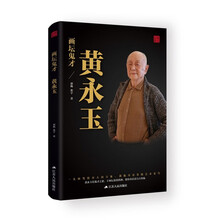“马赛曲”号去东京,抵香港,我们登陆,住九 龙。应邀访李流丹家, 他出示他的木刻作品,印象不错,表现了人民的苦难 。在饭店吃到了炒 菠菜,味美,在巴黎无炒蔬菜,只有生菜或菜泥。北 上,先到广州,无 亲切感,因听不懂广东话,如初到外国,反不如在巴 黎自由。乘火车去 北京报到,路经无锡,下车,宿店。店主见我持护照 ,西装革履,是外 国来的,悄悄问要不要姑娘,我摇头。他加一句:有 好的。翌晨搭去宜 兴的轮船,船经家乡码头楝树港,下船,走回家只一 华里,这是我少年 时代频频往返的老路,路边的树、草和稻,若是有情 当相抱。父亲和妻 竟没有来接,别人似乎也不相识,我默默回家。途中 见小田埂上远处一 矮小老人,夹两把雨伞前来,那确是我父亲。他说昨 天碧琴抱着可雨也 来接过,今天小雨未来,无电话,他们只知就这几天 到家,但不知确期, 今天听到轮船叫(鸣汽笛)才又赶来接接试试。他有点 遗憾昨天碧琴和 可雨没有接到我。转眼抵家,妻抱着三岁的可雨被弟 妹们围着,都站在 门前打谷场上冒着微雨等待远行人的归来。首先他们 让可雨给我抱,没 有见过面的孩子,他不怕生,高高兴兴投入我怀中。
因平时他们经常训 练他:爸爸呢?法不(法国)。我的归来对老父、老母 、妻及全家都是 极大的喜事,但我感觉到父母们心底有黑洞。
是夏天,妻穿着薄薄的衣裤,同一般农村少妇仿 佛,但她朴实中不 失自己的品位,委屈了她三年,她还是她,她不怨这 三年有多苦,似乎 站在流水中并未被打湿衣衫。纸包不住火,家里虽不 对我说,原来土改 降临,我们家被划为地主。十亩之家算地主?有说是 父亲当过吴氏宗祠 的会计,吴氏宗祠田多,但又不是我家的。我完全不 了解地主、富农、 贫农等等的界别及后果,只知家里粮食已不够吃,我 想将带回的不多美 元先买粮食,父亲连连摇手:千万买不得!夜晚,我 和妻相叙,她平静 地谈解放前后的情况,她因难产而到常州医院全身麻 醉用产钳的惊险, 家里经济的艰难,父母的可怜,土改的严峻……我们 相抱而哭,我暂未 谈塞纳河之溺及返国与否的矛盾。她倒说父亲主张我 暂不回来,我不禁 问:“那你呢?”“一切随你。”我只住了几天,便 匆匆赴京,报到要紧, 估计到了北京将可感受到在巴黎时听到进步派宣扬的 新中国新貌。
我是第一次到北京,故宫、老城、狭窄街道上华 丽的牌坊,这吻合 了我想象中的故国旧貌,所谓传统。街上行人如蚁, 一律青、灰衣衫, 与黄瓦红墙不属于同一个时代。教育部归国留学生接 待处设在西单旧刑 部街,我办完报到手续住下后,第一件事是到东安市 场买一套蓝布制服, 换下西装革履,才可自在地进人人群。
接待处的工作主要是联系分配留学生的工作岗位 ,等待分配期间安 排政治学习及政治报告。各行各业的留学生大都与其 本专业系统有联系, 有的很快就被聘走了,甚至几处抢。也有没处要的, 等久了的便分配到 革命大学学习,学习一年政治再看。我是打算回杭州 母校,刘开渠老师 在当院长,已有人开始为我与他联系,妻也曾表示她 愿定居杭州,风光 气候均宜人。离开巴黎时,有人托我带点东西给滑田 友,我找到大雅宝 胡同中央美术学院的宿舍滑田友家。不意在院中遇见 杭州老同学董希文, 他显得十分热情,邀我到他家小叙,问及巴黎艺坛种 种情况,最后提出 想到我招待所看我的作品,我很欢迎。好像只隔一两 天他真的去了旧刑 部街,我出示手头的一捆油画人体,他一幅幅看得很 仔细,说想借几幅 带回去细看后再送回,当然可以,就由他挑选了带走 。大约过了一星期 或十来天,他将画送回,并说中央美术学院已决定聘 我任教,叫我留在 北京,不必回杭州去。当时徐悲鸿任中央美术学院院 长,徐一味主张写实, 与林风眠兼容甚至偏爱西方现代艺术的观点水火不容 ,故杭州的学生也 与徐系的学生观点相悖。因之我对董希文说,徐悲鸿 怎能容纳我的观点 与作风?董答:老实告诉你,徐先生有政治地位,没 有政治质量,今天 是党掌握方针和政策,不再是个人当权独揽。董希文 一向慎重严谨,他 借我的画其实是拿到党委通过决定聘请后才送回的, 用心良苦,我就这 样进入了中央美术学院。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