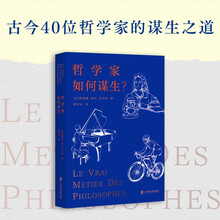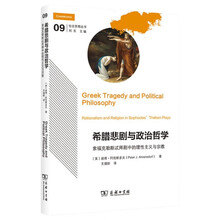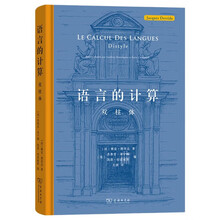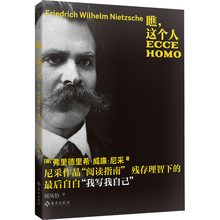《博丹论主权》:
知性是灵魂的国王,而国王的灵魂是一个和谐的共同体的中心。为了联结各种秩序,他的灵魂必须联结在其中。就正义而言,古典德性——智慧、勇气、节制——对灵魂和共同体的各部分来说都是必需之物。但比起正义,更需要和谐。领主式君主也许是公正的,所有政府都有可能正义地行动,但这种共同体却不完整。
完善灵魂和共同体的并非正义,甚至不是和谐,而是对正义与和谐的爱。一个爱着正义与和谐的人,必须关注这些爱,不仅以为它们比他自身伟大,也比正义与和谐本身伟大。最后,王权君主的“王权”具有神学的意义,而非古典的意义。信念、希望、仁慈作为德性,亦即灵魂的状态,完善并就此填充灵魂和共同体。它们不是政治的或理性的,而是在终极的意义上神圣的。它们将人类灵魂与联结宇宙的力量联系在一起。博丹的参考框架足以表明,在“一种确然可靠的关怀”的特殊意义上,这种力量就是爱。
因为爱既是关联性的也是完整的,所以爱能够包含。一般而言,仅仅有爱并不足够,王权君主制不可能依靠多愁善感的情怀而持存。这不过是博丹反对的“一个太善良的国王的单纯和过分的忍耐”。相反,这种爱伴随着一种确然可靠的关怀,还是其他德性的结果,这些德性就包括一种纯粹“智识的和沉思的”知性。爱有“其种属”;对于个体而言,爱是对构成共同体的“许多家庭”的爱;对于王权君主而言,爱是对臣民之爱(同上,页1)。这样,爱总是具体的。博丹赞同政治一哲学的传统主题,它教导我们以最大限度爱我们自己。对爱和关怀而言,存在一个必然的实践限制,这一限制指引爱和关怀,并把爱和关怀包含在内。实现这种实践关怀,可以令我们人类的存在变得完整,无论是作为家庭中的父母还是王权君主,二者的差别只在于包含得多还是少。
然而,就知性而言,一种被包含的、有限制的关怀,表明了某种超越关怀的东西。情况很可能是,只有王权君主才可能具有下述知性的类似物:这种知性不仅仅关乎对人类的关怀,也是一种关于一般的、普遍的关怀的知性。用博丹的话说,除非一个人以长期关怀最大多数的人为责任,否则,哪怕部分地理解“最强大的国王”那种强大的关怀都不可能。王权君主不会也无法爱所有人,至少不能平等地爱所有人。但在他的位置上,关怀不太具有个体的特征,其限制也相对较少。身为王权君主,君主不能为家庭或政党或阶级所限制;极有可能的情形是,在君主治下,人民的幸福与他征服、破坏邻邦并不是一致的。正是在他自己的位置上,王权君主开始理解将所有事物联结为一个统一的、善的整体的力量。就具有这种理解能力的知性而言,最主要的事情是,要充分认识到,即使王权君主在某种意义上是最高的、最好的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开始理解或拥有这种力量。质言之,在终极的意义上,是一种知性的关怀在包含[其他一切事物]。
拙文只是相当简略地展示了博丹的参照框架、王权君主制的中心位置,以及王权君主制中的“绝对主权”。没有王权君主制,绝对主权就不可能,因为绝对主权所必需的统一统治和行动自由就不会存在。在其他任何“国家”中,现实情况都是分裂和争斗;在这些国家中宣称统一,宣称绝对主权,说好听一点是虚构,说难听一点是明目张胆的谎言。论证主权者的兴趣似乎在于主张这些虚构和谎言,但这是鼠目寸光。越是主张绝对权力,就必须采取越多行动,但这些行动却揭示了绝对权力的缺失,并且强化了经验的分歧和分裂。这些行动总是使人衰弱,有时甚至是灾难性的,它们造成的伤害甚至超过对具体国家的实际损害:它们渐渐地、实质性地使国家成为不可信任的政治形式。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