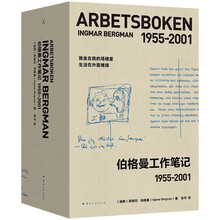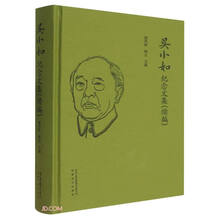《中国文史精品年度佳作(2014)》:
1924年,泰戈尔来华,梁漱溟向印度的大哲介绍儒学之ABC,对狂狷的意蕴加以自己的诠释自己的体悟,他告诉泰氏:“狂者志气很大,很豪放,不顾外面;狷者狷介,有所不为,对里面很认真;好像各趋一偏,一个左倾,一个右倾,两者相反,都不妥当。然而孔子却认为可以要得,因为中庸可能,则还是这个好。其所以可取处,即在各自其生命真处发出来,没有什么敷衍迁就。……狂狷虽偏,偏虽不好,然而真的就好。——这是孔孟学派的真精神真态度。”
好个真精神真态度,我们从这里人手是可以看出梁漱溟人生的真途径,由此来抵达先生的内在深处,这是最好的切口。
于是,我们就不难理解梁漱溟“吾曹不出如苍生何”的激扬文字;于是我们看到1942年,梁漱溟从沦陷的香港只身突围,一路惊险,别人都在为他的生命安危担忧,但梁本人却镇定自若非常自信,他说:我相信我的安危自有天命。今天的我将可能完成一非常重大的使命,而且没有第二人代得。从天命上说,有一个今天的我,真好不容易。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那是不可想象的,乃不会有的事!
而我,作为一个从乡村(从梁漱溟先生曾思考过实验过,流过泪有过忧思,多年拳拳挂念的曹州乡村)走出来的人来说,接触到梁漱溟这个名字,还是在少年时候的1977年,那还是“文革”的自然延续,街街巷巷还有很多的“文革”遗风。当小镇的集市上,狂热的人们敲锣打鼓庆祝《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发行的时候,正是麦子黄熟争分夺秒割下、父老劳碌的时分,我知道了梁先生,毛主席的文章白纸黑字印刷的:《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那里列举了梁漱溟的十五条罪状。真是气盛言宜,如惊涛裂岸,不容得你辨别不容得你呼吸。记得在初中曾学习《战国策·秦王使人谓安陵君》,上面有秦王发脾气:天子之怒,伏尸百万,流血千里。毛主席的震怒一点不亚于秦王。
作为小人物的唐雎说:“大王尝闻布衣之怒乎?”
秦王说:“布衣之怒,亦免冠徒跣,以头抢地尔。”
唐雎说:“此庸夫之怒也,非士之怒也。夫专诸之刺王僚也,彗星袭月;聂政之刺韩傀也,白虹贯日;要离之刺庆忌也,苍鹰击于殿上。此三子者,皆布衣之士也,怀怒未发,休寝降于天,与臣而将四矣。若士必怒,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缟素,今日是也。”秦王与唐雎的廷争与毛泽东和梁漱溟的争执是不好比附的,这两个人是朋友,都是以关注农民而走上了不同的拯救农民的道路,虽结局各异,但不能以成败论。在毛梁的这次争执中,我们看到:两个人的脾气都不小,也可见出雅量与水准,是棋逢对手,但不像在延安的窑洞里,毛泽东曾和梁漱溟彻夜长谈时候的争论,开国后的北京不是延安,就像毛泽东给柳亚子的诗: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
延安窑洞,当时共产党还算在野,而今是“三十一年还旧国”,毛泽东在1938年一见梁漱溟就说:“梁先生,我们早就见过面了。你还记不记得,民国七年在北京大学,那时你是大学讲师,我是小小图书管理员。你常来豆腐池胡同杨怀中(杨昌济)先生家串门,总是我替你开大门。”梁漱溟在1986年回忆说,在1938年与毛泽东延安长谈六次,其中两次通宵达旦,虽“相争不下,直至天明,谁也没有说服谁”,然而毛泽东“轻松自如,从容不迫。他不运气,不强辩,……明明是各不相让的争论,却使你心情舒坦,如老友交谈”。
民国七年的毛泽东是北大的图书管理员,当时毛泽东没有和梁漱溟争论的机会;1938年的延安窑洞,毛梁二人,虽争执,但颇愉快;而1953年的争执,毛泽东的语言如雷霆之怒,驾雷挟电。即使现在我们看《毛泽东选集》第五卷里的文字,很多地方也能见出当时的火药味:
梁漱溟先生是不是“有骨气的人”?他在和平谈判中演了什么角色?梁先生自称是“有骨气的人”,香港的反动报纸也说梁先生是大陆最有骨气的人。台湾的广播也对你大捧。你究竟有没有骨气?如果你是一个“有骨气的人”,那就把你的历史,过去怎样反共反人民,怎样用笔杆子杀人,跟韩复榘、张东荪、陈立夫、张群究竟是什么关系,向大家交待交待吗!他们都是你的密切朋友,我就没有这么多朋友。他们那样高兴你,骂我是“土匪”,称你是先生!我就怀疑,你这个人是哪一党哪一派!不仅我怀疑,还有许多人怀疑!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