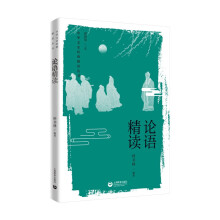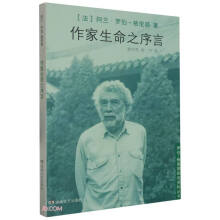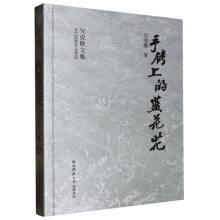也可以把南阳盆地看作碗,陶土大碗。碗内万物,如粥如水如美酒,端起来一饮而尽,就是春风秋雨,在众生嘴唇边浩荡或淅沥。盆地人民幽默,把家乡小名呼唤为“碗”——由此可见,三餐在日常生活中至高无上。农业发达,本地烧制的陶土大碗,迥阔于周边地区的青瓷小碗。男女老少肠胃功能劲健,餐馆与酒馆遍布古道旁、小桥边。喜怒哀乐悲恐惊,爱恨情仇怨别离,一概肇始于餐桌,了结于碗盏。
某日,一个掌握话语权的前朝文人,觉得把南阳小名称呼为“碗”,太粗俗,改称为“宛”吧。于是,南阳简称“宛”。从此,私塾里,小学课堂上,孩子们学习“宛然”“宛如”“宛转”这些词汇时,总觉得有大碗、巨阔盆地,在头顶隐隐浮动。
我曾利用三天时间,自北而南穿越南阳盆地。第一天,伏牛山。听樵夫高唱民歌:“再丑的妹妹也有人爱,破锅亲着破锅盖。只要妹妹对我情似海,你脸上的麻子也放光彩!”第二天,南召境内一座名叫“三棵树”的村庄。我对着一块巨石饮酒,蓦然发现石头上用粗拙雄浑的汉代刀法,凸凹起伏着鸟、仙女、太阳等图案。汉代石刻,记录南阳历史上最辉煌的一个时代,此刻溅上酒滴,是我无意间的祭奠?第三天,新野星空下,朗诵本地诗人岑参诗句:“强欲登高去,无人送酒来。遥怜故园菊,应傍战场开。”吟罢,看菊花正依偎商场怒放。
陶渊明《桃花源记》,写渔人“缘溪行”“复前行”“复行数十步”的探寻过程。渔人出桃花源,虽一路“处处志之”,以图重返桃花源,“遂迷,不复得路”。而后,“南阳刘子骥,高尚士也,闻之,欣然规往。未果,寻病终。后遂无问津者”。刘子骥是最后一个寻访桃花源的人。陶渊明把这个虚构的问津者,写成南阳人,真好。
只有一个南阳盆地里的人,才这样痴痴寻觅精神归宿地、灵魂理想国。
或许,在陶渊明的想象中,南阳就是高尚士子云集的地方吧。
反复穿过南阳盆地,乘车或步行。
手握一页地图,纸质粗糙,如同车窗外的原野。比例失真,一个县城往往被描画得大于一座群山或小于一条溪流,像梦境,有美感。地图上的名字,可与窗外闪现的路标对照:“黑鱼”,像诗人笔名。“树仁”,像儒雅敦厚书生的字、号。“前锋”,这座村庄多武士、足球健将?“马丢”,小镇的祖先大约因一匹马的丢失而痛悔终生?……地图是对本地的抽象。一系列地名背后,有无限的旧事前情,只可猜测而无法洞悉。旧汽车缓慢穿过地图和旷野,像老手指,尝试翻开一部秘史。
在小镇旅馆或一户农家,我用小刀把铅笔削尖,记录一天行踪和心得。铅笔秃了,再用小刀来削。书桌上就积累一小堆铅笔屑,类似于小动物蜕下的皮。铅笔越来越短,蜕下的皮越来越多。最后,一支铅笔,彻底消逝进一片文字里了。
与电脑、钢笔、毛笔相比,铅笔更适宜于随我穿过南阳盆地。尽管它在纸上行进速度很慢,但我懂得,窗外旷野上,那些热爱蜕皮的小动物,也在慢慢穿过夜色。铅笔,能与它们保持相似的步履和心跳。只有铅笔能越过文字的草丛,去触动盆地边缘的群山——
如果它们在深夜摇晃一下,敏感者就会醒来,想起爱恋过的人,身体中的剧痛和雷声,大作不息。
乡村大路两旁的白杨树,随地形蜿蜒起伏跑到大路尽头,就抱在一起,像热恋中的人。我背着行囊也向前跑去。我想听听大叶白杨们哗哗啦啦的风中情话,它们却手牵手向更远处跑去。远处,盆地边缘的群山,在风中微微晃动。强斌班承据丽
奔跑中,白杨树从少年、青年,进入中年、暮年?停步,我靠着最近处的一棵白杨树坐下——它就是跑到天边的那棵白杨树的童年?
P4-7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