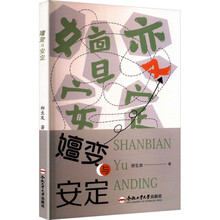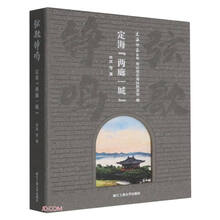一 芙烈达·卡萝的生死爱欲你没有地方放我的爱入晚,这屋子巨大得像是幽魅;白天的阳光全都消散无踪,在没有爱之下,她更觉得冷。
窗外的雾凝结,无消散迹象,她与疼痛一起躺下,就这么躺着,像是和着血块似的,瘫软又结硬,疼痛如兵,集体地在她的危脆肉屋敲打着,像是她画中永恒带刺的荆棘点缀着她周身处处。
直到晨光悠缓漫漫。
她手中的惠特曼诗集正落在诗句:“我溺爱的自己,有许多的我存在着,且都如此甜美动人。”公园的游乐园空无一人,那些大象、长颈鹿、溜滑梯或者猴子单杠都显得如此地寂寞:戴着假鼻子高帽子的小丑装魔术师无聊地自己玩着袖子,飞出一只鸟或者一条手巾,没有笑声的广场。
孩子们去哪了?她想也许都去教堂了,或者被大人关在家里。
这是什么世界?她渴望听见孩子的笑声,但什么也没听见,只听见自己的骨头发出疼痛的扯裂声。她失去一个孩子,距离她十五岁时在国立预校的礼堂看着她未来的丈夫迪亚哥·里维拉①创作壁画时,她发出的野心雄愿要为他生孩子竟过了这么多年了,时光流逝至她自己都觉得诧异:这几年自己是怎么度过的。
爱的花朵为何荒芜得如此迅速,她都还没仔细看好“爱”的样貌,爱就快速化成刺人心髓的痛。或许孩子可以是另一个等待她给予爱的美丽世界,于是她准备好不顾自己的身体有多么难以承受一个孩子的可能重量,她只知道唯有爱可以承接一切的际遇。
就在她准备留下孩子时,未成形的孩子却化为羽毛,轻飘离开了,仅以血色来告知他的离去。
她再次画下烙印的血痕,每一道血痕都几乎让她丧生——她不以阳光来歌咏生命,但她以阴暗来凸显阳光欢愉之稀有与必要。
她是以画面和意象来说故事的高手,她的画作充满了叙述的悲剧性与抒情性。但那抒情性的背后是别人难以了解的伤害。
迪亚哥不在现场,他泰半不在她需要他的生死现场。他热情他的功名事业胜过热情于他的女人,女人和欲望结合,欲望一旦被喂饱,女人就该自动消失。
自她二十岁嫁给他后,十多年来,她历经很多生死关头,很多杂芜荒诞人事,甚至也受邀去纽约有了很成功的画展,在三十几岁前,她学到的只是她一心一意想做好“迪亚哥的妻子”,她当时不要声名,也还没弄懂唯有拥抱艺术才能让自己更独立、更完整这件争。
创作是自我的凯旋,是漫漫长夜的依靠,这样全面性的感悟迟来,在她生命面临夜幕低垂时,她热情地拥抱创作,但上帝留给她的时日已然不多了。
她所处的时代于今看来是多么地风云,独立宣言、左派运动、欧战、世界大战爆发……她在纽约个展上吸引过“米罗紧紧拥抱我一下,康定斯基大力赞赏我的画、毕加索不断地恭贺我……”她写给友人伍尔夫的信里这样提到,这些人都曾和她交锋过,何其精彩的时代。此外,她的作品《框架》还被卢浮宫买下,她于是成了卢浮宫收藏的第一位拉丁美洲画家。
这些光环,都还不足以把她从不断陷进爱的流沙中拉拔出来。
所以即使声名大噪佳评如潮,或者后来她也真正拥抱了艺术,但终其一生她都离不开迪亚哥,没有任何事足以撼动她想要离开他,即使他不断外遇,且还搞上自己的妹妹,即使她自己面临流产的病房孤独与截肢苦痛……她都爱他,挺他,疼他。只是聪慧如她心里又怎不明白,她愈对他好,他就愈发远离自己。她知道他要性自由,他不愿腾出他的心房给她一个人独占,他的心房挤满了许多黏液,沾黏着无数的女人肉体。
无法离开永远比离开痛苦。说要比说不要难受。
(说:不要!多过瘾;要者,永远索取且姿态卑怜。)你没有地方放我的爱,或者你放我的爱的地方太小了。一我在她的生命现场内心呐喊。
也许芙烈达觉得我不该误解她心中伟大的巨人迪亚哥。因其一生都无法离开迪亚哥,不管聚或散,他们已是这孤单与丑陋世界的共同体。他们的组合有如生命树之根,也有如墨西哥那种带着某种奇异幻觉感的大喇喇色泽,他们走到哪都会刺人耳目。
终年日月穿着墨西哥那特湾传统服装的卡萝,在纽约竞被小孩们追着问:“马戏团什么时候到?!”美国妇女们想要学她的穿着,却穿得像是颗“包心菜”。
就是在墨西哥,卡萝也成为众人眼中的独特,因为即使是墨西哥女人也没有人天天把传统衣服披披挂挂在身上。
她需要长裙遮住她的缺陷小腿,但毋宁该说她需要这样的独特,否则她的生命将枯萎。生命够多折磨了,谁还能剥夺她装扮自己的小小乐趣呢。戒指戴满每一根指头,闪闪发亮的假钻石饰品缀满胸前,长发盘起如冶艳蛇蝎,两道连眉如鸟之黑翼。
她有多独特,就意味着她的内心有多痛苦。她有多华丽,就似乎隐藏着更多的爱之荒芜。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