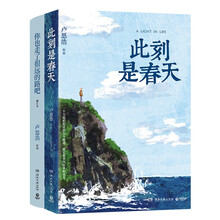“维京”的后代
在介绍现代北欧人之前,我们先看两段史书的记载。古代阿拉伯史学家伊本·法兰德在十世纪时这样描写瑞典人:
我见到了那些罗斯人(也就是瑞典人)携带着货物在伏尔加河上登岸,扎下了营地。我从没有见到过比他们更威严的人;他们身材高大,犹如棕榈树,脸色红润,头发煊红。他们所穿的,既不是短外衣,又不是长袖袍,但是男人都有一种粗糙的斗篷,披在一边,一只手伸在外面。每个男人都带着一柄手斧、一把小刀和一支宝剑,从来没有看见他们不带武器……女人胸前挂着一个小囊,质料或铁或铜,或金或银,照她丈夫的家产而定。
另一个时期较早的阿拉伯作家伊本·都斯塔的描写是这样子的:
他们既没有固定资产,又没有占领城镇或田地;他们唯一的职业就是从事黑貂、松鼠和其他各种兽皮的贸易,谁愿承购,他们就卖给谁。他们把交易所得的金钱收藏在腰带里。……他们勇猛英武。他们出去攻打别族人民的时候,非到把敌人完全歼灭决不罢休;他们把被征服者劫掠无遗,收为奴隶。他们身体结实,相貌堂堂,勇于袭击;不过他们的英勇精神并不表现在马背上,因为他们的一切充满战斗行为的事业都是在船只上进行的。
瑞典人、挪威人是海盗的后代,并以此为自豪,他们经常提到他们历史上的光荣时期,即“维京”时代。在瑞典大使馆宴请我们代表团的午餐会上,漂亮的、“相貌堂堂”的瑞典驻华使馆临时代办就向我们介绍说,他们在举杯祝酒时所说的“斯柯”(即“干杯”)原意却是“骷髅”,即死人的头骨的意思。“斯柯!”“斯柯!”我在北欧跟着说了不知多少遍。我们现在举着精致的高脚玻璃杯,那时的海盗们举着的却是死人头。当时的海盗们向西到法兰克帝国,向南到地中海,向东,经过伏尔加河、黑海直达阿拉伯。难以想象的是,那时他们就驾驶着我在奥斯陆的一所博物馆看到的像水瓢似的无顶船。驾驶着那种靠桨划动的木船远去万里征服四面八方,的确需要勇敢、有力与坚忍不拔的精神。
我在斯德哥尔摩,还看到一艘他们在一九六一年时打捞上来的远洋船——“瓦萨号”。这艘船建造于一六二五~一六二八年,现在修补完好,保持原样。使我惊奇的是,在船员舱里用蜡塑的蜡人,要比现代北欧人矮得多。如说蜡人不足为凭,不能证明当时北欧人的身高,那么那船员舱里的床是“有物为证”的了。船员的床是折叠式的,形状像抽屉,里面放着被褥,白天折起来收在舱壁上,晚上打开来,一个抽屉里颠倒着睡两个人。而抽屉的长度至多只有一米七。我问向导,向导也承认,当时的瑞典人一般只有一米七左右的高度。这就绝不像古书上说的什么“身材高大,犹如棕榈树”了。
现在的北欧人,除了我在挪威看到的一位曾在中国留过学的人因生理缺陷而驼了背之外,年轻人几乎都超过一米八。三百年来北欧人身材增高了十厘米。
在奥斯陆金狮饭店,我和文夫休息时总爱凭窗眺望街景。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是,所有的男女青年(有的还背着很重的滑雪行囊)急煎煎赶路的模样,那真可说是“健步如飞”。到奥斯陆的第一天,晚上一位记者赫根请我们去饭馆吃饭,走在路上,他不无自豪地说:“到挪威来的外国人都说,走在街上一看,就知道所有的挪威人都明白自己要去干什么。”我只好笑笑,对他说:“到我们中国的外国人走在街上一看就知道,时间是属于我们中国人的。我们有的是时间,所以总是不慌不忙。”
北欧人不但身材高大,并且漂亮,尤其是女人,一律是金发碧眼。北欧曾给好莱坞输送去不少演员,成为世界明星的英格丽·褒曼和嘉宝,就是瑞典人。在街上,我也没有看见过面带病容的人;他们爱好运动,爱好户外活动。如那位记者赫根,他说他来看我们之前,白天已经在山上滑了四十公里雪。而我只好打趣说:“我们比你还厉害,你来看我们之前,我们已经在天上飞了一万多公里。”
北欧人身材高大、健康、漂亮,同他们所处的气候条件和食物构成有关。北欧气候寒冷,但并不严酷。四月间,我们在纬度低得多的北京起飞,一天之间到了北欧也不用加衣服。漫步在濒临海边的奥斯陆街头,风凉而不刺骨。奥斯陆的海湾是不冻的,海水碧波涟漪,山上却盖满皑皑的积雪,蓝与白交相辉映。北欧人饮食的烹调在我们讲究“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中国人吃来真淡而无味,但多是鱼虾奶酪,营养价值极高。在瑞典陪同我们的霍尔小姐也认为,北欧人近百年来生活水平的提高,是北欧人身材增高的主要原因。可是霍尔小姐自己,吃饭却非常简单,她陪我们下餐馆的时候,总是大嚼生菜沙拉。所谓生菜沙拉,就是生卷心菜、生黄瓜、生西红柿上蘸点奶油凉拌一下。这道菜,我是敬谢不敏的。霍尔小姐老吃这种菜且能保持旺盛的精力,大概是如我们中国人常说的,“有底”了吧。
寒冷的气候锻炼了北欧人的体魄,同时也使北欧人的性格比较内向、朴实。霍尔小姐说:“要了解瑞典人就像倒西红柿酱一样困难。”我没有倒过西红柿酱,不知道其困难程度;我们在北欧的短促访问,也不可能把他们了解得很多。仅就所见所闻来说,三个国家的人民好像也不太相同。
挪威人生活比较简朴,并且讲究实际,说明白了,就是比较节约。三国对我们的接待,似以挪威为最差,但他们并不是有意慢待我们,确实是按他们生活的基准线定出的较高规格来招待的。在挪威四天,我们从来没有吃到过一道热菜,席间只有三明治而已。不过三明治里夹的是生鱼片和虾,不是火腿肉片。有一次吃饭,我对挪威笔会中心主席内塞女士说:“我们中国人连吃饭都体现了集体主义精神。我们是把一盘盘菜端上来,大家用筷子在一个盘子里夹着吃,不像你们这样分成一份份的用各自的盘子吃。”内塞女士说:“三十多年前,我们普通人民也是像你们中国人那样吃的:一家人围着一口锅,用勺子在里面舀汤喝,就着自己手里的面包。现在这种吃法,是近几十年来才普及的。”我脑海里马上浮现出苏联童话故事片《大萝卜》和高尔基的《我的童年》中的场景:中间一锅冒着热气的白菜汤,一群衣衫褴褛的孩子围着它,贪婪的一勺接着一勺的稀里哗啦地抢着。原来,他们摆脱贫穷并不久;他们还没有学会奢华。
在金钱往来上,西方人一般都划得非常清楚。我们中国人过去讲究在“政治上划清界限”,西方人可是一直在金钱上“划清界限”的。而挪威人,我看是到了滴水不漏的程度。到挪威的第三天,一位年轻的出版商与几位作家在豪华的派克饭店请我们吃饭(也只是冷餐而已)。饭后,按给我们规定的日程,我们应该前往奥斯陆大学东亚语系的教授何莫邪家。可是没有车来接,要我们自己雇出租车去。于是我们在出版商的汽车里只好向他借一百挪威克朗去雇车,讲好我们用美元换了挪威克朗后还他。他如数借给了我们,开车走了(他已经完成了他的接待任务)。等我们到何莫邪教授家吃完了晚饭要回金狮饭店时,又没钱了,又得向何莫邪教授借钱。这一天,我们向外国人做了两笔“贷款”。我私下里认为,区区一百克朗(约合十几元美金,三十元人民币),他们会慷慨解囊的。在中国,倘若有外国作家到我家吃饭,雇出租车送他们回宾馆,本来就是我分内的事,怎么能让外国客人自己付钱呢?殊不知,我们换了挪威克朗在第二天还他们的时候,他们毫不谦让地照收不误。
如果相信子英的介绍,那就有更多的笑话了。他说:在瑞典,假使你忽然烟瘾大发而又忘了带烟,要向旁边的人讨一支来抽,你也必须花钱。旁边那个人即使衣着华丽,他同样会毫不脸红地收下一支烟钱。不像在我们中国,在公共场合中你向别人讨一支烟抽,不管是谁都会给你的。在斯德哥尔摩大学的校舍里,十二个学生共用一个公共厨房。厨房是现代化的,照我们中国人的说法是非常“高级”。但那些很富裕的瑞典学生们相互之间连一撮盐、一块方糖也分得很明白。瑞典年轻人在谈恋爱的时候,男女上咖啡馆,去迪斯科舞厅,一人一半,各出百分之五十。要是请客,必须先说清楚谁请谁,如接受了别人的邀请,就应有回请,所谓“来而不往非礼也”。这和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四十年代好莱坞制造的义男淑女的神话差得很远了。
不但在婚前,在婚后,夫妻之间的经济也分得够仔细的。据子英说,那种“男主外,女主内”的古典式家庭结构,在西方已经很少见了。
下面,我们再把话扯回来。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