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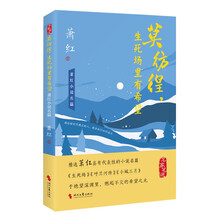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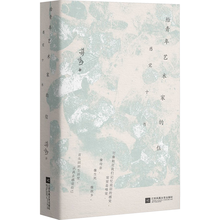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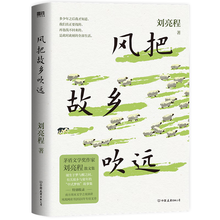
许知远曾将韩良露比作“江湖百晓生”——“早年闯荡文化江湖,到处逢场作戏,只为二三十年后可以说我在场、我知道、我记得的故事”。《文化寻味》以六十篇文艺、旅行、食趣、社会、记忆的精彩篇章,勾勒出了韩良露的“文化江湖”。对韩良露而言,世界仿佛一本百看不厌的生命之书。她热爱旅行,热爱拥抱异国美食与文化,勇于尝试,无惧于表达自己的个性、主张与态度。人到了中年以后,更像是有了万花筒般的视野,她不时地转动焦距,就看到了组合出的各种人生图像。
70年代,回头看见我
许知远说我像江湖百晓生,早年闯荡文化江湖,到处逢场作戏,只为二三十年后可以说,我在场、我知道、我记得的故事。
一、台南旧事
我喜欢台南那种缓慢的、懒散的、优闲的气息,潮湿的空气中飘浮着草木青味、黄昏时随着台南人上街漫无目的地散步,入夜后沉静的暗巷浮动着花香、夜访郡王祠深夜的阴森,晨探赤嵌楼黎明的苍茫。
我站在台南火车站月台上,等着南下的慢车从永康开来,载我去保安村,我并不是想赶时髦,去玩一趟永保安康的火车旅行游戏,而是想回忆一趟二十多年前的逃亡路线。
那一年,把青春日子过得像写坏了的《麦田里的守望者》的我,实在厌倦了在台北的生活,突发异想地要到远方去念书,当年还不流行高中生出国,我只好在全岛选一个可以转学的地方。
父母当然希望我选离台北近的地方,虽然他们一直没有明白为什么我非要离家求学,一向只有南部的孩子离乡背井到台北唸书,哪有北部的学生一个人去南部唸书的道理。但我那一对开通或宽容到不可思议的父母,对我的青春浪荡生活早已不知如何是好了,高一念中山女中时,旷课加请假记录破建校历史,高二转去了辞修高中,依然不改本色,还闹过一次笑话,在全校朝会时(那一天我还是不在,事后经同学转告),校长宣布高二上年度全校*名的奖学金得主韩良露,因请假加旷课太多,操行成绩只剩下了不到30分,因此被取消资格,当场引起全校哄堂大笑。
在台北其实也没什么压力的我,只是难耐那段想离家远远的冲动,想一个人过日子,想每天爱干什么就干什么,想不向任何人交代地体会孤独和寂寞。
*后我选定了台南,主要原因是因为我母系方面的亲人,虽然他们已经通通住在台北了,但台南对我一直有种神祕的牵引力量,长大后才明白当年我一定是听到了不明的、远古祖灵的召唤。父母说,考上了台南女中你就去吧!他们一定觉得我上不了,没想到两百多人考转学,只收了我一个人。
父母只好帮我租了房子,在府前路郡王祠旁的巷子里,两层楼的老式洋楼,屋主是在台电上班的高级职员,太太在家教钢琴,有一个正在唸私立长荣女中高三的女儿,这一户保守的人家,肯把房间租给外地学生,看上的是要唸台南女中的我,会对他正要考大学的女儿激起竞争鼓励的作用。
事情完全出乎他的预料,注册入台南女中高三后的我,*个星期摸清了学校有多少棵老榕树、受够了清晨朝会的团操,更受不了台南女中古怪的制服,更奇怪全班女同学为什么下课休息时都静悄悄的?
我又开始了逃学的日子,刚好认识了在台南美新处办画展的人,要我白天帮忙看画廊,反正是义工,我有空去时,就到图书馆借英文小说,画展看烦时,还可以丢下整屋的画,到门口的冰果室吃西红柿沾糖姜酱油和水果冰。
我旷课了一个月,认识了一些斯文秀气的台南男孩,一起骑单车去南鲲鯓,看还没开过画展只是传奇老人的洪通,一起在台南孔庙的大榕树下交换阅读彼此写的现代诗,这些男生都跟我的外公、大舅一样,会一种很柔软的台南腔及闽南话。很多年后,我去了京都及苏州,才了解到什么是古都人的声音。
旷课一个月后,学校开始查问了,我索性瞒着台北的家人,也骗了学校的教务主任说我水土不服,干脆办了休学,当时,我已经舍不得离开台南了。我慢慢地溶入了台南的古老灵魂之中,明白了台南人的压抑、保留、淡漠、守旧的外表下,潜藏着狂热、执着和骄傲。
休学了三个月后,父母终于发现了我的祕密,宣布要来带我回家。当夜,我四处联络台南的友人,凌晨带着行李偷偷离开租屋处,只惊动了客厅中正在打瞌睡的大狗。清晨,我从台南火车站搭上慢车,直赴保安村友人父亲的铁路宿舍落脚。父亲运气好,竟然等到了不知情的友人去找我,东打听西打听下,知道了我在保安村的藏匿之处。那一天晚上,父亲领我从保安村回台南,却遇上台南全市大停电。一个城市会为一个人的逃亡终结而停电吗?
二、人生撞球台
整个人生像一场无止尽的撞球,大家撞来撞去,但都在一个撞球台上,有的球早撞到,有的球晚撞到,但也有的球一撞离了台子没了音讯。
高一高二都在台北逃学四处混,别人也许以为我在混太妹,但如今回头一看,就像那句广告词说的,“学琴的孩子不会变坏”,我大概也可说成“爱文艺的少女不会变坏”。虽然不走正轨,却一直走正道,许多日子和男友逃学在西门町的“天琴厅”;也抽菸,奇怪的是抽了两三年后就自动不想抽了,大概是没吸进肺里,也喝未满十八岁的自由古巴鸡尾酒,但至今不酗酒;在天琴厅认识了一些办现代画会、剧场杂志的人,也开始去牯岭街找禁书看,看老舍、鲁迅、巴金、曹禺,还去记忆中小小的位于二楼的帕米尔书店买书,不知为何地深受克鲁泡特金的《面包与自由》一书的吸引。
年轻的我,并不了解人生有如长河,随时会遇到生命河道转弯的时候,后来我的人生的确波澜起伏,也转过几次人生的大弯,但有些核心的情感却始终如伏流。
高三*终又逃回了台北,准备考大学,补习班也没去,常常去的是罗斯福路台大校门旁的香草山书屋,当时罗智成、杨泽都还在那做书店工读生,当时看了不少法国作家的书,纪德的《背德者》、波特莱尔的《巴黎的忧郁》,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也认识了一批在编《影响》杂志的人,当时会去一个叫谢正观的人家里聚会,还曾见到但汉章,因为《影响》的影响,我开始去西门町的台映看艺术电影,也促成了我在大一升大二的暑假,竟然就一个人办起夏日艺术影展,每天从上午10点放电影到晚上10点,一天放五至六部当时一般人看不到的电影。当时我手上有个小电话本,记录了台北各大专院校的艺术电影同好者的电话,一通电话随时可以招来数名至十数名的影客。在没有网络的时代,我也不知自己如何掌握了当时的动员能量,这样的能量日后我都不曾用在任何政治或商业领域,直到近几年在南村落举办文化活动时才重新启动。
小电话本后来在我搬家时遗失了,真可惜,否则还看得到不少人的老电话号码。我常说我如今认识的一半的艺文界人士的名字都记在那小本里,但其实大多数人当时我也不熟,反而在日后的二三十年间逐渐和其中不少人变熟。说来也怪,我和许多男人的江湖交情都是在三十多岁以后才能熟(例如倪重华、罗智成、杨泽等),为什么?也许是我对偶像型、才子型的男人有先天的抗拒,不想成为仰慕他们的女生,因此要保持距离,直到彼此可以自在平等相处。
推荐序
做什么,像什么 严长寿
一剑干将,一剑莫邪 陈浩
自序 小露台私语
辑一美和文化是我们的命运
辑二不只是流动的飨宴
辑三思索时感觉到地球转动
辑四七十年代,回头看见我
美食只是良露生活中的一个方面。她是个美感与见识兼具的生活家、文化人,非典型知识分子;她的观察力不凡,永远能看到事情的一体多面,从而把知识转化为智慧;她的感官敏锐,集各种品味于一身。
——公益平台文化基金会董事长严长寿
这又是韩良露让我惊奇之处,我深知她写文学艺术电影的能耐,而连房屋税都可以谈得头头是道,不免超出一般人太多了。但回想那些年她投入江湖,在电视台打工为父还债的历练,这投资理财的实用知识,她可是实打实地磨砺得来的。那日聊天,她谈起我东家近两年的股价起落,如数家珍。我学会了一件事,那就是永远不要对韩良露让你惊奇的本领感到惊奇。话说得远了,《文化寻味》展示了韩良露擅长论述的内功,文字的魅力丝毫不减。
——云广科技总经理、资深媒体人陈浩
过去九年间,我在工作及写作的“主屋”里,虽然做了不少自以为任重道远的推广饮食文化与城市文化的事,但在创作上,我仍需要有爱写什么就写什么的自由,完全不必在乎自己的专业是什么;只要是我真的关心也非想不可的事,我都像在小露台上想世界的事情般,写下关于世界的种种。于是就有了这本内容十分多元,姑且称之为《文化小露台》的书了。
——韩良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