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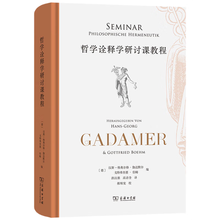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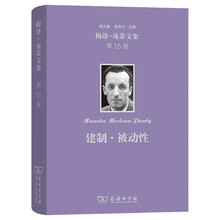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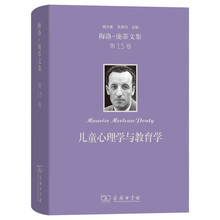



美国立宪所确立的作为“新政治秩序”的共和政制,在一定程度上既是现代的,又是古典的。
美国共和政制是现代的,因为美国政制的建构遵循了现代政治的基本逻辑,分享了现代政治的基本目标。以美国政制为代表的现代共和政制之所以有别于古典共和政制,是因为它建立在“自然权利论”而非“自然正当论” 的基础之上,以“个人权利”而非“共同善”为根本目标。当然,也可以说,它把“自然权利”视为“自然正当”,认为“个人权利”促生“共同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美国共和政制的思想基础是现代自由主义,而美国共和政制本身是以“人生而平等”——人人享有平等的天赋权利——为基础的自由民主政制。
美国共和政制是古典的,因为美国政制的建构运用了古典政治的实践理性,显示了古典政治的立法智慧。以美国政制为代表的现代共和政制虽然是自由民主政制,但又不止于自由主义民主政制。现代共和主义以现代自由主义为基础,但其内涵比现代自由主义丰富多了;现代共和政制固然是自由民主政制,但其内涵也比自由民主政制丰富多了。
美国政制不仅是民主政制,还是有限的民主政制,亦即对“民主”施加了一定限制、在一定程度上打了折扣的民主政制。其目的主要就是为了防止民主的暴政与集体的专制,以保护个人的权利与自由,实现包括每个人、特别是少数个人在内的所有人的真正平等,而非仅仅局限于多数人的平等。为此,美国政制变直接民主制为间接民主制,以代议制这一崭新的现代发明为手段,由选举产生的人民代表代表人民进行统治。故而,它既是以“人民的同意”为基础的民主政制,但所实行的统治却又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民主“自治”,而是有限意义上的民主“自治”。
因此,进而可以说,美国政制不仅是自由政制,还是有限的自由政制,亦即对“自由”施加了一定限制、在一定程度上打了折扣的自由政制。当然,与其说是美国立法者对“自由”施加了限制,不如说“自由”本身在客观上就存有一定的限度。“自治”是“自由”的最集中体现,也是对“自由”的最高表达。但由于人与人的差异,特别是大多数人热衷于个人自由而非政治自由,热衷于个人利益而非公共利益,所以完全意义上的“自治”不可能真正实现。而完全意义上的“自由”,亦即完全出于个人意志、绝对不受外界限制的个人自由,所导致的结果肯定不是自治,而是其反面——混乱。由于政治自由、特别是“自治”只能在有限意义上实现,而个人自由、特别是无视一切权威的“自由”绝不能任其泛滥,所以“自由政制”不仅在理论上是有限的,在实践上也必须受到一定限制。
对民主的限制,是为了自由,为了让人们平等地享有自由;对自由的限制,又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保障自由本身的安全,为了让人们长久地享有自由。正是为了让人们长享“自由之赐福”,美国政制还有进一步的突破。
美国政制不仅超越了简单意义上的“民主政制”和“自由政制”,还超越了“共和政制”本身。或不如说,正是作为有限的自由民主政制,美国共和政制在本质上要求超越自我,把非共和政制的因素纳入共和政制的架构之内,成为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新共和政制。
和现代政治扬“权利”、抑“权力”的基本旨趣一样,美国政制也保持了对政治权力的怀疑,并通过制度上的精妙设计来防范政治权力对个人权利的侵犯。其中最典型、最著名的就是以三权分立为基础的分权制衡机制。然而,美国立宪的初衷与直接目标,不是限制政府的权力,而是赋予政府以有效的权力。美国立法者看到,权力过于受限或者根本就无权的政府只能是无能政府,这样的政府若说以人民的自由和权利为目标只能是空谈。面对内部和外部的深刻危机,它甚至连自身的安全都无以保证,更何谈保障人民的自由和权利?所以,美国立法者明确指出,一个优良的政府必然是一个有效的政府。它必须能够有效地管理自身所需管理的事务,特别在某些关键时刻,它必须能够有效地解决突发难题与内外困境,而就根本而言,它必须能够有效地保障国家与公民的安全,确保人民所享有的权利与自由的真正实现。
美国立法者并不是要否定共和主义及其所追求的政治目标,而是认为仅仅有共和主义的热情是不够的。如果在政治生活中严格地遵循纯粹的共和主义理念行事,那么在各种不可预测的必然性因素面前,共和政制很容易就会陷于被破坏、被毁灭的命运。因此,共和政制要想维持自身的安全与持久,就不能无视那些必然性因素的影响,必须把能够有效应对那些必然性因素的手段与措施纳入制度设计之中。在美国共和政制具有非共和色彩的制度设计中,最主要的就是具有“民选君主制”意味的总统制。总统因应政治形势所具有的自由裁量权使其能够灵活而有效地应对紧迫情况下的一时之需,必要的时候甚至可以越过宪法行事。不过,在一般情况下,总统必须严格按照制度的规定行使自己的权力,本色还是共和政制下的总统。甚至总统自身的超制度行为,也是出于制度自身的规定。
为了确保共和政制的安全,为了保障公民权利与自由的实现,政府必须是一个掌握必要大权的有效政府。此外,政府还应该是一个能够恪尽职守的责任政府。这就要求政府的工作人员,亦即代表人民——名义上的统治者——行使政治权力的实际统治者,应该是拥有德性、才能与智慧的人。选举,其目的本身也就是在人民之中挑出较为优秀的人来。美国立法者一方面看到了人性中的恶,所以赞同权力需要受限制的看法,但是另一方面,美国立法者也没有忽略人性中的善,特别是少数有志于献身公共利益的卓越之士所显现的光辉,因此设计出更为通畅的制度渠道,为他们进入政府提供机会与便利。分权制衡机制一方面固然是为了让政府各部门互相牵制,以对政府权力起到防范与约束的作用,但另一方面也是变相地鼓励政府各部门的竞争,使真正能够更好地行使权力、担起责任来的人脱颖而出。美国政制所立基的共和主义自由,不仅需要德性,并且它自身就是培养德性的土壤。
总之,美国立法者在建构政制时保持着清明的政治理性,表现出卓越的政治智慧。他们虽然为美国政制选择了全然不同于古代政治的现代目标,但同时采用了更具包容性与灵活性的制度设计,力图创建一个真正能够有效地担负起政治责任、管理好政治事务、确保政治目标实现的全国性政府。在理论上,他们把“自治”奉为最高目标;但在实际上,他们明白“自治”所具有的限度。
……
任何制度之所以能够长期屹立不倒,并不是因为制度背后的权力有多大,而是因为制度背后的精神是深入人心的。没有制度精神的建构,制度形态的建构不论多么完美都是没有根基的。
——林尚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