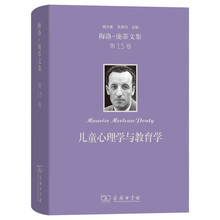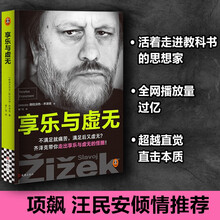无物,因为生活最终不是靠城邦来过,而是要靠每个人来过;城邦不是有目的、有意图的动物。与此相应,如果政治秩序的目的在于邦民的幸福,那么,从某种意义上讲,公共领域永远要为个人领域负责。没有一种对不同于公平分配的善的理解,就不可能有正义,也不可能有对诸善的公平分配。如果德性就是正义,那么德性只不过是美好愿望,它想要做正确的事,却完全不知道正确的事的内容。假设有必要为保卫城邦而牺牲某人的家庭。如果此人对家庭并没有强烈的忠诚,那么这就谈不上牺牲,更谈不上高贵。因此,做一个真正的好邦民的前提条件是不把自己完全奉献给城邦。那么,最好的政制中的好邦民的特征——奉献——究竟是什么?对于他所奉献的城邦的定义性原则,他应该如何理解?
亚里士多德在卷四讨论农民的民主制与手艺人的民主制。作为城邦居民,手艺人对城邦的依赖不断增长,并且相应地以牺牲个人领域为代价。农民则不同,他们在家劳作,对他们来说参与政治是种奢侈,而手艺人能够经常参与[68]邦民大会。像当代每天乘车上下班的人一样,手艺人变得部分地脱离于家庭。手艺人更像是卷三中组成城邦的个人,而非卷一中组成城邦的家庭的成员。农民作为纯粹邦民的程度低于受益人,然而悖谬的是,恰恰由于农民不完全投入公共领域,农民成为更好的邦民。由此,卷三提出的好人与好邦民的关系问题,在卷四得到回答:在好政制中,好人与好邦民是一回事,只要好政制有意地不完善——不是“最好”的政制。政治生活大体上总有缺陷,要让好人等于好邦民,除非让他生活在要求人并不完全奉献给它的政制中。那样一来,好人不会完全投入生活于其中的任何城邦。最好的城邦要求这种情况;次好的城邦则于这种情况相称。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