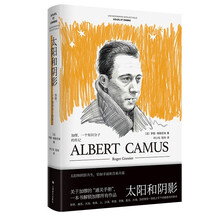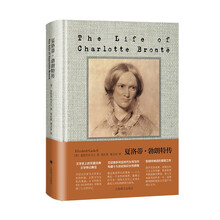在政治激情的半睡眠状态得到的短暂休息中,文坛的庆祝活动有几天刚刚占据了整个法国。夏多布里昂的故乡圣马洛在一个小广场上给它光荣的儿子竖立了一座塑像,这座塑像正好面对作家于1768年9月4日出生的房子。这场庆祝活动将《基督教真谛》的作者崇高的形象重新置于人们的记忆里;这个形象仅仅经历了二十七年的流逝,就已经暗淡无光了。必须经过议会休假,论坛偃旗息鼓,各党派休战,圣马洛的庆祝活动才会这样在全国的四面八方引起回响。
这个城市等待了二十七年才清偿了它的欠债。必须说,夏多布里昂在他的灵床上只要求他的同乡给他一个坟墓,他的高傲所梦想的坟墓,要求一块墓石和一个花岗岩十字架,置于“大贝”岛的礁石顶上,面对大洋。他长眠在那里,长眠在他一生挨过的那种孤独烦恼中,有如按他的身材缝制的一件呢服。他把虚荣心扩展到禁止别人在碑石上刻上名字。他是岩礁本身,这块巨大的岩石向风暴挑战,永远是黑色的,在暴风雨中是胜利者。这具有壮美的效果,一个有着伟人感觉的头脑做出了这种盘算。因此,我设想,如果夏多布里昂能够被征求意见,他是会拒绝竖立塑像的。但是,圣马洛被虔敬和动人的情感所引导。而他的可怜的、小小的青铜像仿佛被“大贝”岛的巨大岩石压垮了,这座塑像的构想与死者梦想面对无限以获得不朽的豪迈态度相比是多么平庸啊!夏多布里昂曾经是一个出色的导演。也许人们本不该去触动他死前安排好的特殊荣誉。
糟糕的是,圣马洛并没有安放这样一座塑像的位置。必须了解这个条件严酷的城市,它似乎开凿在岩石中,夹在两堵悬崖之间。它安置在那里,仿佛在一道非常狭窄的裂缝深处,挂在海洋之上,海洋以永恒的波涛拍打着它,却没有损伤它。它地方很小,挤在厚壁中间,小巷纵横交错,一直通到围墙。它有三条岩石带,却没有一条散步的道路,没有一片相邻的、灰色的、封闭的田野,就像一座城堡那样。这是一座以骁勇闻名的战争城池,说到青铜铸件,它只给大炮以位置。因此,要涉及给夏多布里昂的塑像选择一个场地时,圣马洛人就十分尴尬了。人们不得不把它放在城市唯一的十字路口。最后使市政府下定决心的是,作家出生的那幢房子如今已被改造成旅馆,就撇在那里。七棵瘦弱的梧桐树封住塑像,旁边的房子压抑着它,以致它好似待在井底。再者,令人气恼的是,把它置于一左一右两个池塘中间,这是退休的小店主在万塞纳或者阿斯尼埃尔的别墅中让人挖掘的那种可笑的池塘。夏多布里昂有了这样的陪伴,看起来像一个摆锤,夹在两只绕金属丝的玻璃烛台中间。多么可怜巴巴的夏多布里昂啊!青铜塑像的作者艾美·米莱先生自然不得不凑合这个框架的比例。因此,他制作了一尊小型的夏多布里昂像,形象极其平庸,令人发笑。作家坐在一大块岩石上,一只肘子支在一册《基督教真谛》上,手托住额头;而另一只手拿着一支笔,仿佛准备写作。脸稍微转向天空。这是正在遐想和等待灵感到来的夏多布里昂。我承认,就我而言,我感到这个作品完全令人不快。我不能想象夏多布里昂不是站着的模样。他应该站着写作,这个文体的巧匠,他的句子带着翅膀扇动幅度很大的声音凌空而起。再说,这个作家坐在岩石上,手中拿着笔,眼睛望着云彩,这是多么小市民气的创作啊,多么像行吟诗人的姿态啊!处在情歌的氛围中,这是不错的,可是在现实中,作家是以另一种方式写作的。我确实相信,把米莱先生的青铜像缩小了,放在有些多愁善感的老夫人的壁炉上,会获得青睐。啊!但愿这个大散文家处在“大贝”岛的尖端上,在自由的空气中,俯瞰着天际,保持骄傲和死亡的严峻线条,具有另一种洒脱!
官方的荣耀不可避免地具有一种庸俗的排场,尤其关系到向一个文坛王子致意。圣马洛市肯定所费不赀,给自己添了无穷的麻烦,才终于想象出组织一些庆祝活动,就郊区节日的范围来说形式有所不同。至少必须在夏多布里昂的塑像脚下,有一个我们的名人,一个杰出的作家,以法国文学界的名义向他致敬。在我看来,唯有维克多·雨果今日才有相应的资格同他面对面说话。但是,圣马洛的市政府根本没有想到邀请这位著名诗人——他不该是个共和派,而且可能发表危险的言论。市政府只限于发出一些我可以称之为官方的邀请,因此,有三位院士:卡米尔·杜塞先生、卡罗先生和德·诺阿依先生受到邀请,他们的职责是代表法国文学界来到圣马洛。卡米尔·杜塞先生和卡罗先生现今是科学院办公室成员;德·诺阿依先生是继承夏多布里昂的席位的那个院士;至于保尔·费瓦尔先生,他像《勒内》的作者一样是布列塔尼人,当下他主持文学家协会:只因有这些称号,人们选择了这些先生,而不是别人。再说,并非是选择的,而是不得不接受。必须说的是,在这件事中,文学不是微不足道。卡米尔·杜塞先生拥有和蔼可亲的声誉,他的全部家当是几部作为诗歌爱好者写的喜剧,获得过令人敬重的成功。卡罗先生是一个思想正统的、有教养的哲学家,小型号的库赞,一个平淡的、甜蜜蜜的作家,他板板正正的格调获得了成功。德·诺阿依先生是一个公爵,如此而已。末了,保尔·费瓦尔先生是四个人中唯一真正的文学家,在三十年中日复一日地写作连载小说,却没有任何严肃风格的品质。要是国外有人以为这几位先生就是我们当代名人组成的神圣军团,我会感到遗憾。我断言,在这些侏儒旁边,我们有一些巨人。必须知道,在法国,伟人是受到怀疑的。在公共的庄严场合,权威人士要穿上制服参加,但从来不让给国家增光的伟大天才发表讲话。官方不起眼的角色讲话就足够了,他们当然属于庆祝活动的次要角色,尽管他们有头衔,衣履挺括。
因此,圣马洛的庆祝活动具有寒碜的特点,夏多布里昂的巨大身影不得不忍受着“寒碜”的压抑。但庆祝活动的程序却很复杂。中午,所有的宾客要么穿着官方的制服,要么穿着黑色服装,从市政厅列队前往大教堂,在那里举行纪念弥撒。队伍从那里再前往夏多布里昂广场,广场上挤满了密集的人群。田野里敲响铜鼓,港口的大炮发出轰鸣。突然,盖住塑像的幕布在观众的掌声中滑落下来。这类庄严活动一成不变的仪式就是这样的。然后是接二连三的讲话。各种各样的人发言:有官员、代表、普通的宾客,不要忘了那三个院士和那个文学家协会主席。这是些可怜的讲话,用的是现成的句子,如雨般的话语在灿烂的阳光下震耳欲聋,声音单调。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