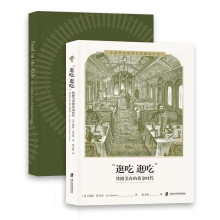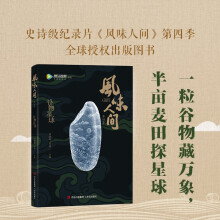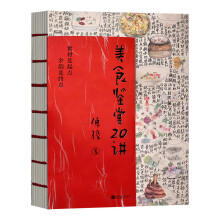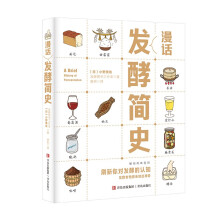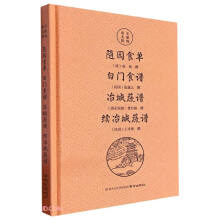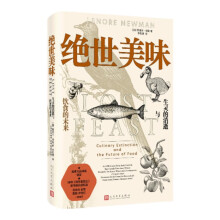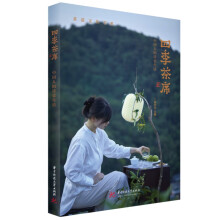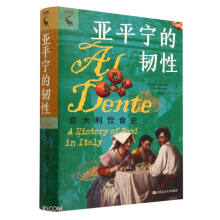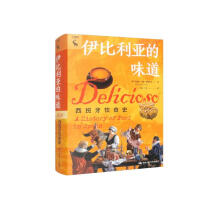《中国饮食文化史(黄河下游地区卷)》:
一月:“正月之旦,是谓正日。躬率妻孥,洁祀祖祢……及祀日,进酒降神毕,乃家宝尊,无小无女……,各上椒酒于其家长,称觞举寿,欣欣如也。”正月初一是最为重要的祭祀日,由家长带领妻儿老小,向祖先进酒降神。此后,全家无论尊卑和男女老少,都要列次序坐在最高辈长者面前,然后由晚辈们分别依次向长辈敬献椒柏酒,举杯敬祝长辈吉祥长寿,全家其乐融融。其中,正月元旦日敬献椒柏酒,花椒象征着玉衡星精,祝长辈和祖辈长寿。
二月:“祀太社之日,荐韭卵于祖祢。前期齐、馔、扫涤,如正祀焉。其夕又案冢薄馔饲具,厥明于冢上荐之……”二月在农村的太社按日子进行祭祀,应劭《风俗通义》卷八中说:“社者,土地之主,土地广博,不可遍敬,故封土以为社而祀之,报功也。”后世的土地庙,就是当时的“里社”,前称“里社”“祀太社之日”(后世称的“社日”,即是立春后在二月内的第五个戊日,为春社),向祖先献祭鸡蛋、韭菜,提前准备祀馔。当日晚上,又在祖坟前列供桌上供,第二天天明去坟上祭祀,如果这一天不是祭祖的好日子,或有其他急事,则可以请巫师另选日上坟祭祖。
三月:“是月也,冬谷或尽,椹麦未熟,乃顺阳布德,振瞻匮令,务先九族,自亲者始。无或蕴财,忍人之穷。”在《四民月令》中,作者劝人积德行善,这个月份正是秋冬积存的粮食可能快要吃完,而桑椹和冬麦尚未成熟之际,粮贮多的人应当多以仁德之心去怜恤缺粮受饥之人。先关照本家的九族亲戚,由亲缘近者开始帮助缺粮人家。不要为了自己家积攒钱粮,而忍心看别人受穷挨饿。反映了那时春荒造成农历二三月挨饿是普遍的事。同时也说明由于本地区广种桑树,每年“桑椹红”正是穷人春粮尽之日,桑椹正可疗饥救急,由此可见一斑。
四月:“是月也,可作枣精,以御宾客。”
汉代黄河下游地区桑蚕为农家重要副业。每年桑蚕吐丝做茧、缫丝之后,农家都有大量的弃蛹,可知汉代蚕蛹可能早已成为普遍的季节性农家副产佳肴。在《齐民要术》卷三《杂说》篇中引《四民月令》四月篇,其原文作:“是月也,可作弃蛹,以御宾客。”但校释作者在注释中说:“弃蛹”应是“枣精”的误写,并因此将《四民月令校释》乃至转引《四民月令》的《齐民要术》相应处均作如是改动。但笔者以为此处改动有误,其理由有五点:
其一,《四民月令》四月篇中指出:四月“蚕入簇,茧既入簇,趣缫剖绵”,说明农历四月正值切开蚕茧取得蚕丝的加工季节,养蚕人家必然都会获得大量的蚕蛹,崔窘将其称之为“弃蛹”,是比之于蚕茧壳为缫丝的原料——主要的收获目的而言是恰当的,但是蚕蛹毕竟是大量的副产可食之物。况且味美可食,如何能任意弃之呢?
其二,蚕农人家,多在农村,家境多不宽裕,未必在平时招待得起许多宾客,所以,一旦当自己养蚕而获得许多蚕蛹又一时吃不完时,而这个季节蚕蛹又易于腐败(当时可能尚未掌握腌渍制作方法),或因缫丝工作忙而无暇顾及,于是就会去请一些友人亲戚来,饱餐一顿烹调鲜美的蚕蛹,并同时表示感谢友邻们平时对于自己家事的帮助之情,这种举动,于古于今均在情理中。既然写入《四民月令》,就说明养蚕户的这种应季饮食活动,在当时已经形成了一种食俗。
其三,当时的广大农民限于家计,平时多以粮菜为餐,在他们日常饮食结构中,动物类食品所占比例极少,蚕蛹虽然不算高贵食品,但是其中富含蛋白质和脂肪,经过烹调,毕竟比菜粥美味得多,用以“御宾客”也是说得过去的菜肴。时至今日,在黄河下游地区各地,蚕蛹在酒席上仍然很受欢迎。试想在食物并不十分充足的两千年之前,农民是绝对不会将蚕蛹轻易地抛弃而不食用的。
其四,该书校释者认为御宾客用“弃蛹”似乎不妥,而将“弃蛹”改为“枣精”,笔者认为缺少根据又不符合情理。因为在农历四月,黄河中下游地区已值初夏,是各种菜蔬均很丰富的季节,招待宾客时却要摆上“熟的米屑掺有干枣泥”的“枣糟”冲熟成粥来招待客人,确实不合时宜。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