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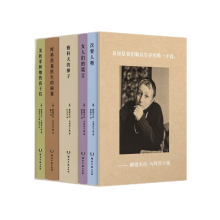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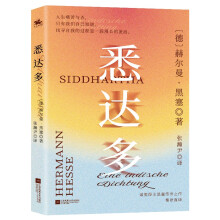
1.卡夫卡之后的荒诞天才,莫言、余华极为推崇!
2.魔幻现实主义小说开山之作,深刻影响马尔克斯《百年孤独》!
3.新增9927字内容导读,收录作者珍贵图片,2000多字生平。
4.被苏联勒令在作者布尔加科夫生前不得发表,世界文学史上被禁30年的奇书!直到1987年,中文首版才面世。
5.俄国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却通俗易懂,毫无尖酸晦涩,故事性强,读到停不下来!
6.布尔加科夫的作品解禁50多年,影响了整整一代人——马尔克斯、莫言、余华、格非、苏童等作家真心喜爱。
7.一边打压禁止,一边深夜捧读。他是斯大林心中又爱又怕的文学家,苏联zui危险的舆论武器!
8.被埋没的俄罗斯文学巨星,自称俄罗斯文学原野上“唯一的一匹文学饿狼”。
9.俄罗斯文学资深翻译家徐昌翰经典译本,俄中完整直译,忠于原作,一本无愧于读者的匠心译作。
10.战斗民族民众实力打call,票选“心目中喜爱的小说”No.1,本土支持率远超《战争与和平》和《罪与罚》。
11.全球读者心目中的“口碑神作”,共53个语种,690个版本。
12.《大师和玛格丽特》把历史传奇、神秘幻想和现实生活糅合起来,一场跨越时空的狂欢,上帝与魔鬼交错登场。一幅包罗万象的浮世绘,看光怪陆离的众生相。
《大师和玛格丽特》是俄罗斯作家布尔加科夫代表作。撒旦假扮外国教授沃兰德走访20世纪30年代的莫斯科,遇见莫斯科文联主席柏辽兹和青年诗人伊凡,他们不信上帝,也不信魔鬼,沃兰德逐一反驳,并预言柏辽兹当天的死亡。伊凡怀疑沃兰德是外国特务,紧追不舍,却被关入精神病院,并认识了大师。大师写过一本关于彼拉多审判耶稣的小说,不容于世,被关进精神病院。玛格丽特遇见撒旦的随从,得到回春脂,经历许多奇事后,终于救出大师。
第一章
千万别跟生人搭话
燠热的春日,夕阳西下,长老湖畔来了两位公民。头里那位四十上下,一身银灰色夏装,矮矮的个头,黑色的头发,顶门已秃,长得富富态态,手拿一顶帽顶打褶、相当体面的宽檐帽,刮得光光的脸上,点缀着一副特大号角质黑框眼镜。身后跟着个小伙子,肩宽背阔,赤发蓬松,后脑勺上歪戴着一顶格呢便帽,上身花格翻领衬衫,下身皱皱巴巴的白裤子,脚穿黑便鞋。
头里这位赫赫有名,叫作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别尔利奥兹,是一家颇有分量的文学杂志主编,莫斯科某文学协会(简称莫文协)主席。同行的年轻人是诗人伊万•尼古拉耶维奇•波内廖夫,笔名流浪汉 。
两位作家同志走进绿荫乍起的椴树林,径直奔向油漆得花花绿绿的小卖亭,亭子上悬着一块招牌:“啤酒、矿泉水。”
说到这里,且容我先把当晚第一桩咄咄怪事作上一笔交代:这是一个毛骨悚然的五月的傍晚,商亭左近以及平行于小铠甲街的整条林荫路到处阒无一人。夕阳正穿过干燥的雾氛,朝花园环城路冉冉西沉,烈日把莫斯科烤得滚烫,热得人透不过气来。怪的是椴树荫下却不见游客,路边长椅无人问津,整个林荫路空空荡荡。
“来瓶矿泉水。”别尔利奥兹说。
“矿泉水没货。”小卖亭里的女人说不上为什么没好气地回答。
“啤酒有吗?”流浪汉哑着嗓子问。
“啤酒晚上才能来。”女人回答。
“那有什么?”别尔利奥兹问。
“杏仁茶,只有温暾的。”女人说。
“好吧,好吧,温暾就温暾吧……”
杏仁茶上泛着厚厚一层黄沫,飘出一股剃头铺子的怪味。两位文学家一顿豪饮,接着马上打起嗝来。他俩付过茶钱,坐到一张临湖背街的长椅上。
这时又出了第二桩怪事,不过仅同别尔利奥兹有关:一时间他的嗝突然止住了,心脏却咚地猛跳了一下,好似朝什么地方直坠下去,待到回归原位时,疼得就像扎进了一根秃针。更有甚者,这位别尔利奥兹蓦然间被一股莫名而强烈的恐怖感攫住了:他恨不得拔腿就跑,立刻从这长老湖畔逃之夭夭。
别尔利奥兹心情抑郁地朝身后看了一眼:恐怖感从何而来呢?实在莫名其妙。他脸色惨白,掏出手帕擦擦脑门,心想:“这是怎么啦?从来没有过的事呀!心脏出毛病了?……疲劳过度?……兴许,该把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先撂在一边,到基斯洛沃茨克 去歇上两天……”
正在这节骨眼上,一团热气飘到他眼前凝聚起来,形成一位怪模怪样的透明的公民:小脑袋上扣着一顶马车夫戴的小巧玲珑的硬檐大盖帽,穿着一件也是轻飘飘的花格上衣……个子足足两米出头,但人却瘦得出奇,是个溜肩膀。列位注意,这家伙脸上完全是一副幸灾乐祸的表情。
别尔利奥兹一辈子不信邪,哪见过这等活见鬼的怪事。他脸色更白了,眼珠子瞪得差点没掉出来,心里直犯嘀咕:“这绝不可能……”
惜乎事实就在眼前,不容不信!这位透明透亮、又高又瘦的公民正悬在半空中左摇右晃。
这一来别尔利奥兹吓得非同小可,连眼睛都闭不上了。待到再一睁眼,一切早已杳然:幻影消失了,穿花格上装的不见了,扎进心里的秃针也同时被人拔掉了。
“呸,真见鬼!”主编喊了一声,“伊万,你看我,方才差点没热昏过去!甚至产生了某种幻觉……”他想挤出一丝笑容,可眼神里却余悸未消,两只手还在哆哆嗦嗦。但他总算一点点镇静下来,取出手帕扇了两下,摆出精神头十足的架势说了一句:“来吧,咱们接着谈……”于是,被杏仁茶打断的话头又接了下去。
事后方知,这番话谈的是耶稣基督。原来这位主编约了诗人给下期杂志写一部反宗教长诗。时过不久,伊万便应约交稿,遗憾的是主编竟一点儿也不满意。尽管流浪汉不惜浓墨重彩,把长诗主人公耶稣涂抹得一团漆黑,但依着主编的意思,整部长诗还得重写。这会儿主编正在给诗人大讲耶稣,颇有给学生上课的味道,目的就是要指出诗人的基本错误。
伊万不成功的原因何在?是才尽智穷、力不胜任,还是对问题一无所知?这就很难说了。不过若要说他笔下的这个耶稣,可也真算得活灵活现,只不过浑身毛病罢了。
别尔利奥兹呢,却打算向诗人证明,问题并不在于对耶稣有没有赞美,而是世上压根儿就没有这么一号人,种种有关耶稣的传说,纯属子虚乌有,都是最不值钱的瞎话。
列位须知,主编本是一位饱学鸿儒,言谈中他巧妙地指出,许多古代历史学家,如名满天下的亚历山大城的斐洛 ,学富五车的约瑟夫•弗拉维 ,都不曾有一个字提及耶稣的存在。好个别尔利奥兹,果然不愧是纵览经史、学识渊博,话里话外又告诉诗人,在塔西佗 著名的《编年史》十五卷四十四章虽有一处提到耶稣之死,其实那纯粹是后人的伪托。
主编这番谈话,诗人听来处处新鲜。他洗耳恭聆别尔利奥兹的教诲,一双充满活力的碧眼目不转睛盯着主编,只是不时打两个嗝儿,惹得在心里不由得直骂杏仁茶可恶。
“所有东方宗教,”别尔利奥兹说,“几乎都出过一个什么童贞女诞育的神。基督教也没有做什么新鲜事,它不过是依样画葫芦地炮制了自己的耶稣而已。其实,历史上哪有过耶稣这个人呐,需要着重说明的应该是这一点……”
别尔利奥兹那尖声尖气的高嗓门响彻了空荡荡的林荫路。只有他这样一个博古通今之人,才敢于涉足如此深奥的学问而不至碰得头破血流。诗人呢,也得以与闻多多趣闻逸事,增长不少有益的知识。比如,埃及的欧西利斯是天地之子,是一位德行崇高的神祇;腓尼基有个神祇叫法穆兹,还有个神祇叫巴杜克;墨西哥的阿兹德克人过去特别崇拜一个鲜为人知的可怕神祇维茨里-普茨里;等等。正在别尔利奥兹对诗人讲到阿兹德克人用泥团捏制维茨里-普茨里的当儿,林荫路上出现了第一个人。
后来不少单位出过证言来描绘此人的外貌。不过,说实在的,那放的都是马后炮。然而,若将这些证言的内容加以对照,真叫个使人无所适从。比如,第一份材料说此人身材矮小,镶金牙,跛右足;第二份却说他身材魁梧,戴白金牙套,跛左足;第三份只是一笔带过,说此人并无特征。应该承认,这些证言全都漏洞百出。
事实上这位公民哪条腿也不瘸,身材既不矮小,也不魁梧,只不过个头稍高而已。至于牙,左侧镶的是白金牙套,右侧是金牙。穿着一身价格昂贵的灰常服,脚上是一双与衣服同色的进口皮鞋。灰色贝雷帽潇洒地歪戴在脑袋上,腋下夹着一根文明棍,黑色镶头雕成了狮子狗脑袋形状。此人看上去四十出头,嘴角微歪,胡子刮得挺干净,黑发,右眼珠乌黑,左眼珠不知为什么却是绿的。眉如漆描,一高一低。一句话,是个外国佬。
他从主编和诗人并坐的长椅前走过,瞟了一眼,收住脚步,一屁股坐到旁边那张长椅上,距两位朋友只有几步。
“是德国人。”别尔利奥兹暗忖。
“是英国佬……”流浪汉脑子里寻思,“嚯,还戴着一副手套,也不嫌热!”
外国佬举目朝那环湖列成方阵的一幢幢高楼眺望,看来此地显然他是第一次光临,故而兴味盎然。
他的目光滞留在大厦的顶端几层,上面的玻璃窗映着即将同别尔利奥兹永别的太阳,闪动着万点碎金,发出耀眼的光辉。接着,又把目光向下移动,但见苍茫暮色之中,一扇扇玻璃窗已变得昏暗无光。他说不上为啥傲慢地冷笑一声,眯起眼睛,双手扶定文明棍的圆柄,下巴颏压到手背上。
“伊万,”别尔利奥兹说,“你有些地方,比如上帝之子耶稣诞生那段,写得相当精彩,讽刺也很深刻。不过关键在于耶稣降生之前早已出现过不少别的神子,像古代腓尼基人信奉的阿多尼斯,弗里吉亚人 信奉的阿提斯,波斯人信奉的密特拉都是。简而言之,他们谁也谈不上降生不降生的,谁也没有真正存在过。其中包括耶稣。所以,你千万别去写什么耶稣诞生的场面,或者,比方说,写什么智者报信 的场面,而是要把报信之说的种种荒诞不经写出来。否则照你那么一写,就像真有那么一回子事儿似的!……”听到这儿,流浪汉忙屏住呼吸,强忍着把一股难受的逆呃压了下去,结果打出的嗝来更不是味儿,声音也益发响亮。这当儿别尔利奥兹也收住话头,因为外国佬竟突然起身,朝两位作家走来。他俩瞅着来人,满面愕然。
“请原谅,”外国佬来到面前,话虽带点洋腔,说得倒还清楚,“我同二位素昧平生,不揣冒昧……不过,二位这一番宏论实在太精辟,太有意思了,故而……”
他客客气气除下贝雷帽,这一手搞得两位朋友毫无办法,只好起身答礼。
“八成是法国人。”别尔利奥兹想。
“准是波兰人……”流浪汉寻思。
笔者还得交代两句:打从外国佬一开口,诗人对他的印象就十分糟糕;不过别尔利奥兹倒似乎挺喜欢这个人。其实也算不上喜欢,而是,怎么说呢……就算感兴趣吧。
“我可以坐一坐吗?”外国佬彬彬有礼地问。两位朋友身不由己地往边上一闪,外国佬就势一转身坐到他俩之间,立刻加入了谈话。“如果鄙人不曾听错,二位方才好像说,世上没有耶稣?”他用左边的碧眼盯住别尔利奥兹问。
“是的,您没听错,”别尔利奥兹也恭而敬之地回答,“我正是这样说的。”
“啊!太有意思了!”外国佬叫了起来。
“这家伙搞什么鬼名堂?”别尔利奥兹皱起眉头心中暗想。
“阁下也同意贵友的这番高见吗?”陌生人又往右一转,朝流浪汉问。
“完全的百分百!”诗人说话总爱别出心裁。
“妙哉!”不速之客叫了一声,但说不上为什么又鬼鬼祟祟朝身后张了一眼,把本来就不算高的嗓门压得更低了,“请原谅鄙人这样喋喋不休,不过,抛开别的先不论,以我的理解,二位竟不信上帝吗?”他眼里流露出又惊又惧的神情,接着加上一句:“我发誓,一定守口如瓶!”
“是的,我们不信上帝。”别尔利奥兹见这位外国游客如此胆小怕事,微微一笑,“不过,这事完全可以放心大胆地谈嘛。”
外国佬朝椅背上一靠,好奇得甚至发出一声轻轻尖叫。
“你们都不信神?”
“是的,我们是无神论者。”别尔利奥兹笑眯眯地回答。流浪汉却火冒三丈,心想:“缠住不放了,这洋鬼子!”
“啊,太好了!”让人纳闷的外国佬大叫一声,转动脑袋,一会儿朝这位文学家瞧瞧,一会儿朝那位文学家看看。
“在我们国家,不信神绝不会有人感到奇怪,”别尔利奥兹彬彬有礼地说,颇有外交家的风度,“我国大多数人出于自觉,早就不相信上帝的种种神话了。”
谁知这时外国佬竟站起来同惊愕不已的主编握握手,冒出这么一句:
“请允许我向您表示衷心感谢!”
“您干吗谢他?”流浪汉眨巴着眼睛问。
“为的是这条非常重要的新闻啊。对于我这样一个旅行者来说,这条消息实在太有意思了。”洋怪物意味深长地竖起一根手指说。
看来,这条重要新闻给外国佬留下的印象的确十分深刻,只见他又惊又惧地抬起头来,把幢幢楼宇一一看过,仿佛生怕每个窗口都会冒出个什么不信神的人物来似的。
“不,他不是英国人。”别尔利奥兹心想。流浪汉却琢磨:“这家伙俄语怎么说得这么地道?哪儿学的?真有意思!”接着,又蹙起眉头。
“不过,鄙人倒要请教,”外国佬经过一番忧心忡忡的思索,又开口了,“对于那些上帝存在说的论据又作何解释呢?众所周知,这样的论据足有五条之多呢!”
“咳,”别尔利奥兹不无遗憾地回答,“哪一条论据也是一文不值!人类早就把它们统统塞进历史博物馆啦。您总该承认,对一个心智健全的人来说,任何证明上帝存在的论据,都是难以成立的啊!”
“妙哉!”外国佬又叫道,“妙哉!在这个问题上,您同康德那不知安分的老儿说法倒是如出一辙。不过怪就怪在虽说这五条论据已被他彻底推翻,可后来他却像自嘲似的反倒又搞出来个第六条。”
“康德的论据,”满腹经纶的主编委婉地一笑,“同样不足为训。难怪席勒说,康德对这个问题的观点只能使奴才感到满意。施特劳斯 对第六条可是公然嗤之以鼻的。”
别尔利奥兹一边说话一边心里嘀咕:“这到底是个什么人,俄语怎么这么棒?”
“真该把康德抓起来。单冲他这套谬论,就该打发他到索洛夫基 去蹲上三年!”伊万冷不防脱口说了这么一句。
“伊万。”别尔利奥兹搞得很窘,轻喊了一声。
不过,把康德送往索洛夫基的建议非但没使外国佬惊讶,反倒逗得他大为开心。
“着哇,着哇!”他喊,那只死盯着别尔利奥兹的碧绿的左眼闪出一缕光芒,“那地方他去正合适!那天吃早饭的时候我就对他说过:‘教授,一切悉听尊便。不过您琢磨出来的那一套,实在不怎么合乎情理。也许挺高明,可谁也闹不明白。人家会笑话您的。’”
这话把别尔利奥兹听傻了,心想:“吃早饭的时候?……对康德说?……胡诌些什么呀?”
“可是,”外国佬毫不在乎别尔利奥兹这副大吃一惊的表情,接着又对诗人说,“要想把他打发到索洛夫基去怕是没法办了。早在一百多年前他就上比索洛夫基远得多的地方去了。而且,实话对您说吧,谁也没那个能耐把他再弄回来。”
“真遗憾。”诗人挑衅似的说。
“我也深以为憾。”陌生人说话时一只眸子熠熠发光。随即又说:“不过,有这么一个问题我始终百思不解:如果没有上帝,那么请问,谁来支配芸芸众生的一切呢?谁又是天下的主宰呢?”
“人自己支配自己呗。”流浪汉忙愤愤地回答。其实,这个问题他也闹不清。
“对不起,”陌生人客客气气地说,“若是说到支配,总得在一段说得过去的时间里有一个比较拿得准的计划才成吧?人要是非但无法对短得可笑的一小段时间——比如说一千年吧——提出任何计划,甚至连自己的明天也无法担保,那么请问二位,这支配二字又怎能谈得上呢?”
“说实在的,”这回陌生人转向了别尔利奥兹,“就拿您来说吧,试想,正当您支配着别人和自己,在那儿发号施令的时候,总之,正当您春风得意的时候,突然,您……嘻嘻……肺子里冒出个大瘤子……”只见外国佬甜蜜地一笑,仿佛能琢磨出肺子里长瘤子这档子事来心里不知有多高兴似的。“是的,瘤子……”他像只猫似的眯起眼睛,把这个刺耳的词儿又说了一遍,“结果呢,您这种支配说完就完!
“于是您哪,除了保命要紧,别的事可就一概不感兴趣了。一来二去家里人事事瞒着您,您也估摸出大事不好,赶紧四处求访名医。后来就连走方郎中也不放过了,甚而至于还算命打卦。可是求医问药也好,求神打卦也罢,全都无济于事了。这您心里明镜似的。最后的结局别提多惨:两天前还自以为能支配这支配那,如今却躺在木头匣子里一动不动了。身边的人也心里有数:躺着的这家伙再也不中用了。于是就把他塞进炉膛,一烧了之。
“有时还更糟:某某人刚打算到基斯洛沃茨克去疗养,”说到这儿外国佬拿眼睛朝别尔利奥兹一瞟,“心里想,这还不是小事一桩吗?可谁知就连这点小事也支配不了,因为不知怎么搞的他竟会一跤滑到电车轮子底下轧死!您说,自己支配能支配到这个份上吗?您难道不认为,说他完全受别人支配反倒更合乎情理吗?”说罢,陌生人吃吃怪笑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