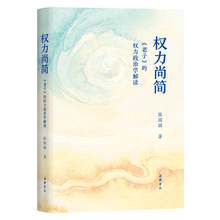《从庄子到僧肇:论大乘中观学对中国美学精神的拓展》:
由本文前面的梳理可知,“物”是中国本土哲学中的独特范畴,但此处以“色”代替“物”不仅仅是遣词的差异,而是包含了思想的转换。“色”的含义虽然大概与实存之“物”或“现象”等词相同,但却是佛学的独有概念。支遁《即色游玄论》中仅流传下来的这几句话也触及了佛学的核心义理。佛学认为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是彼此相待而存、相待而灭的;外缘具足则一物生起,即佛陀所谓“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是也,而外缘离散则一物灭去,所谓“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是也,这即是万法缘起、无自性故而“空”的基本含义。佛学内部流派杂陈,往往不可通约,但此种“空”义却是各派立论的起点,尤其对印度早期大乘教派如中观学、早期大乘经典如《般若经》而言,缘起无自性的“空”都是其力图阐明的核心义理。支遁时代流行中土的正是早期大乘佛学的《般若经》系列,支遁此处正是对缘起无自性“空”理论的阐发:“性”即本性,也就是佛学所谓的“实相”,事物的真理;“自”即独自,全然不依凭外力、外缘而能自已存在。但支遁认为无“色”能够自存、自有,故日“色不自有”,这便是佛学所谓“空”的内涵,因此他又说“虽色而空”。应该说,支遁的即色之论把捉到了大乘空观的要点,相比于“六家七宗”的其他各家都多少还在延续玄学旧义,未曾从因缘相待的角度阐发空义,支遁的思想实已突破了玄学的藩篱,而应归于佛学的范畴了,这一点对比他和郭象的“物论”更可一目了然。郭象哲学的核心概念是自生、独化,明确表示物之生起,没有任何外在的力量和原因,万物都是自生自成自足自在的,所谓“明物物者,无物而物自物耳”(《知北游注》),指出没有使得物成为物的“物”,不过是“物自物”,这和支遁“色不自有”的佛学思想显然是针锋相对的。郭象和支遁在物性问题上的迥异见解正可看作是玄学和佛学思维方式的本质差异,从因缘相待的角度认识万物的本性,并以此建立哲学大厦的基石,这在中国传统的思想中是付之阙如的一个维度,支遁在中国哲学史上的重要意义也于此可见。
前文提到郭象“自生”哲学所留下的诸多难题,而“色不自有,虽色而空”的哲学思路就为解决自生哲学的理论困境提供了新契机。相比于玄学,“即色论”提出了一种全新的、非本体论的哲学进路,依其观点,万物皆处在绵延不断的因果链条上,这样去认识万物就避开了玄学本末、有无的旧路,同时也脱去了本末、有无论中所难免产生的各种“本体”观念。这当然能打开“物论”的新视野。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