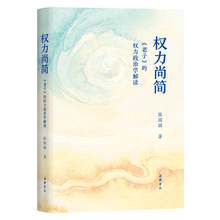《近世儒学史的辨正与钩沉》:
对海门而言,江与河的比喻,是指具体时空中的存在类型和样态。儒和禅的不同,正如江与河一样,是具体时空中不同的存在。这种万事万物在具体时空中的差异,作为“百虑”和“殊途”,是无需也不能求其一致的,正所谓“因缘之应迹难齐”,所以海门说“欲合一,虽至神不能”。另一方面,虽然江与河在具体的时空中各自有其不同的存在方式,但二者的性质、功能和归宿却是相同的。性质都是“湿性”,功能都是“流行”、“利济”,归宿都是“到海”。就此而言,作为“一致”和“同归”,儒和禅之间的共性也是无从抹杀的,正所谓“心性之根宗无二”,所以海门又说“必歧为二,虽至愚不许”。如果能够明了儒与禅“不可分”、“不可合”各自所在的意义层面,那么,“理一”和“分殊”可以两不相妨而一体无间。海门所谓“了此无二之宗,何因缘之不可?顺彼难齐之遇,何心性之不存?”正是此意。如果不通“理一分殊”之旨,不能明了儒与禅之间分合的意义层面,那么,其弊就不免会使儒与禅都偏于一端而未能得其整全。对儒家来说,如果视禅为“异端”,“使忘言绝虑之旨、知生知死之微,皆推之于禅而不敢当之为儒”,儒家自然只有“粗浅淡薄”的一面;对佛教而言,如果视儒仅为“世法”,“使日用饮食之常、经世宰物之事,皆推之于儒而不敢当之为禅”,佛教则“不可以治家国天下”,所谓“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以及“行住坐卧,皆是禅定”、“担水砍柴,无非妙道”,就都无从谈起了。海门所谓的“儒者之过”和“禅者之过”,正是对儒家和禅宗仅得一面的结果。在他看来,前者是“不知孔子之儒”,后者是“不知如来之禅”。而要了解“孔子之旨”和“如来之旨”,对海门来说,必须分别到“濂洛以后诸儒”和“曹溪以下诸师”那里去探求。显然,对海门来说,宋明理学和禅宗各自代表了儒家和佛教的真精神。
笔者曾经指出,晚明阳明学发展出了一种“理一分殊”的多元主义宗教观。这种宗教观既肯定“百虑”,又信守“一致”;既肯定“殊途”,又信守“同归”。虽然认为具体时空中任何一种人类的精神传统都不能以根源性的“道”本身自居,只能是统一性的“道”的“殊相”,但由于同时并不否认宇宙间存在根源性和统一性的“道”,所以也不会流于相对主义。事实上,海门的《佛法正轮序》,正是这种“理一分殊”的多元主义宗教观的最佳见证和说明。笔者以往的论述并未引用海门这篇文献,这里也恰好可以补充。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