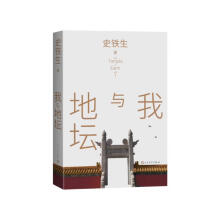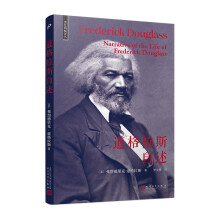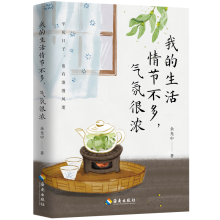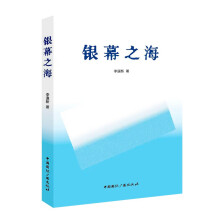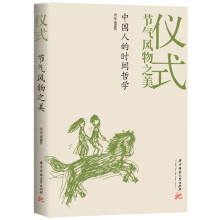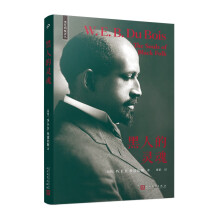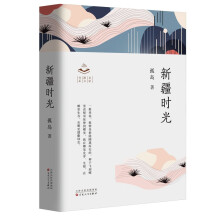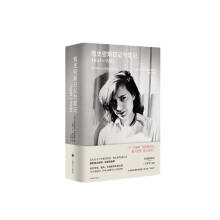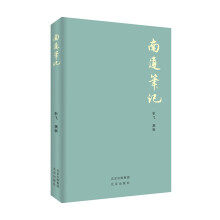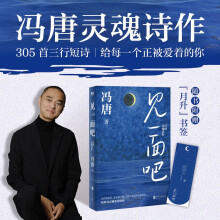《雨声》:
总之,所到之处,所见之事,给我的印象就是“随意”,让人觉得,这里是一个宽容大度、实事求是、人乡随俗的地方,也有马马虎虎、随遇而安、消极被动。这里没有斤斤计较、刻薄死板、寸土必争,却又缺乏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积极进取的精神。
以一鳞半爪、点滴见闻来判断一个城市是轻率的。但我真心希望这种判断是成立的。一个城市,一个成熟的城市,并不在于高楼林立、市井繁华,而在于轻松方便、自由和谐。从标准化到人性化,从分级挂挡到无级变速,从非开即关到模糊控制,从讲原则立场到模糊政策,从一言堂到讨价还价,从非对即错、非敌即友到多元化一体化,不都是进步吗?不都是人文社会的需要吗?秩序、规范、制度、纪律,乃至严刑厉法,都是相对于违规、相对于向善的人性背离才有用的。一个融洽的家庭,一个默契的组织,一个和谐的集体,一个宽容的社会其实是不需要太多苛刻规范的。那些看上去没有分工设计楚河汉界,甚至各行其是混乱如麻,而实质上却左右逢源水到渠成,甚至丝丝入扣珠联璧合的过程,才会透出自然美与生活美。
这样的城市大概是不能用建设来实现的,是无法模仿的。如果说伊斯坦布尔真是这样,那也许是它自身地理限制、历史进程和宗教信仰的结果。
伊斯坦布尔位于欧亚两大陆接合部,是连接东西方的桥梁。贯通黑海与地中海的博斯普鲁斯海峡将其划分为欧洲与亚洲两大部分。在市内穿行的小火车,据说西接巴黎东达伊朗。西方文化与阿拉伯文明在这里交汇碰撞,促进了城市的开放与宽容。伊斯坦布尔依山靠海,所有建筑错落在山地丘陵上。从海峡中看两岸,一排排建筑由海边往后退,由低往高层层叠加,就是放大了的布达拉宫。全国八千万人,伊斯坦布尔占1/8。加之山地与海峡占去了相当的地面,居住密度极大,人均空间很小。伊斯坦布尔的历史是辉煌的。继东罗马帝国之后,奥斯曼帝国也定都于此。前者在这里留下的古代文明随处可见。高悬头顶的罗马水渠、直插云端的千年石柱,无不让人肃然起敬。后者的版图曾相当于现在四个欧洲,是近五百年来中东地区统治范围最广和最为有效的一个国家。在它治下的四百多年间,除了与欧洲基督教君主国和亚洲的波斯帝国偶有冲突,其内部不同民族、宗教、派别间一直保持着高度和谐,成为伊斯兰世界团结的核心。骄傲的历史给了伊斯坦布尔人自信大方。谈到历史,他们便会陶醉于自我欣赏,滔滔不绝。“一战”后,土耳其结束了帝国制,开始了世俗主义的改革。在价值观上更趋向于西方的自由民主,特别是近些年来这一步子似乎迈得更快。军事上它是北约成员,经济上一直在为加入欧盟努力。在美伊战争前,政府接受了美国提出的在土驻军的要求。但新的执政党正义与发展党对言论更开放,允许党员就美驻军问题进行讨论与投票,结果否决了这一动议。美国政府的胁迫与利诱都未能发挥作用。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