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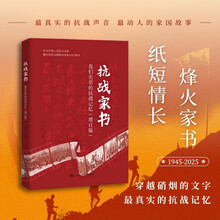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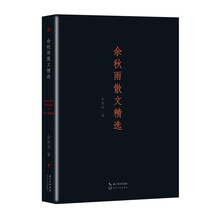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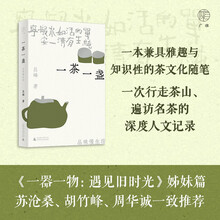


回忆文学世家与前辈作家的交往:现代文学史上的耀眼群星是家中常客
叶兆言在《朱自清先生醉酒说英语》《白马湖之冬》《巴金的最后三部小说序》《父亲和方之的友谊》《郴江幸自绕郴山》《万事翻覆如浮云》里回忆文学世家与朱自清、夏丏尊、巴金、高晓声、汪曾祺、林斤澜、陆文夫等文人交往的故事、他们与父亲的情谊、在特殊年代的命运,以及对现代文坛的贡献。因为经历,所以同情,叶兆言将宏大抽象的历史洪流,化为日常私人细节,让记忆生发出见证的力量。
回忆少年时期,和父亲叶至诚曲折坎坷的一生
这部作品也是叶兆言个人成长的自传,祖父叶圣陶、父亲叶至诚、伯父叶至善、姑母叶至美都是文坛中人,他的家族叙事里贯穿着“人与历史”的哲思。在他平俗冲淡的点滴回忆中,叶氏家族的生平事迹、坎坷遭遇、举手投足、人格操行被串联起来。家族的疼痛体验里,多少关于历史、时代、社会、人生的沧桑感喟尽寓其中。
回忆六七十年代初读外国文学的故事
在读书荒芜的时期,他不顾父亲“禁令”,长年累月地从家里书房偷书看。《塞万提斯先生或堂吉诃德骑士》《重读莎士比亚》《〈少年维特之烦恼〉导言》《难忘雨果》《想起了老巴尔扎克》《永远的阿赫玛托娃》《横看成岭侧成峰》是作者的外国文学“阅读笔记”,塞万提斯、莎士比亚、歌德、雨果、巴尔扎克、阿赫玛托娃、奈保尔等作家的作品在他的少年时期留下了深深印记,随着阅读经验的丰富,对其人其作的认识也越来越全面,在评点之中,亦可见作者的文学品位。
朱自清先生醉酒说英语
读朱自清先生日记,有几处小记录让人会心一笑。譬如喝醉了酒,一向拘谨的朱先生会慷慨陈词,对熟悉的朋友大说英语,这是地道的酒后“胡说”和出“洋相”。事后听别人说起,朱先生非常震惊,也非常羞愧。我们都知道朱先生是个认真严肃的人,酒后失态本不足为奇,发生在他身上却多少有些意外,仿佛做鬼脸,如果是学童倒也罢了,没想到私塾先生也变得调皮捣蛋起来。三十年代初,朱先生以清华中文系主任的身份,去欧洲做访问学者,为此写了《欧游杂记》和《伦敦杂记》,传唱一时。不过我更喜欢他的日记,因为这类文字不为发表而作,可以读到更真实的东西。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五日的日记中有这么一段:
早大一有人示我“文侯之命”,问文侯是指重耳否,余竟不知所对,惶恐之至。
即使最有学问的人,也不可能什么都知道,“惶恐之至”充分说明朱先生做人的态度。在英国期间,因为英文程度不够,朱先生屡屡遭人白眼。不由得想起闻一多和郁达夫国外留学时的情景,都说中国人出了国都爱国,但是留学的年龄阶段不同,思想情绪也不同。闻和郁在国外做学生时岁数还小,受人歧视,难免孩子气,因此也难免口号标语似的愤怒。朱自清已经是清华的大教授、系主任,他所产生的情绪就要复杂得多。
首先是学外国语言产生的自卑。年龄越轻,学习语言能力越强,反过来,年龄越大,能力越弱。但是年龄大了,理解能力更强,于是弱和强的悬差,让做事认真的朱先生无所适从。出国三个月以后,朱先生第一次做了这样的梦,他梦见自己“被清华大学解聘,并取消教授资格,因为我的常识不够”。这个梦很值得让人玩味,一个月后,他又一次做了类似的梦,“梦见我因研究精神不够而被解聘,这是我第二次梦见这种事了”。有趣的是这种噩梦还在延续,过了四年,早已回国的朱先生在日记中写道:
昨夜得梦,大学内起骚动。我们躲进一座如大钟寺的寺庙,在厕所偶一露面,即为冲入的学生发现。他们缚住我的手,谴责我从不读书,并且研究毫无系统。我承认这两点并愿一旦获释即提出辞职。
我想说的是,做学问的人老是自卑和自责,绝对不是什么坏事,盲目自大才是可笑的。钱钟书先生在小说《围城》中,把出国留学镀金比喻成为种防止天花的牛痘,胳膊上有了那么一个疤,做学问的便算功德圆满。这个带有讽刺意味的比喻虽然尖刻,毕竟涉及了要害。朱先生在日记中曾这样勉励自己,说现在大学里的好位置,差不多都已被归国留学生占满了,像他这种没出国留学过的教授已是硕果仅存,必须自重,珍惜自己的机会,要加倍努力。这绝对是当时的实情,留学犹如科举时代的功名,有没有进士出身的身份至关重要。朱先生日记中,屡屡能看到俞平伯先生闹加薪,这让朱先生很为难,作为好友,深知俞平伯的学问,可是作为系主任,不能不考虑到资历,只能让俞一再失望。俞先生出身北京大学,和傅斯年一样,同为黄侃先生的高足,又同是五四新青年,可是傅在国外留学多年,其地位和待遇不知高出多少。一九二〇年俞先生和傅斯年曾乘同一艘轮船去欧洲闯荡,到英国以后,傅先生留了下来,俞先生却因为留学费用不足,玩了一圈潇洒回国,结果没有洋学历便成终生的遗憾。
朱先生在英国做访问学者的时候,非常用功,像海绵一样充分吮吸着西方的养料,文学、哲学、艺术、交际舞以及各种客套礼节,无不一一虚心学习。值得指出的,朱先生此时虽已和陈竹隐女士订婚,并没有完婚,是地道的黄金王老五。在朱先生身上,见不到今日成功人士的那种自以为是,他到了西方,没有潇洒地赶快享乐人生,而是老老实实做学问,丝毫不敢怠慢。庞大的西方像座高山一样蛮横地挡在他前面,他努力了,用功了,甚至可以说奋斗了,但是结果却是,越想更多地了解,越发现根本不了解,越是崇敬,越是自卑。因此,在他的梦境中,没有学问被解聘也就不奇怪,隐藏在潜意识中的恐惧仿佛漏网的鱼逃了出来。
自从进入近代以后,中国的学人对于西方总是崇敬与疑虑并存,陈寅恪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中说:
窃疑中国自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
陈先生的意思,是说无论生搬美国的资本主义,还是硬套苏联的社会主义,在有着几千年传统的中国,都成不了大气候。这道理大家多少也有些明白,陈先生在国外待过许多年,通许多国语言,由他来指出这件皇帝的新衣最有说服力。问题在于,事物总是有另一面,成不成大气候是一回事,管用不管用又是另外一回事。外来的和尚好念经,外国的东西确实对中国起着决定作用,这不仅表现在政治思想上,同时也反映在学术思想上。吴宓先生在晚年的日记中曾说:
寅恪兄之思想及主张毫未改变,即仍遵守昔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说(中国文化本位论)。在我辈个人如寅恪者,决不从时俗为转移。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本身就是一种时俗。趋时从俗有时候免不了,只有程度的不同,就好像同样喜欢外国的好东西,有人关注先进的文化思想,有人留恋流行的实用小家电。不同的人,对西学为用的“用”,有截然不同的理解。不由想起学术界关于中国人种起源的讨论,古文大师章太炎的《种姓篇》就认为中国人的祖先源于古巴比伦人,另一位经学大师刘师培也持差不多的观点。时至今日,这种胡乱认人作父的学术观点听上去怪怪的,但是在一个世纪前,这其实是一些很有意义的思考,学术界不仅怀疑中国人源于古巴比伦,而且还可能是古埃及古印度的后裔。
做学问具有开放性的思维总是好事。陈寅恪先生的过人之处,在于他对西方文化有超过常人的学识修养,在于扎实的现代史学基本功训练。陈先生也承认,他研究中西文化交流,尤其是佛学传播和中亚史地,都曾深受西洋学者的影响。这是一些终身受用的影响,在很多方面,外国人做中国的学问,比中国人做得更好,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然而仅仅只是受其影响,还是远远不够,师傅引进门,修行在各人。做学问有做学生的虚心是对的,如果老是当不长进的学生,老跟在洋人后面亦步亦趋就不足取。受最先进的学术影响,向最先进的思想看齐,是通往真理之路的捷径,也是打开现代学术之门的钥匙,去西方留学不外乎为了走捷径和找钥匙,朱自清正是带着这样的观点远赴英伦。但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便宜无好货,捷径也会把人引向死胡同,钥匙也可能只是打开了一道无关紧要的院门。
有个河南人去美国研究哲学好多年,突然看破红尘,起程回国,去少林寺当了和尚。大家觉得奇怪,既然是出家,何必远涉重洋,绕道美利坚,直接在老家上山不就行了。做学问犹如出家当和尚,有时候非得绕道走点弯路才行。顿悟的境界不是什么人都能轻易达到的,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得出的结论也就不同。上个世纪的六十年代末,中国正进行着如火如荼的“文化大革命”,著名汉学家李约瑟先生在《东西方的科学与社会》中表达了一个十分有趣的观点,这个观点我们真是不太乐意接受,就是中国科学的发展主要是为了“实用”。无论是在过去,还是今天,中国人都天真地相信自己的文化传统,更多的是精神上的追求,“朝闻道,夕死可矣”,所谓“君子养浩然之气”。天知道中国的科学实用在什么地方,恰如鲁迅先生说过的那样,中国人发明了火药是做爆竹敬鬼神,发明了指南针也不过是用来看风水,而火药和指南针只有到了洋人手里,才能成为征服殖民地掠夺宝藏的利器,应该说洋人讲究实用才对。
联系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句著名的口号,就会意识到李约瑟并没有完全说错。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实用”这个词早就扎根在我们的文化中,只是不知不觉。越是到近代,实用的观点越是甚嚣尘上。譬如郭沫若对闻一多先生有个很新奇的比喻,说闻先生虽然在古代文献里游泳,但不是作为一条鱼,而是作为一枚鱼雷,目的是为了批判古代,是为了钻进古代的肚子,将古代炸个稀巴烂。闻一多生前也曾对臧克家说过:“你诬枉了我,当我是一个蠹鱼,不晓得我是杀毒的芸香。虽然两者都藏在书里,他们的作用并不一样。”他声称自己深入古典,是为了和革命的人里应外合,把传统杀个人仰马翻。在一些文章中,他甚至把儒家道家和土匪放在一起议论,“我比任何人还恨那些故纸堆,正因为恨它,更不能不弄个明白”。
我一向怀疑这话中间多少有些做秀成分,按照我的傻想法,闻先生如果不是对中国古典的东西情有独钟,有着特殊的兴趣,绝不可能成为一名纯粹的书虫。抗战期间,西南联大的文学院落脚蒙自,闻先生在歌胪士洋行楼上埋头做学问,除了上课、吃饭,几乎不下楼,同事因此给他取名为“何妨一下楼主人”。如果仅仅是为了和古代文化作对,给传统添些麻烦,这种信念支撑不了多少时间,因此,我更愿意相信他只是找个冠冕堂皇的借口,因为在习惯中,大家共同关心的兴奋点,常常是我们的行为有什么“用”,对于国计民生有什么实际的好处,有什么样的思想教育意义。以成败论英雄,以有用没用来衡量价值,这种学理定势并不是随便就能改变。做学问和做生意并不一样,可是在谈论别人的学问时,我们常犯的一个低级错误是自己也忍不住变成了生意人。
正如把清朝乾嘉学派的考证说成是只会做死学问,简单地归结一代知识分子怕掉脑袋,这种貌似深刻、似是而非的简单结论,多少有点投机取巧。乾嘉学者在考据上找到的乐趣是后人无法想象的,学问无所谓死活,书呆子往往比那些读书的机灵鬼更可爱。回顾已经过去的上一个世纪的学术史,我对闻一多先生学术研究的中断觉得最痛心,因为他对中国文学史研究的独到匠心,空前绝后无人匹敌。与严谨认真的朱先生相比,闻先生的才、学、识各方面都更胜一筹。虽然在美国留学时学的是美术,但是因为早年就打下的良好西方教育基础,就如种过牛痘已有免疫能力一样,他不会在令人眼花缭乱的西方思想面前无所适从。他全身心投入自己所做学问的那股疯狂劲儿,为了一个词语一个神话下的刻苦钻研功夫,是同时代以及后来的学人望尘莫及的。
更难能可贵的,是闻先生拥有诗人的敏感与丰富想象。良好的基础与吃苦耐劳的精神,对于做学问来说,确是非常难得,毕竟还不是凤毛麟角,无迹可寻。就像是否“有用”不是最重要的一样,基础与刻苦只是鸟的一对翅膀,没有翅膀飞不起来,也飞不高,但是,仅仅有翅膀仍然远远不够。诗人的敏感和想象能够创造一切,纵观古今中外,第一流的学问恰恰都是有诗人气质的人完成的,诗人不计成败利钝,无所谓后果,不在乎起因。放大了说,诗人气质绝非只有诗人才有,这是一种难以用语言描述的东西,看不见,摸不着,无声无臭,来无影去无踪,它创造了世界上一切真正美好的东西。
诗人气质不仅造就了第一流的诗人,还可以产生第一流的艺术家和科学家,产生第一流的政治家和商人,产生第一流的军人和运动员。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在诗歌精神上可以对话,大科学家本身就是一首诗,牛顿、达尔文、爱因斯坦,他们的发明创造离开不了诗歌精神。乾嘉学者致力于训诂,达尔文研究人类进化,牛顿和爱因斯坦投身于物理学,都是异曲同工,因此,不要以是否实用来判断是非,不要以是否产生经济利益评估价值高低,这种老调还得重弹。
二〇〇一年三月十二日 河西
他的祖父是著名教育家、文学家叶圣陶,有着波澜曲折的神奇身世;父亲叶至诚,也是一位作家,曾任著名文学期刊《雨花》主编;母亲姚澄被誉为“锡剧皇后”;伯父叶至善和姑母叶至美,也都是文坛中人。他的家世实在太显赫了。但他不太愿意别人总提他的家庭,他认为作家应该是独立的,只是在回答自己为什么如此勤奋的时候,这个世家子弟才愿意举出家庭这个例子来。
——仲伟志
叶兆言的性格为人绝对是儒家的,他是一个真正的读书人,满腹经纶,优雅随和,身上散发出某种旧文人的气息。
——苏童
我从老派人的聊天中,明白了许多老式的情感。旧式的情感是人类的结晶,只有当它们真正失去时,我们才会感到它的珍重。老派的人所看中的那些旧式情感,今天已经不复存在。物是人非,生活的节奏突然变快了。寂寞成了奢侈品,热闹反而让我们感到恐惧。
——叶兆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