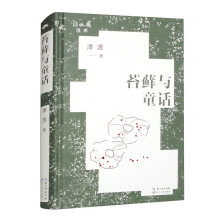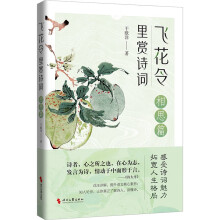牧歌(2007)
一代一代从画框内滑坠了,
犹如新生;分袂前夕,
他们身裹洞穿窗页的日光光柱的织毯;草草纺成的
褪色披肩,眉
端的汗粒,赛璐珞色影调斑驳的
风信子蓝;脖颈里涌动带电的焦灼,
他们缩陷入一张纤薄的嘴,一柄蜻蜓的窥镜,一孔裂隙,和繁弦急响,
伸展在初冬之日萌蘖的枝杈里。
罗马哀歌(2004)
向上,直至分蘖的
门厅游廊,直入稀薄的大气,那里
不再有阴影,不再有皮肤里
脆弱的晶体,不再有尚未命名
便被拆散的触摸;不向
最后的晚间安息道别。
与孤寂踽行着的活细胞一道,俱已入葬的,是
被拒斥的恐惧,被抵制的郁悒,
萎缩稠叠的骨架的遗韵,
世界的天坑,以及,种种地表之下的景况,
那语言的弦外之音。并不是大地,
不是在石块的间隙里撰写的
墓志铭,并没有最后一眠之前的
巡更守夜,更无销声敛迹的记忆堂皇重量
施压之下的惊栗;
只有一张脸,在窗玻璃后,在出口。
关于安德烈·梅德维德近期的诗歌
[斯洛文尼亚]叶尔卡·科尔内夫·施特兰恩(JelkaKernev trajn)
近半个世纪以来,安德烈·梅德维德一直在斯洛文尼亚的诗歌舞台上扮演着一个重要角色。不惟于此,从许多方面而言,他的诗歌创作已自成为一种现象;最先就此诗歌现象进行过较为详尽诠释的,是斯洛文尼亚哲学家塔拉斯·科尔姆诺埃(TerasDermnauer,1930—2008);他也是一位文学批评家,斯洛文尼亚现代主义艺术及新前卫艺术运动的理论家和权威批评家。
梅德维德的诗歌首次刊发于1970年代。他在1980年代持续发表的诗作大部分秉承一种“黑暗现代主义”风格,引入了一种来自于彼时期艺术批评的音调。1990年代,他的诗集《麋鹿之躯》(1992)标志着其诗歌文字系统展开了一种转化和变形的进程。这一进程至今仍在持续——我们仍然能够从他晚近出版的诗集中观察得到。这些变化,更准确地说,这些质变,显现于节奏,声音,语词,句法,动机等各个层面。
但一个难题不容回避;读者很快便可明确地认识到,一旦关注这些诗歌,我们就无从援引我们熟稔的其他文学批评写作中诸如“主题”,“动机”等一类关键词。就此而言,我们也许仅能勉为其难地,隐喻地论及梅德维德晚近诗歌中三个较为宽泛的共同区域。一方面,读者可见一些很大程度上与地理和历史名称有关的指称,诸如城镇(《格拉诺姆》,2012),国家(《利比亚》,2010),地区(《地中海》,2009)和大洲(《非洲》,2006)。而另一方面来自诗集本身:书名即包含构词法,以便与个别的文学作品、神话、神话故事素材构成互文关系。此中较早出现的,是诗集《罗马哀歌》(2004):某种地方精神或风土占据了书名的一域。本书值得单独提及,是因为它预示了一种正在形成的,对于记忆,尤其是对于不再被需要的记忆之辙迹的处理方式,也即,对那些在梅德维德诗中可辨识的常用名称的处理。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