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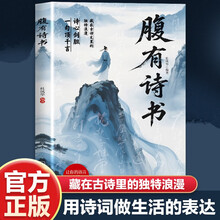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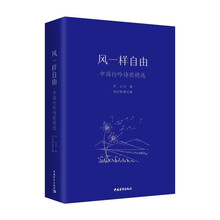
夜伐与虚构
一
我们原本不在这儿作息。
世界另有其哀沉的心脏,废墟中由一根床柱死死
压着。废墟的废墟可以追溯到造物主那双
木匠之手。
心脏的心脏则是同一坨肉。
祖父是个山水间针对性极强的小贩。
意即在规定的路线上,一个终身与负载物
谈论轻与空的游方僧。他的重中
之重:山河的庙墙高抵苍穹,但他不得入其门
躬身移至莲花座前。
信仰没有现实主义做依靠。临终忆旧,反复强调
——挑着一担沉重的盐巴,跟在军阀贩运鸦片的
长枪队背后:“我就像躲在枪管里,没有土匪
敢朝盐巴上撒尿。”一如慧能
混迹在猎人队中证悟和避祸,自己其实
也是猎物,灵魂关进猎人的箭囊。
万念归于一念:穷途之上不能戴着猎物的面具。
二
后来:战争打了很多年。
能被叫作“祖父”的人——尽管同样被
另外的子弹一次次撂倒——那得蒙受多大的恩宠
才能得到这个名分。如同拣选。
种上庄稼或未曾开垦的沃土,被打死的祖父数量惊人。
他们还是愣头青,没有结婚,搂着纸扎的新娘,
长眠于斯。儿孙的数量不比我们少多少,
但遇上火焰,他们就忍不住凑上来点燃自己的脑袋。
化成沙。凝固成蚂蚁。臭虫。蚕蛹。蛇。
就像是一群人走进画中,画被烧毁后,
除了灰烬,还从火焰里跳出来许多我们熟知的生灵。
人与其他生灵之间形成对称,彼此调换角色
不是一件难事,前提是死亡一直被辜负,
而死者保持了语言上的沉默。
再后来:祖父——真实的祖父从四川泸州开始
向着南方跑,平时是走,这一次是跑。
丢掉团箩、扁担、花椒和棉褂,提着防身用的尖刀,
样子像一个追杀乌鸦的青年道士。道路的四面八方
战场上飞来具体的人体器官,并无完整的某个人。
幸运的是他听见了迦陵鸟的鸣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