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柏拉图的<会饮>》:
厄利斯和玻俄提亚的法律由有情人本身制定,因此有情人享有充分自由。它不是由父亲们本身制定,尽管父亲们可能是有情人。但他们制定法律时担当的身份(capacity)是什么?这里提出的解释不充分。对青年男子的爱为何高于对男童和女人的爱?让我这样来说:在厄利斯没有法律禁止这类事情;因此有情人对限制不感兴趣。厄利斯法律的毛病在哪里?不清楚。因此让我们看另一群住在小亚细亚、生活在蛮夷治下的雅典人。自由。自由需要最有能力拿起武器的人结成爱的纽带。最有能力拿起武器的那些人当然既不是女人也不是男童。于是我们看到了一种截然不同的观点。此前我们看到的是nous[理智]——理智(intelligence);现在我们看到,nous或日理智绝不会让男童恋正当化,因为它会让人们爱更有智慧更年长的人。但如果问题关系到政治自由,关系到最有能力捍卫这种自由的人,那么,在仍有能力继续战斗的人之间,在较年长的一代人(在罗马人那里是四十五岁)[70]和较年轻的一代人(比如说十七岁)之间,便有了某种关联。我们必须看看这个理由是否充分。
通过182c34中的各种事例可以发现,爱欲能造就崇高的(lofty)灵魂,但爱欲不是唯一造就崇高灵魂的东西。这里我们看到另一种考量。自由被用作对男童恋的支持,但这种支持为何不起作用?自由何以不充分?每个继续读泡赛尼阿斯讲辞的人都可知道答案。爱欲与自由的关系为何不保险?因为这种观点假设有情人要充当奴隶。nous[理智]——心智(mind)——失败了。自由也不起作用,因为这种关系带有奴性。
另外还有几点,我们可以简单考虑一下。第一是泡塞尼阿斯谈到蛮夷时提到的那种狭义的政治利益。“凡把取悦有情人规定为坏事的地方,这种法律之所以得到制定,都是因为那些法律制定者的恶行”。这样的法律源于统治者的贪婪,源于他们不断攫取的欲望,也源于被统治者的缺乏男子气。这个说法极有趣。被统治者,即便是被僭主统治的人,也跟统治者或僭主一样是立法者。这里当然包涵真理的要素,这个要素被现代科学意义上的政治学的某些潮流夸大得如此过分。比如说,本特利(Bently)的政治统治理论认为,不存在纯粹的僭主。受统治的人们总会对统治者施加某些影响。正是在这种观点的鼓动下,泡赛尼阿斯才说,立法者,即便是僭政下的立法者,既有统治者,也有被统治者。在另一种情形中——泡赛尼阿斯在此谈到未开化的希腊人,那里制定的法律是完全高贵的,即没有任何限制——法律被制订是因为立法者灵魂的懒惰。在这里各位看到,泡赛尼阿斯没有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做任何区分。为何?很显然——这些[未开化的]人是共和派(republicans),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区分不存在。他们是真正的自由人。关于男童恋他们怎么说?他们说你想怎样就怎样吧。因此,自由不需要高贵的爱欲。我们看到的另一条证据表明,泡赛尼阿斯企图为男童恋寻找依据的第二个尝试——这次尝试不是凭nous[理智],不是凭理智(intelligence),而是凭自由——也破产了。那么他会在哪里找依据?柏拉图没说,“这是我的价值判断”;每个白痴都会这样说。他会问,你这个价值判断的理由何在?为何说男童恋是好的?法律为何允许它存在?你必须给出理由。有些人想加入男童恋行列,有些人因为男童恋被禁感到难受,这些事实肯定不是改变法律的理由。肯定有好理由存在。给我一个好理由。是理性吗?不是。自由吗?不是。
……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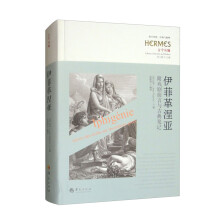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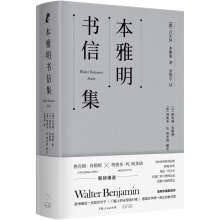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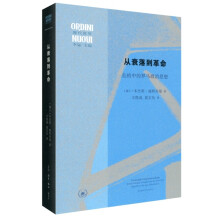
——G.R.F.Ferrari,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
★政治哲人施特劳斯早在1973年就已辞世,时隔一代人之后突然撞见此书,其震惊和意外,不亚于在一座古老的德国教堂的地下室偶然发现一卷巴赫手稿。
——Mark Blitz,Weekly Standa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