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资风云》:
为充饥煞费苦心
曾善才的商业禀赋早在童年时期就异于常人。20世纪70年代初期,10岁的曾善财不过是个三年级的小学生。当班里的其他同学还在跟着老师的指挥整日里把“斗私批修”之类的口号喊得震天响的时候,他已经开始琢磨起如何才能通过与同龄人交换他们喜爱的玩具或铅笔、本子之类的学习用品,以换得自己家里极为稀罕的焦香锅巴或白面馒头了。
曾善才的家住在大河东岸一个小县城的郊区。虽说离县城较近,但在当时中国经济总体水平比较落后的大环境下,他家和千千万万个农村家庭一样,异常贫困,三间低矮的土坯茅草房既昏暗又潮湿。因为堂屋的一角就是土坯垒砌的鸡圈,屋子里弥漫着刺鼻的臭味。好在大队、小队对“割资本主义尾巴”抓得紧,他家也就养了三母一公共4只鸡,否则屋里不知要有多臭。
曾善才的父母带着他年仅3岁的小妹妹善玲住在东边的房内。曾善才和8岁的善兵、7岁的善农、5岁的善田三个弟弟挤在西边房间的一张土坯大“床”上。“床”上铺着厚厚的稻草。夏日里,稻草上面会扔上一块破篾席;冬日里,稻草上会胡乱垫上一床破棉絮,棉絮上再放一条薄薄的黑乎乎的破棉被。夏天还好对付,实在热得不行,他们干脆把席子拿到门外的空地上露天将就一晚。到了冬天,尽管兄弟四人把身上的衣裤一股脑地压在被子上,仍会冻得瑟瑟发抖。迷迷糊糊中,哥几个都竭尽全力把被子往自己身上裹。所以一觉醒来,不是曾善才被冻得肚子疼,就是其他几个兄弟被冻得喷嚏连天。说来也怪,就算这么折腾,小哥几个也很少感冒发烧。
曾善才的家里家徒四壁。堂屋里除了前面提到的那个土坯鸡圈,还有一张东倒西歪、黑不溜秋的小破桌和几块木头墩子、两匹拔秧用的秧马,而木头墩子和秧马是当凳子用的。他父母屋里最贵重的家具就是当年他妈妈结婚时的嫁妆——一只黑乎乎的木箱,几乎别无其他家具。农具倒是有一些,像笆斗、筛子、簸箕之类的日常用品主要堆在曾善才兄弟们住的西屋,稻圈、米缸、面缸则放在他父母住的东屋。然而稻圈里有粮食的时间一般不会超过6个月,也就是从每年的10月到第二年的3月。一旦到了4月,稻圈也就基本见底了。想想每年秋季一家人也就分到一千多斤稻子和一两百斤红薯之类的杂粮,他们这一大家人能够坚持到来年3月底已经相当不易了。为了度过春荒,曾善才的父母只得一方面把每天一干两稀三顿饭改为每天一干一稀两顿饭,把稀饭里的米少放一些,水多放一些:一方面千方百计到野地里寻些荠菜、黄蒿之类能吃的野菜加进稀饭汤里。即使这样将就。仍难免接不上春粮。曾善才的父母只好厚着脸皮端起破瓦盆,东家两碗米,西家两碗面,临时借一点。然而在那个年代,周围比他们家宽裕的邻居很难找到几家。实在没办法了,一家人干脆一天只吃一顿稀饭、一顿野菜汤。
在这种环境中渐渐长大的曾善才最大的奢望就是每天都能吃上饱饭。然而这个愿望对他来说实在遥不可及。饥肠辘辘的曾善才只好找根长麻绳把自己的腰部紧紧地束起来,以便稍稍减轻点饥饿感,然后带领弟妹们到野外觅食。春荒时,他们扛起铁锹满地里挖黄鳝、泥鳅,或者直接把雪白的槐花、嫩绿的豌豆苗大把大把地塞进嘴里。夏天里,他们啪叽啪叽跳进小水坑,试图抓上几只小鱼小虾:或者干脆爬到大树梢上把大大小小的鸟蛋一股脑地揣进兜里;或者到草丛里、菜地里捉蚂蚱、土狗、豆虫之类的小虫子,然后随便在田埂上挖个坑,拣起枯枝烂草放进坑里点着火,将这些战利品扔进去烤一烤,待香气四溢时取出,分而食之……
多年以后,当历经波折的曾善才回忆这段往事时,他印象最深的不是这些野味的鲜香,而是对大米饭和白面馒头的无限向往。有意思的是,当大米饭和白面馒头真正摆在他面前任其取用时,他却再也提不起食欲,反倒无限留恋起槐花的甘甜和蚂蚱的鲜香来。
曾善才的学习成绩与班里的大多数同学差不多,得二三十分是常事,很少有考及格的时候。
……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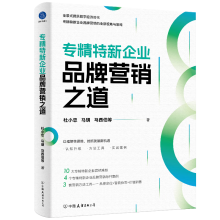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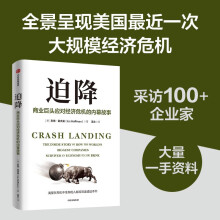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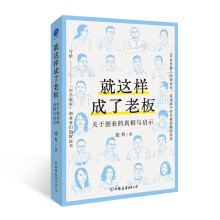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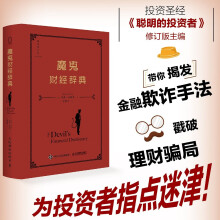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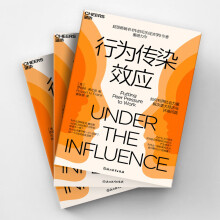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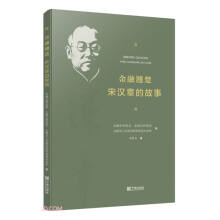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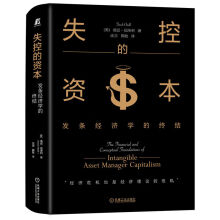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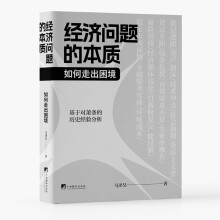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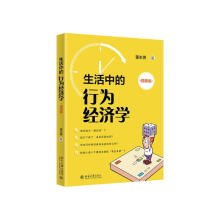
——石生
★笔落惊风雨,书成泣鬼神。
——朱卫文
★不愧文坛实力派,寓情于景,妙趣横生。
——彤丽炜
★一看作者就是企业管理高手,从市场到生产,从财务到供应,门儿清!
——散人
★梦里梦外,爱恨情仇尽有!
——十八帮主
★让人物按照自己的方式思考、说话、做事,让故事按照生活的逻辑发生、发展、变化,小说的本质就是生活与语言的艺术。
——海滨
★看这样的创业史,总有强大的时代烙印,就像一代创业者的胎记,那么清晰,那么引人入胜。没有不好的员工,只有不好的制度。窥此一斑,得知作者心中全豹。
——邹秀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