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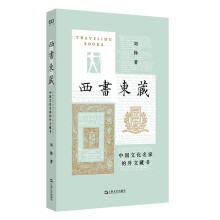






周氏兄弟
一
七十年代末,或者八十年代初,周家的第三代来找过我祖父。一男一女,是周作人的什么人,我一直没弄清楚,可能是孙子和孙媳妇,也可能是孙子与孙女儿。我当时正在读大学,是假期里,他们来了,指名要见祖父,我也懒得细问,把他们送到祖父房里完事。客人走了,才知道他们是周作人的后人,而目的是希望祖父帮忙。帮什么忙,已记不清,好像是为了八道湾的房子。吃饭桌上,祖父和伯父一边喝酒,一边商量这事,我自己的事太多,也没认真听他们说什么。只记得祖父心情有些沉重,因为他吃不准这样的事情,是否应该让周建人知道,周建人知道了又会怎么样。
周建人是祖父的好朋友,当时还健在,他们之间的友谊很漫长,好像在商务印书馆共事的时候就开始了。祖父后来参加民进,最重要的原因,也是老友周建人的劝说,在这之前,祖父一直无党无派,所谓民主人士。不止一个人问过这样的话题,那就是祖父和鲁迅关系究竟怎么样。小时候,我也这么问过祖父。后来书读多了,才觉得这问题可笑。周氏兄弟中,鲁迅要比祖父大许多,周作人也是,即使最小的周建人,也要大好几岁。熟读鲁迅文章的人,一定会记得收在《野草》中的那篇《风筝》,年长的哥哥欺负弱小的弟弟,以后又忏悔,故事叙述得很动人,文章中那个弱小弟弟的年龄与祖父相比,又成了不折不扣的老大哥,因此,以祖父的为人,绝不会僭越说自己和鲁迅如何如何,他绝不会闹出“我的朋友胡适之”这类笑话。祖父的好友俞平伯是周作人的得意弟子,鲁迅和周作人显而易见应该算前辈,是属于师长一辈的人物。
祖父感到心情沉重,是周作人的后人,为什么舍近求远,不去找周建人。这种事,以旁人的眼光看,论家属关系,周建人是叔公,论社会地位,周建人当时是人大副委员长,怎么说都是找他更合适,此时的周建人就在北京居住。清官难断家务事,很多事情说不清楚,祖父是一个极重亲情的人,他自己没有兄弟,因此很羡慕别人的兄弟怡怡。周氏兄弟的失和,差不多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而兄弟之间的关系紧张,尤以鲁迅和周作人之间,最为极端。在现代文学史上,鲁迅和周作人兄弟俩作为不可替代的两座高峰,曾让无数的文学青年仰慕,他们的反目,老死不相往来,这种紧张关系不仅在生前,死后也影响到了各自的后代,鲁迅和周作人的后代之间,一直没有来往。鲁迅的孙子周令飞曾写文章披露,说周作人逝世以后,给周海婴寄去了讣闻,海婴考虑再三,没有参加追悼。
二
周作人在妻子死后半年多,写下了这么一段话:
余与信子结婚五十余年,素无反目事。晚年卧病,心情不佳。以余弟兄皆多妻,遂多猜疑,以为甲戌东游时有外遇,冷嘲热骂几如狂易,日记中所记即指此也。及今思之皆成过去,特加说明并志感慨云尔。
读周作人的晚年日记,可以发现许多夫妻不和睦的蛛丝马迹。周作人老婆是日本人,在中国人的传说中,日本老婆以贤惠闻名,但是信子却给晚年的丈夫,带去了连绵不断的烦恼。周氏三兄弟中,除了鲁迅早逝,周作人周建人都长寿,周作人死于“文化大革命”,若没有这场风暴,他很可能继续活一段时候。晚年的周作人,除了饱受政治运动的惊吓,老夫妻之间的吵架也是常事,当然主要是信子的胡搅蛮缠,所谓冷嘲热骂,最过分的便是大打出手,斯文扫地。这种无休止的纠缠,既多而且凶猛,难怪他要发出“苦甚矣,殆非死莫得救拔乎”的感叹,甚至生出“临老打架,俾死后免得想念,大是好事”的歹毒念头。周作人行文一向以平淡著称,在日记中,这类记录虽然仍有节制,有时也接近呼天抢地,恶意图穷匕见。他显然意识到自己的日记,有一天会变成读物,一日夫妻百日恩,夫妻间的事情,别人永远闹不清楚,因此专门写下一段文字,留作日后为信子辩护的依据。
这段文字的要害,于信子是撇清了,却牵扯到了周作人年长四岁的哥哥鲁迅和年幼四岁的周建人。周建人的前妻是信子的妹妹芳子,换句话说,信子既是周建人的嫂子,又曾是他的大姨子。夫妻性格不合,中途分手本是很正常的事情,信子站在妹妹一边,反对周建人也在情理之中。芳子和周建人分居以后,一直和周作人夫妇生活在一起。这姐妹俩谈到已在外面又和别人结婚的周建人,自然不会有什么好话。
至于鲁迅,大家都知道有个朱安夫人,鲁迅和许广平同居之后,朱夫人和鲁迅的母亲鲁瑞老人,一直留在北京。抗战初期,周作人不肯南下做义民,后来又落水做了汉奸,其中有一条很无聊的借口,是有老母和寡嫂要抚养。这借口很难站住脚,又确实能蒙住一些人。其实自从鲁迅逝世,母亲改由周作人抚养,可以说天经地义,本来养老应该是所有儿子的共同义务。鲁瑞和朱夫人并不住在八道湾,八道湾的房子虽然是以鲁迅的名义登记,自鲁迅搬出以后,这里就成了周作人的天下。此外,查一下日期也就明白了,鲁迅是一九三六年死的,在这之前,母亲的费用一向都由他这个做老大的独自负担,死后,经济上做了安排,北新书局每月拿出三百元来,二百元给上海的许广平和海婴,一百元给北京的鲁瑞和朱夫人。抗战爆发,南北交通阻隔,接济时时中断,周作人才从一九三八年的一月开始,每月给母亲五十元,区区五十元对大名鼎鼎的知堂老人,又算什么。
一九三九年一月,周作人收下了北大任命他为图书馆馆长的聘书。此时的北大已是伪北大,这一步迈出去,犹如尝了禁果,荡妇初次接触男人,想回头也难。接下来,一发不可收,官越做越大,水越陷越深,一九四二年鲁瑞老人去世,周作人大办丧事,共用去一万四千多元。当时的钱急剧贬值,即使贬,这钱也太多了。如此隆重的葬礼,与其说体现了周作人的孝心,还不如说显示了他当时的得意。周作人写了一辈子好文章,此时却栽在了官迷心窍上,以周作人的学识,他如何不知道一个文化人下水的后果,但是仕途这剂春药,对知识分子的诱惑实在太大,一旦沾上,和吸毒也没什么太大的区别。不妨想想他当时是如何阔绰和威风,那个平淡出世的知堂老人,突然形象全变了,穿狐皮衣裘,三天两头上馆子,小孩过生日,光犒赏佣人就两桌,家里奴仆最多时,竟然有二十三个人之多。
周作人做汉奸时表现出来的官场得意,是很多热爱苦雨斋文字的人不堪回首的一个噩梦,你无法想象自己倾心的一个作家,竟然会做出如此不明智的选择。记得有人专门做过这样的文章,把周作人下水当“督办”,说成是中共地下党的安排,由此证明周作人差不多是准“特工人员”。这种为周作人极力辩护的用心,也许是好的,可惜有些离谱,改变不了历史原有的记录。我曾见过日本友人清水先生的文章,说在这特定时期的一次聚会上,曾见到过已做了大官的周作人,说他穿着缎子袍褂,像过节一样,神采奕奕地坐在前排。沐猴而冠,对知堂老人来说,是最残酷的讽刺。这样的聚会,自然是当时的日方安排的,周作人倒是敢作敢当,实事求是地说过自己为什么要下水:
关于督办事,既非胁迫,亦非自动,当然是由日方发动,经过考虑就答应了。因为相信自己比较可靠,对于教育,可以比别个人出来,少一点反动的行为也。
比别人少一点反动,这大约也是事实,欣然从命,更是事实。为了短暂的荣华富贵,既留下一世骂名,还实打实地坐了牢,真不值得。在本世纪,知识分子坐牢常可以成为一种革命资本,然而周作人似乎活该,想翻案也翻不了。做汉奸好比淫妇偷人,小偷偷东西,无论什么充足的理由,别人都不会同情。用“小事聪明,大事糊涂”来形容周作人,也许最恰当不过,在是否“下水”这件大事上,他糊涂了,在记日记这种小事上,又太清醒。周作人只用了轻描淡写的一句“以余弟兄皆多妻”,不仅为妻子信子做了辩护,而且把所有过错轻轻一推,都推到了自己弟兄的“多妻”上面。周作人相信日后愿意读他日记的人,都是些熟悉周家家事的读者,这里面的微言大义,不说自明。
……
叶兆言的性格为人绝对是儒家的,他是一个真正的读书人,满腹经纶,优雅随和,身上散发出某种旧文人的气息。
——苏童
如果不是大量阅读文学史、文化史、艺术史、人物传记及书函、日记,如果不是大量阅读哲学、美学、外国文学史艺术史以及通俗性的文史读物,叶兆言的散文绝不可能有如此的博识。
——吴周文、张王飞
叶兆言这类文字,似野史而非野史,似信史又多传奇,外被锦绣,内含翠羽,简约处一笔带过,丰富处不吝笔墨,文字功夫几臻炉火纯青。通过它们,叶兆言努力探讨现代知识者和文化人的人格、心灵与性情,力求还原历史人物,揭示人性弱点,藉以反思历史和现实,呼吁良好的人文生态。
——张宗刚
叶先生的文章很能打破之前对某领域大家的过高仰视,在零碎的片段中会发现其实大家也是普通人。
——读者 澜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