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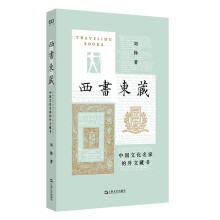






84岁的铁扬先生专职绘画,近年陆续发表了不少散文及小说。本书收入他多篇散文近作,内容包括:童年故乡风物描绘、个人回忆(包括童年生活记忆、从医经历、文工团生活及“中戏”求学经历)、人物描摹(父兄、乡亲及师长)和对几位画家及作品的艺术随感。是一位老美术工作者,在长期以来积累的对绘画以及艺术的点滴发现、感悟以及对人生、乡土、生活本质的思索的基础上,用文字做出的勤勉、诚恳的记录。这些作品细腻、真实,饱含情感。作者自述写作的原因是心中的故事太多。作者用经过训练的眼睛观察生活,所以他的文字有着独特的面貌。
湖畔诗
一
那时,我毕业于省内一所卫生学校,属中专。在临床科学习时,老师让我注重妇科。毕业分配时,人事部门又问我,愿不愿意当司药,说,当司药可以留城。我想了想说,可以。
留城还是有吸引力的。是许多同学争取不到的。再说,学医的分科是要由毕业后的实习所决定。我们并没有经过实习,对于专业对口不对口也就无所谓了。再说我对妇科的认识“注重”还仅停留在书本纸面上;从解剖图上看,女人的子宫像个切开的梨,卵巢像只怪蝴蝶。至于妇科那些更“深刻”之处,对我还是神话一般。这样,我就留城在一个不小的单位医务室当了司药。现在我与面前的瓶瓶罐罐、药粉、药片打交道。只待有女性患者凭处方取药时,我才有意无意地把她们暗藏在体内的脏器和我的书本知识相“对照”。这时,我常感到我内心的不洁。
单位的医务室,只有我和一位姓李的医生两个人。但我们所处的空间不小。我们把这间空旷的大屋子用布幔分割成了几个小空间,每个空间都有自己的专门用途。我站在属于我这块空间里,面对那一排被我擦拭得干净的橱柜,心想,大医院也不过如此吧。
李医生是一位很有阅历的西医,他做过军医。但他在叙述他的军医生涯时显得有点混乱。他说,一次有件事他让小鬼去报告指导员,小鬼朝他打了一个敬礼去了。小鬼、指导员这当然是革命军队中的称谓了。小鬼通常是指为领导服务的警卫员或通讯员。有时他又说,一次,他让勤务兵深夜十二点到劝业场买元宵,勤务兵也朝他打了个敬礼去了。勤务兵当然是另一种军队中的称谓。而劝业场在天津,天津当时是敌占区。有一次他还说,一位慰安妇找他看病。他用日语和她说话,慰安妇听不懂,原来这慰安妇是朝鲜人。还讲了这位小慰安妇不少细节……
这位高挑个子、鼻子修长、眼窝深陷看上去有几分西亚人血统的李医生,现在正值中年,且无家庭拖累,一个人独来独往。
我尊重李医生,因为他像我心目中的医生,不论他那一尘不染的衣着,还有文雅的举止,就连他洗手也带着极严格的职业特点:手心手背搓擦几遍,然后又叉开五指,双手交叉又一阵揉搓,连指甲都不放过,最后用净水把手冲了又冲。李医生告诉我洗一次手有六道程序。至今他开处方还用拉丁文,他把拉丁文写得龙飞凤舞。虽然用拉丁文开处方已被废止,但李医生用。他说病人看到拉丁文从心理上已经得到安慰,你用中文写“苏打”就不如用拉丁文写“nitrum”;你用中文写“磺胺”就不如用拉丁文写“sulfonamides”。拉丁文之于病人是一种必要的心理暗示。我赞成李医生的观点。我认真解读着李医生天书般的处方,和李医生准确无误地做着配合。
只有一点我对李医生心有疑虑,便是他对女患者的过分关照和“瓜葛”。在属于李医生的空间里他和女患者没完没了地“搭搁”,他本是正统的西医,却弄起了号脉、按摩、推拿一类。这使得他有更多的时间在患者的身上安抚、弹拨。他还与患者聊些与疾病无关的话题,诸如对蜂窝煤炉子的改造;用买脸盆的小票能在哪里买到水壶,的确良和棉布哪种织物优越。有时他还和女患者聊织毛衣的针法,我猜李医生并非织毛衣的内行,但他能说出不少针法和花样:诸如太阳花、萝卜花、玉米花还有大阿尔巴尼亚、小阿尔巴尼亚……女患者也津津有味地附和着,她们的笑声不时从李医生的空间升起。
二
买东西凭小票,改进蜂窝煤炉子,毛衣的针法都联系到阿尔巴尼亚。这是一个特殊的年代,当时有个“三年自然灾害”的说法。国外有帝、修、反来和我们作对。地球上除了中国这盏“社会主义明灯”,远处只有一个阿尔巴尼亚国也点着一盏“社会主义明灯”,这使得我们不得不饥肠辘辘地和一个阿尔巴尼亚肩并肩地迈着前进的脚步向前走——“我们走在大路上”,像那首歌里唱的。于是,阿尔巴尼亚的毛衣针法也不远万里传过来。刚才我就是从单位礼堂听完政治报告走出来,领导在报告中先讲了目前形势、讲“三年自然灾害”,又再次强调了帝、修、反的存在,然后说,现在我们的生活已进入到一个“低指标、瓜菜代”的时代。低指标是国家配给每个人的粮食指标要降低,“瓜菜代”是号召大家以瓜菜代粮。还说目前这点困难要大家克服,谁也不要忘记地球上还有四分之三的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中,这四分之三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人还要等我们去解放,虽然我们是低指标瓜菜代。
我从礼堂出来拐进食堂去打饭。我的同志们已先我一步排起长队,拿饭盆的,拿饭盒的,拿钢精锅的。人们穿得很厚,有人穿着棉猴戴着帽斗儿,显得队伍十分拥挤,谁也不提刚才听报告的事,只搓着手、跺着脚、哈着气等打饭的小窗口打开。小窗口终于打开了,一股热浪从里面冲出来,把一个冰冷的食堂冲击得热气腾腾。人们开始把一张火柴盒大小的饭票递进去,把属于自己的那份饭食打出来。不久我也打出了我那份以菜代粮的饭食,往宿舍走,路过传达室时,传达室师傅递给我一封信。这是一封来自老家的信,白报纸做成的信封上印着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戏装画。写信人是我的堂叔向老宽。
我回到宿舍,先捅开炉子,守着炉子吃饭看信,今天的饭食还好,除了两个甘薯面包着的榨菜团子,还有一块“人造肉”。在此,我应该把人造肉做一介绍,因为它体现着我国人民在这个特殊时期的一项重要发明创造:这是由薯类和碾碎的玉米秸秆发酵而酿成的糕状物,一面涂着酱红色模仿肉的外形,更有能人在“肉”的侧面用颜色分出层次——五花肉似的。目前我们单位全体职工分成班组,正轮番着制造。在一个地窖里,摆着各种容器——瓦盆、脸盆、碗盘都有,再把所需原料填进去,让其发酵。现在我们这个班组的“造肉”工程,正在窖内实施中。
两个榨菜团子,也并非真正的榨菜,那是生长在我们这个城市东面大淀里的金鱼草。吃这东西能使人忘记自己的属性,想到的是牛、羊、驴、骡和水中的鱼类。但我们吃——我们时刻牢记“低指标,瓜菜代”的口号,这里有最高领袖的最高指示的含义。领袖就有过“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必要时还要“杂以瓜豆”的语录。虽然现在的形势已不是多吃少吃的问题,瓜豆也成了稀奇,但领袖的语录仍在鼓舞我们。大家以坚定的信念吃着盘中餐。
我吃着“人造肉”看信。信,确是老宽叔的笔迹,他识字,先前他在城里上过“高等”。他在信中叫了我小名后以自己的口气叙述道:恁(你)家那几间没人住的老西屋,前几年生产队喂牲口占着。现在牲口被社员杀着吃了,房子也没人管了,快塌了,卖了它吧!时下咱村东头王老五的儿子当兵复员回来要娶媳妇买房,这也是一个机会。有机会咱就该利用。房塌了就不如卖了。信中还说我们弟兄三人我最小可离家最近……老宽叔说得对,我的两位哥哥都是“三八”式干部,后来都南下任职。此事当然就落在我的头上。
面对信的内容,我困惑了好几天,回家卖房,在目前这当是一件不光彩的事,它不符合我们“走在大路上”的雄心壮志。这是一条不光明的小道。可又想到老宽叔“塌了不如卖了”这句话,我决定去和李医生商量。我把老宽叔信的内容告诉了李医生,没想到李医生赞同老宽的观点,他说话简单,他连着说了两个“卖”“卖”,又说“不卖白不卖”。不过他提醒我一定要到单位人事部门请假说明情况。最后,我受了李医生的鼓励羞羞惭惭地来到人事部门说明情况。人事部门领导说,你不是党员卖房自己负责。党员可不行,要受党纪处分,这行为纯属资本主义,复辟资本主义正是我们要提防的。“你没有听过报告?你看全国人民正在意气风发地干什么!你的行为又算什么!”面对领导的一席话,我面红耳赤地呆立半天,还是依老宽叔和李医生的话为指导向领导表态说:我愿自己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