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新耶路撒冷
1925
“费拉德尔菲亚和朱比莉!”当海蒂说想给他们的双胞胎宝宝取这两个名字时,奥古斯特大呼:“你怎么能让咱们的孩子们叫这么离谱的名字呢!”
倘若海蒂的母亲还在,她也一定赞成奥古斯特的想法。她会说海蒂起的名字太粗俗了,“又恶俗,又惹眼”,她会这么评价。可她毕竟已经不在了,而海蒂想给他们起一个在佐治亚州没人叫过的名字。于是,她起了这两个充满希望,永远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的名字。
这对双胞胎出生在六月,在海蒂与奥古斯特结婚后的第一个夏天。他们在韦恩大街租了间房子——房子虽不大,但周围的环境还不错,而且用奥古斯特的话说,这只是暂时过渡用的。“等买了属于咱们自己的房子就好了。”海蒂这样说。“嗯,咱们一买到房子就搬走。”奥古斯特也同意。
六月末,知更鸟占满了韦恩大街的树顶和屋顶。住宅区里到处是鸟儿欢唱的声音。每天,双胞胎宝宝在鸟儿的欢唱中入睡,海蒂的心情也欢快无比,成日脸上挂着微笑。每天上午总会下雨,到了下午阳光便出来,把海蒂和奥古斯特的家照得明灿灿的,他们家门前不大的草地里,小草绿得清脆,像是第一天来到这个世界。街道上邻居家的女主人们早早就开始烤面包了,到了中午,她们就会把面包晾在窗台上,每每这时,整个街道上便处处散发着草莓面包的香味。海蒂和她的两个宝宝,他们三人在门廊的阴凉处打盹儿。海蒂想着到了明年的夏天,费拉德尔菲亚和朱比莉就能走了。他们会摇摇晃晃地沿着门廊迈步,像两个可爱的小老头。
海蒂·谢泼德望着她襁褓中的两个宝宝,他们七个月大了。他们坐起来呼吸会好一些,于是她给他们垫了个小枕头,两个孩子立刻安静了。这个晚上过得很不好。肺炎是可以治愈的,虽然并不容易,但总归要比腮腺炎、流感,或胸膜炎要好些,也总比患上虎疫或猩红热要好。海蒂坐在洗手间的地板上,身体靠在坐便器上,双手抱着腿。水蒸气模糊了窗户,它们渐渐凝成水滴,沿着窗棂滑过白色的木框,顺着下面的瓷砖缝隙流下。海蒂已经放了几个小时的热水了。奥古斯特今晚大半宿都要在地下室给热水炉子添煤,他本不想离开海蒂和孩子去上班,可是……干一份活儿就有一份报酬,而且煤储藏室里人手也不够。海蒂向他保证:过了今晚,孩子们就会好起来的。
前天医生来过,他建议用蒸汽疗法,然后开了一小剂吐根树糖浆,并告诫他们不要用农村里落后的土办法,比如用滚烫的芥末膏疗法,不过热敷是可以的。他用一种清透油亮的液体把吐根树糖浆稀释后,交给海蒂,给她示范如何用手指头压住孩子的舌头,好让药水直接流到喉咙里。奥古斯特付给医生三美元,医生一出门他便开始弄起了芥末膏。唉,肺炎。
小区里不知何处有汽笛在哀嚎,声音如此剧烈,想必是在他们家房子前了。海蒂吃力地站起身,将洗手间窗户上的雾气擦出一个圆。街上什么也没有,唯独一排排白色的房子,还有人行道边灰色的雪堆,以及将要冻死的幼树苗,在它们方寸间的冻土里各自挣扎。楼上的窗户里,星星点点亮着灯光——街区里有些男人做着跟奥古斯特一样的工作,有的送牛奶或者送报纸。这里还住着学校的老师,还有许多其他的从业者,海蒂对他们便一无所知了。在整个费城,人们都顶着严寒,一大早起来到地下室添煤烧炉子。在这种艰苦的状态下,人们是比较团结的。
天边渐渐破晓,黎明来了。海蒂睁开双眼,她记起儿时的日出——那些景象总在牵动着她,随着她在费城居住的时间越久,对佐治亚州的记忆与想念便越发急切。少女时期的每个早晨,海蒂都是在清晨的工作号角声中醒来,那时天刚蒙蒙亮,号声响过田地、房屋,还有那群黑色的橡树。海蒂躺在床上看着一双双劳作的手从她的窗前掠过。通常动作迟缓的人们会在第一声号角响起后就会经过她的窗前:孕妇、病弱或残障人士、那些老得走不动的、那些背着娃娃的……号角声像鞭子一样,驱赶着他们前行,它严肃了整条街道,严肃了他们的脸。白色的田野正敞开胸怀等待着,采摘的人们霎时间像蚂蚱一样散布开来。
海蒂的两个宝宝微弱地朝她眨着眼睛,她分别挠挠他们的下巴,再过一会儿她该给他们换芥末膏了。浴缸里放着热水,蒸汽盈满了房间,她又添了一小把桉树叶。在佐治亚州,海蒂家前面的那片树林里就有一棵桉树,不过,这种树扛不住费城的冬天。
三天前,宝宝们的咳嗽加重了。海蒂在身上裹了一件大衣,就跑到彭妮水果店去问老板哪里能找到桉树。老板告诉她在几个街区以外的一栋房子里有。海蒂刚来德国城,在这横七竖八的街道里,不一会儿她就迷路了。当她最后找到那栋房子的时候,身上已冻得发紫了,她花了十五美分才从一个女人手里买来一袋桉树叶。而这,在佐治亚州不需要花一美分她就能够得到。“啊,你年纪还很小啊!”那个卖桉树叶的女人说,“你多大了,丫头?”这么问让海蒂有些不高兴,但她还是答了她十七岁,为了让这女人不要把她当成从南方来的难民,她特意多说了些,她说她结婚了,老公正在上电工的培训课,他们刚刚搬到韦恩大街。“哦,挺不错的,亲爱的。你们家的人都在哪呢?”海蒂迅速眨眨眼睛,使劲吞了口口水,“佐治亚,太太。”
“你在北方这儿没亲人吗?”
“我姐姐在,太太。”她没有告诉这个女人,她母亲在一年前当海蒂怀着身孕的时候便去世了。海蒂的妹妹珍珠,觉得在北方顿时变成了孤儿和外地人,受不了母亲去世的打击,回到了佐治亚。她的姐姐玛丽恩也一同回去了,尽管那时候姐姐说过,等她生下孩子就立刻回来。然而,冬天都要过去了,海蒂不知道姐姐还会不会来。这个女人仔细地端详海蒂。“我跟你一起回去看看你的小可爱吧。”她说。海蒂谢过了她的好意,她是个天真的傻姑娘,她太过骄傲地否认了自己其实需要这个女人来看看孩子。她独自一人回了家,手里紧握着那袋桉树叶。
冬天的空气像火一样包围着她,将她所有的杂念烧得一干二净,她的心中只有一个信念,要把她的孩子们治好。她紧紧攥着这个棕色的纸皮袋,手指头冻僵了。她冲向韦恩大街上他们的家,头脑无比清醒。她感到自己能看进宝宝们的身体里,穿过他们的肌肤、血肉,直直地进入他们的胸腔,看见他们那疲倦的肺。
海蒂将费拉德尔菲亚和朱比莉挪得离浴缸更近一些。她新添的桉树叶有点多了——孩子们受不了这薄荷味儿的雾气,紧闭起双眼。朱比莉攥起小拳头,举起胳膊,仿佛是要擦擦流眼泪的眼睛,可是她太虚弱了,她的手臂又落了下来。海蒂跪下来,亲吻她的小拳头。她拿起女儿无力的手臂——轻得竟像小鸟的骨头——用朱比莉自己的手拭去了她的眼泪,倘若她有力气,她一定是想这么做。
……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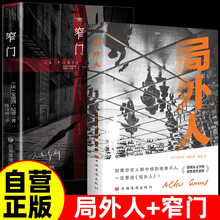

——奥普拉
“《十二族》从第一句话开始,文字便十分优美、简洁。文中所表现的人物谦虚、伟大、堕落,然后又被救赎。跟进他们的故事是让人心痛的过程,阅读这本小说要本着宽容,本着希望,本着怜悯,本着爱的精神去体会它。阿亚娜·梅锡斯的作品是小说中的珍宝。”
——普利策小说奖《修补匠》作者保罗·哈丁
“《海蒂十二族》生动有力地描写了一个家庭由于生活的种种磨难而导致家人无法团聚,家人的心却仍然紧紧团结在一起的故事。小说的语言优美,不做作,纯正,严密。人物角色各个性格鲜明,作者用审慎的态度将他们逐一刻画。这部处女作表现出了鲜有的成熟度。”
——玛丽莲·罗宾逊
“很精彩……成千上万的希望与挣扎中的非洲裔美国人中,生活着这样一个坚强的能屈能伸的女性。是他们为这个国家带来了希望。”
——《华盛顿邮报》
“一部很有力量的小说……梅锡斯女士让我们窥见了人类精神中那个挥之不去的,充满希望的救赎与反抗的可能性。”
——《纽约时报》
“梅锡斯用无比精准的语言与莫大的勇气阐述了海蒂的九个孩子(以及一个外孙女)的戏剧性的生活片段,表现了大迁徙时期的人们破碎的梦想与痛苦的历程。梅锡斯的描写深入到性、婚姻、家庭关系、骨气、欺诈,以及种族歧视,书中的人物各个历经磨难,饱受沧桑,却仍然坚持对生活的信念,他们的生活仍然充满美。”
——多娜·斯曼,《推荐书目》(特别推荐)
“非常精彩……梅锡斯充满自信地挥洒着她的文字,她证明了自己是个十分强大并极具天赋的作家。”
——《出版人周刊》(特别推荐)
“刻骨、感动……心碎……梅锡斯采用了托妮·莫里斯的一些富有事情的语调,而她自己的描述语言也十分接地气,流畅自如,真实而不华丽,本书的结构非常有创意……很棒的处女作品。”
——《科克斯书评》(特别推荐)
“这部小说语言直接,却又不失诗一般的话语,情节环环相扣……我们可以感受到重新来过给人带来的兴奋,人类对于归属感的最基本的需求,以及那个永远在牵引你回去的,家。”
——《VOGUE》
“文笔优雅自如……这部小说讲述了我们对快乐的渴求的同时,也讲述了我们逃离痛苦的挣扎。”
——英国《卫报》
海蒂作为阿亚娜·梅锡斯书中的标题人物角色,是一个鲜明的悲剧角色,她的性格特色展现是多方面的,她是一位一直在努力实现自己梦想的母亲与妻子。她的故事发生的背景是在20世纪的费城,小说讲述的是痛苦的失去、悲伤与存活,一部讲述在失望、伤心与痛心遭遇面前的忍耐。多少愤恨与梦想传了一代又一代,多少儿女在不经意地重蹈他们父辈的路子。
——《纽约时报》专职书评人 角谷美智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