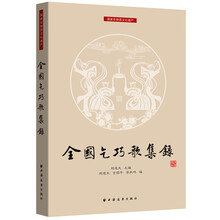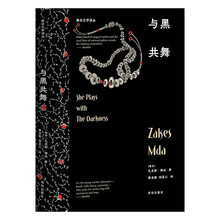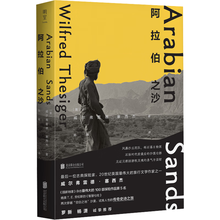凯特·肖邦的作品美,不仅美在爱,还美在死。如果我们把爱看做一条永恒和谐的生命之线的话,那么死,尤其是那么高贵而美丽的死,就如镶嵌在这生命之线上的闪光珍珠。“死亡是此在的最本己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存在,就为此在开展出它的最本己的能在,而在这种能在中,一切都为的是此在的存在。”死亡是每一个人自己的事,一个人对待死亡的态度,是区别于他人最本质的可能性。凯特·肖邦用诗性的语言,为我们描绘了一个个区别于他人的、能够表明自己的本质的死亡。如《谢瓦利埃医生的谎言》中那个美丽纯朴的女孩的举枪自杀,《智胜神明》中波拉的母亲在音乐激发的回想中悄然而逝,《黛丝蕾的婴孩》中的黛丝蕾怀抱孩子的投湖而亡,还有《觉醒》中的爱德娜的裸身投海而去等等。
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些女子的存在,更不用说去描写她们的死亡。当她们死后,又有谁会在乎这些不再活着的边缘人的欢乐和悲伤?有多少人能站在她们的立场为她们说过话?人们总是把她们的名字与弱者相连,人们会讴歌海明威的举枪自杀,可是这无名女孩的举枪自杀,难道不更体现了一种壮美与悲怆?让我们再次回顾一下,爱伦·坡在他的《创作原理》中曾经说过的话:“人世间最伤感的莫过于死亡,而美丽的年轻女子的死亡更让人痛彻心骨。”尼采也说:“最高贵的美是那种渐渐渗透的美,人几乎不知不觉把它带走,一度在梦中与它重逢,可是在它悄悄久留我们心中之后,它就完全占有了我们,使我们的眼睛饱含泪水,使我们的心灵充满憧憬。--在观照美时我们渴望什么?渴望自己也成为美的:我们以为必定有许多幸福与此相连。--但这是一种误会。”
逝者离去的方式,常常反衬生者活着的价值有无、美感的存在与否,这似乎是一个沉重的话题,也是一个不能不面对的问题。上述提到的4位女子的死亡,让我们反思自己的人生。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对本属于自己的死亡常常采取逃避的态度。一个人如果在世俗的生活中丧失了个性,他往往意识不到自己的存在。他会忘记自己是一个必死的生物,一直等到临死时才恍然大悟。可是《谢瓦利埃医生的谎言》中那个无名的女子却不是这样的,她有着与海明威一样的直面惨淡人生的豪情,也如莎士比亚一样洞明生死的真相:“说实话,我一点也不在乎:人只能死一回,咱们都欠上帝一条命;不管怎么样,反正今年死了,明年就不会再死。”所以她积极面对死亡,以一种超然的态度去迎接它,“把死亡当作一种美的事物来接受”。也留给了我们以高贵震撼的美感--“质本洁来还洁去”。她的死让我们饱含泪水,让我们的心灵充满憧憬,希望我们的存在是美的,希望我们的死亡也会是美的。“人不是为了忍受失败而被打造的。一个人可以被毁灭,但是不能被打败。”18、19世纪的西方世界,科技迅猛发展,不仅改变了人的生存方式,使人的思维方式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世界变得冰冷,人变得物化。资产阶级的科学文明虽然带来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但却造成了人的心灵的枯竭,吹散了人生诗意的芬芳。正如尼采所说:“这种无人性的齿轮机和机械以及劳动者的‘无个性’和‘劳动分工’的虚假经济性使生命成为病态。”来自诗意芬芳的乡村的淳朴女孩,不愿让自己的生命成为病态,不愿接受科学文明带给人的异化,宁可举枪自杀。人本尘土,还归于尘土,质本洁来还洁去。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