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一开出一树好花
【原文】(1)
爱问:“‘在亲民’,朱子谓当作‘新民’,后章‘作新民’之文似亦有据。先生以为宜从旧本作‘亲民’,亦有所据否?”
先生曰:“‘作新民’之‘新’,是自新之民,与‘在新民’之‘新’不同,此岂足为据?‘作’字却与‘亲’字相对,然非‘亲’字义。下面‘治国平天下’处,皆于‘新’字无发明。如云‘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如保赤子’,‘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之类,皆是‘亲’字意。‘亲民’犹《孟子》‘亲亲仁民’之谓,‘亲之’即‘仁之’也。‘百姓不亲’,舜使契为司徒,‘敬敷五教’,所以亲之也。《尧典》‘克明峻德’便是‘明明德’,‘以亲九族’至‘平章’、‘协和’,便是‘亲民’,便是‘明明德于天下’。又如孔子言‘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便是‘明明德’,‘安百姓’便是‘亲民’。说‘亲民’便是兼教养意,说‘新民’便觉偏了。”
【原文】(2)
唐诩问:“立志是常存个善念,要为善去恶否?”
曰:“善念存时,即是天理。此念即善,更思何善?此念非恶,更去何恶?此念如树之根芽,立志者,长立此善念而已。‘从心所欲,不逾矩’,只是志到熟处。”
“精神道德言动,大率收敛为主,发散是不得已。天地人物皆然。”
王阳明毕竟不是生在普通人家的孩子,说他生在大明王朝第一流的官僚家庭也不为过。他的父亲王华是成化十七年(1481年)辛丑科状元,到正德元年(1506年)已经担任礼部左侍郎,成为内阁辅臣候选人之一。
王华,字德辉,号实庵,晚年又号“海日翁”,曾在龙泉山的寺庙中读书,故后人尊称他为“龙山先生”。
天顺六年(1462年),十七岁的王华以“三礼”参加院试,辞章优秀。阅卷的官员不相信如此干净漂亮的文字出自一个乡间少年之手,于是对他进行复试。复试中王华一挥而就,所作文章依旧不凡。阅卷的地方官员不禁大为感叹,认定此子他日必大魁天下。
从此之后,王华名声大噪,远近富户大族都备下厚礼,登门邀请王华教育自己的子弟。
成化初年,浙江学政张时敏在对余姚的一帮士子进行仔细考校后,做出一个大胆的预测。他说:“谢迁与王华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们将来都是状元的料,前途不可限量。”
果然,谢迁后来成为成化十一年的状元,日后终成一代名辅;而王华则是成化十七年的状元,只是遭遇刘瑾之祸而未能实现自己的志向。
宁良当时是掌管浙江一省民政的布政使,他想要为子弟挑选一位好老师,于是便请浙江学政张时敏推荐。张时敏说:“浙江士子之中,学业优异者不在少数;若只是为子弟的举业择师,可推荐的也不少;若论学品兼优,最堪为人师表者,非王华莫属。”宁良欣然采纳了张学政之言,礼聘王华为师。
宁良的老家在湖南祁阳,王华受聘后便被安排住进了宁家的梅庄别墅。宁良出仕前曾在这里读书,当时别墅里还有数千卷藏书,这让一心好学的王华大喜过望。王华白天用心授课,晚上则博览藏书。虽然他在当地待了三年多时间,但从来没有进过城。如此刻苦勤奋,学问自然愈加精进,于是被人戏称为“五经司令”。
当时在祁阳士子中,嫖妓酗酒之风盛行。王华虽然孤身在外,但是他从未放纵过自己。在他结束聘期要回浙江时,当地士子为他在江边亭楼设宴饯行。
宴席一直持续到后半夜才结束,所有人都醉醺醺地离开了,只剩下王华被安排在楼中留宿。待王华进入楼中,刚要宽衣就寝,恍惚间就发现两个美貌的年轻女子坐在帐中。他虽有几分醉意,但仍能自我克制,可他刚要转身退出,发现门不知何时已被死死锁住。
两个女子向他走来,王华作势将她们推开,可对方扭着腰肢又黏了上来。“读书的种子”平日里只知道读圣贤书,从未经历如此不堪的场面。情急之下,王华破窗而出,卸下一块门板掷入江中,然后跳上门板,连夜渡江而去。那帮等着看好戏的人不由得投来惊异和赞叹的目光……
成化十七年(1481年),王华高中状元,被授为翰林院修撰。没过多长时间,他又被皇帝任命为每日进讲的日讲官。每次进讲,他都要高声朗语,言辞贴切。当时负责向皇帝进讲的官员有好几位,有的在进讲前会不眠不休准备很长时间,生怕没有做足功课出了差错。
明朝的官员俸禄是很低的,如果没有灰色收入,很难应付在京城做官的开支,尤其是交际方面的开支。一个京官要想在京城混得顺风顺水,需要付出的往往是俸禄的数倍或数十倍,乃至上百倍。低品级的京官大多是没油水可捞的职位,而支出又相对较高,所以京官中的大部分人都生活得很清苦,整日巴望着被外放的机会。
王华在物质方面没有过高的要求,生活十分节俭,且应酬往来极少,面对清苦的生活也能安之若素。好在朝廷不时给些额外的奖赏或补助,这样王华总算可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
十一岁的王阳明被父亲带到了京城,并在他的严厉监督下接受儒家传统教育。通常情况下,伴随着这种教育的是先生的戒尺和家长的棍棒。父亲王华告诉他,这样的教育对个人和国家都是很有必要的。王阳明虽然心怀不满,但也只能接受。
父亲王华像是看管犯人一样敦促王阳明做功课,这让王阳明叫苦不迭,也让他无限怀念和爷爷在一起的快乐时光。在王阳明的作息时间表上,除了睡觉和吃饭,其他时间都要用来学习。他的生活就是背不完的四书五经,写不尽的八股文章。王阳明能够感觉到,父亲看自己的眼神里充满了焦虑和怀疑。焦虑是因为他脑子里那些乱七八糟的想法让父亲无从把握,而怀疑则是因为他不相信王阳明能够自觉地学习,成长为一个令他满意的读书人。
王阳明虽然置身于父亲王华所营造的紧张的学习氛围中,不过有爷爷在旁宠护着,还是有机会忙里偷闲。与父亲王华相比,爷爷王天叙在子女的教育问题上显然要宽容许多,他既可以接受一个坚守传统儒学的儿子,又可以接受一个天马行空、不按常理出牌的孙子。
在不多的空闲时间里,王阳明为了让小伙伴们都跟自己玩,便省下自己的果品、点心,拿给伙伴们分享。王华得知儿子此举后,也不免大为赞叹,如此年纪就能克制私欲以遂其志,实在难得。
据说,王阳明小的时候就有了做圣贤的想法。虽然这时他的圣贤理想还不够真实,但是可以看出,他为自己谋划的人生路径迥异于大部分同龄人。也许有人会问,在王阳明的内心世界里,他所认为的圣贤到底有着怎样的面目呢?
《传习录》第一篇就是“新民”与“亲民”之争,或许可以为我们的认知打开一个缺口。
王阳明与朱熹在“新”与“亲”上各执一词并非文人之间的炫技,是两人在政治价值取向、为政理念上存在着差异。王阳明作为后辈,并没有冒犯朱熹的意思。心学不是凭空而来的,更不是王阳明独自开创的,在一定程度上,心学只是对儒学道统的一种继承和开创。
作为王阳明的首席弟子,徐爱心有疑惑,他问王阳明:“《大学》一书,明明德确实很重要,可是为什么又要强调‘亲民’呢?”
王阳明的回答是:“在儒学中,修己和治人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比如说像我父亲这样一个人,如果有一天从风光无限的京官生活一下子跌落尘埃,生活的困顿且不去说它,最难忍受的还是世人的白眼,尤其是来自那些不明底细的故交旧友的非议。到了那时,生有异才有什么用?笔绽莲花又有什么用?也只能以文章为游戏,自轻自贱了吧。巨大的生存压力之下,如果再无一点儿精神的空间,那真要把人给生生闷死。修禅,遁迹山水,都是为了解脱。说是万念俱空,一丝不挂了才去潜心禅修,但实际上还是对现实俗物眼不见心不烦的逃避。‘明明德’是要倡立天地万物一体的本体,也就是关注我们的精神世界;亲民(关怀和爱护民众)是天地万物一体原则的自然运用,也就是在追求精神世界同时,更要实实在在地去接地气。”
他同时还说:“明明德必须要体现在‘亲民’二字上,只有亲民才能彰显出光明的德性(明明德)。比如我们爱自己的父亲,同时也要兼爱别人的父亲以及天下所有人的父亲。做到这一点后,我们心中的仁德才能真实地同自己的父亲、别人的父亲以及天下所有人的父亲成为一体。只有成为一体,孝敬父母的光明德性才能完全彰显。”
朱熹作为宋明理学的集大成者,他强调的是“存天理,灭人欲”,他的善政理想就是,君王个人或辅助君王的人都应该洗涤身心,成为有德之人。不仅如此,他们作为统治者,还要使被统治者也成为有德之人。
王阳明认为,人是万物之灵,同时又是天底下最高级的动物,因此要特别关注人自身的病痛苦难,要重视人的自由性和主体性,否则的话,为政者就没有是非之心。
王阳明确信,如果这个世界每一个个体都能推己及人,由远而近,将恻隐之心投注于每个人,那么这个世界就可以实现万物一体的理想。生命时时欲飞,然而在道德的重扼下,却总是飞不起来。有时看似轻盈地将要越过去,还是会被一根看不见的绳子拽着,想要飞却怎么也飞不起来。
人来到这个世界究竟应该怎样活?走什么样的路?立什么样的志,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王阳明一生都将在这几个问题上打转转,而他来到这个世界的意义,用黄宗羲的话说:“以心学教天下,示人作圣之路,改变了理学将心物分为二的错误路线,让人步趋唯诺,无非大和真觉。”
在《传习录》中有一篇关于立志的篇章,王阳明的弟子唐诩问:“立志就是要时常心存善念,就是要为善去恶吗?”
王阳明认为,人心存有善念之时,才是最能体现生命本质特征之时,所以善念对于人心而言本该是人心的常态,所以没有必要“刻意”去存善念,所谓的“立志”并不是要人心去开疆拓土,去创建善念,而是持守此天理不失的“守成”之道。孔子的“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只是立志到熟处而已。精神、道德、言行举动,大多以收敛为主,发散是不得已。天地间的人和万物都是这样的。
生命不管处于何种阴暗崎岖的境地,都能感受到云遮雾掩背后那一丝“良善之光”在向你招手,而人的主观克制之力可以在瞬间引导良知重现,而不是让你在阴霾之中越陷越深。生命的本性是阳性的,是积极向上的,所以存此良善之心是阳明心学的核心命题。而在修持此心时,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收敛”二字,也就是谦虚、谨慎、不抛弃不放弃、不好高骛远。而与之相反的状态是发散,发散就是指一个人始终处于激进的、亢奋的状态,结果导致用力过猛,步子迈得过大。
祖父王天叙曾经对他说过一段魏晋文人的故事,嵇康有一次问孙登,人这一生应该有什么大追求才算圆满。孙登没有正面回答,而是反问道:“你懂得火吗?火烧起来会产生光,但是火的燃烧却不需要用光,在这个因果关系里,用光是果。同样的道理,人活着并拥有才华,但才华也不是人活着的前提条件,在这个因果关系里,用才是果;用光看,首先要有木材来生火,用才呢?那得要洞明事理,要懂得自保之道,如果人都死了,才高八斗又有什么用呢?”
孙登实际上是借用这则火的寓言,交给朋友一个人生的妙方,火、光、薪三位一体,火为主体,光为附属,薪为根本,火得薪而燃,光得火而亮,无薪便没有一切,或者才是王道。
而他的朋友嵇康却对此不以为然,用一句“才多识寡”便堵住了朋友之口。等到被拖到洛阳东市砍头时才真正明白,但一切都晚了。他所能做的也只是向行刑者提出最后一个要求,取过心爱的古琴,对着日光下自己的影子在高台上再弹一曲《广陵散》。
其实对于一个年轻人,实现自我价值的路径有各种可能性。这时候,摆在王阳明面前有两条路可供选择:一是一心扑在科举这件事上,像父亲王华那样当一个状元;二是加入当时社会的主流文化圈,潜心修习辞章之道,成为像李梦阳,何景明那样文名遍天下的大家。
而这两条路,都算是人生的正道。所谓正道,不过是全力求取现实世界的荣华。不过王阳明对于现实的荣华看得并不是那么重,功名对他的吸引力是什么?无非是可以借助这个平台实现治国平天下的理想。
当精神世界遇到堵塞的时候,王阳明想到了现实世界,而现实世界的圆满并不比精神的圆满来得更加容易。人生在世,本就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每天被俗物裹挟前行,像一粒尘埃飘来荡去,没完没了地寻找着来处与归途。辗转不得,强求不得,唯有将此心专注一处方可得。有时候,做一个知行合一的人,总是会比一个寡淡漠然的人来得疲惫。而人最大的敌人不是别人,而是自己;自己最大的敌人不是这副招摇过市的臭皮囊,而是皮囊之下那颗不让自己平静安分的心。
……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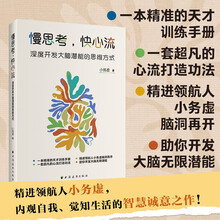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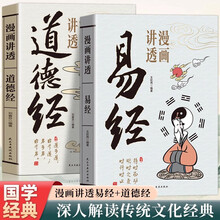







——余世存
我们这个时代缺乏王阳明的“痴”,这个时代的聪明人真应该看一看这本书。
——岳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