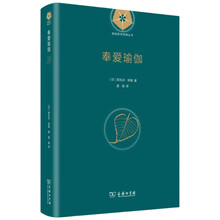呼唤文心的复苏
——文言文的辉煌与衰落
王文元
作者引言
最近,已经沉寂一百多年的国宝——文言文露出一丝复苏的迹象:2015年年初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了由陈永正、徐晋如主编的精装巨制《百年文言》,精选了从1911年至2011年百年间将近四百篇优秀的文言文作品。2015年下半年,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了王文元的文言文学术新作《儒道釋疏观》。此外,民间也暗流涌动,屡有才华横溢的文言爱好者初露锋芒。尽管如此,保护国粹的形势仍很严峻。不妨与邻国日本做一下比较:日本的文言文是从中国舶来的,但在整体水平上,我们与日本在掌握文言文的写作技巧方面仍存在巨大差距,日本人至今仍然普遍用文言文书写新年贺卡与往来书信。日本民间的吟道同好会(吟唱汉诗的文化团体)会员竟然超过五百万。文言文究竟有什么魅力,让日本人念念不释?国人究竟因为什么弃国宝如弃敝屣?在现代化的当今社会文言文究竟还有什么用处?文言文与历史文化传统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系?“文言文现象”的本质是什么?这种现象只发生在东方吗?文言文在本土能够复兴吗?……本文试图廓清以上种种疑惑,揭示出文言文的本来面目。
华夏的文化有心,心就寓于文言文;华夏民族有心,心就寓于礼乐文教。文心与人心结合孕育出中华五千年辉煌灿烂的历史。诸子之一的扬雄将中国的文字比喻为“心画”甚为贴切,中国的经典都是用心绘制出来的,都是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灵物,本来此物只应天上有,上苍却赠给了我们的先人。我们的先人也没有辜负上苍的眷顾,将一个个字符小心翼翼地放到文言文中,奇迹出现了:字符活了,而且充满了敬天爱民、悲天悯人的情怀。这种情怀出于对上天好生之德的回报。中国人认为人类历史是“天生神物圣人则之”的历史,是“天地变化圣人效之”的历史,是“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的历史,是“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的历史。总之,中国人紧跟着天,寸步不离。他们总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怀着“其亡,其亡,系于桑苞”的忧患意识,维护天的权威,祈求天保乂华夏民族。
每一个民族或国家都有自己的历史,但拥有用同一种文字记录、而且数千年不间断历史的只有中国。这是因为中国古人的信仰、价值观以及所使用的文字都是与众不同的,西方的文明出自于脑(通常称其为“理性”),是造作的产物;中国人的文化出于对自然的描摹与效法(通常称其为直觉或具象),包括汉字与文言文都是道法自然的产物。天不变道亦不变,以天为摹本的汉字与文言文因此而获得稳定性。稳定意味着保留记忆,而记忆则是生命最本质的特征。阿尔茨海默病的患者生不如死,就是因为他们失去了生命的本质——记忆,失去了体验生命流程的能力而变为行尸走肉。人怕患失忆症,民族何尝不尔?人生叹短,圣人亦然。老子将人生喻为刍狗,刍狗是用青草扎成的狗,用来祭祀,祭祀过后即丢弃。生命如同刍狗,老子的话是对吝啬的造物主的最严厉的抗议。孔子的抗议温和得多,他走到河边对弟子说:“逝者如斯夫。”虽然孔子温和,其城府却深不可测,他在感慨人生短促的同时构思出一种对抗死亡的策略,那就是通过民族与家族延续个体生命,通过名检让生命改变一种方式继续留存。人不能长久于世,但民族能,家族能,名检能。孔子完成了中国的第一部历史——《春秋》(那之前的历史典籍如《尚书》等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只是一种未经加工的历史资料,相当于今天的档案),开启了中国人书写历史、延续生命的历程。司马迁继承了孔子的遗志,补写了他之前2800年的历史。直到清朝,中国记史的传统未曾中断过。中国因此而成为世界上唯一保存5000年完整记忆的民族,创造了永远不可能被打破的记录。这一切功在孔子,功在司马迁,功在汉字,功在文言文!
崇尚理性的民族或国家很难产生连续的历史,因为理性的发展规律是由低级至高级,永远在发展,一刻也不停歇,语言文字也随之不断变化,前人的文字很容易成为死文字。莎士比亚生活的时代距今不过四五百年,但今人已经读不懂其原著,因为莎士比亚用过的词汇中,有两千多个今天已经废弃不用。至于埃及的圣书文字早在两千年前就已经沦为废字,现在世界上没有一人能读懂。我见过更加耸人听闻的报道:当下,有将近三分之一的美国大学生读不懂《华尔街日报》,因为新的单词与短语如雨后春笋,让读者难以招架。现在的牛顿大辞典收录的英文单词早已破百万大关。而常用汉字(中文的汉字与西文的单词都是基本表意单位)数量,汉朝是9300多字,今天也就一万多字(《康熙字典》中的许多字都是专用字,一般场合不用)。中文表达新思想、新事物一般不采用造新字的办法,而是采用合成新词、新短语的办法,而新词、新短语使用的仍旧是那些已有的字。这种现象在文言文体中尤为典型。使用文言文体的场合,造词受规则的制约,因此一般不会出现随意改变汉字原意的情况。“文饰”的修辞方式又将表达限定在“礼”的范围之内,所以有文言文体在,古典历史文献就永远可读,历史就永远可读,今人与古人就能够心心相印。
西方的语言文字都是不断变化的,以二三百年为一个周期,经过两个周期,后人就难以识别前人的文字。用这样的文字书写历史,当然不能传之久远。世界上有不少国家或民族很早以前就开始记录历史,但只有中国获得成功,其余都因文字不能为后人识别而宣告失败。中国成功的首要原因就是汉字是能够以不变应万变,为古人与今人所共用,实现古今“书同文”。显然,靠“考古”是制造不出历史的,口口相传也难以将历史完整地传至后世,非得有一种相对稳定的文字不可。
我们应该为我们的悠久历史而感到幸运,我们的先人以其超乎寻常的智慧创造出了能够书写历史的文字。这种文字有过很多名字,比如鸟迹文、甲骨文、钟鼎文、古文、籀文、石鼓文、小篆等,直到发生隶变,才形成被现代人称为汉字的文字(古人未使用过“汉字”一词,“汉字”是从日文引进的)。汉字是祖先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财富。这里有一个认识上的误区需要纠正。有人认为甲骨文是汉字之源,因此汉字训诂要以甲骨文为准。这种说法不准确,也不全面。汉字的词源学的本义可能来自于甲骨文,也可能来自金文、古文,但更多的场合来自小篆与隶书。中国最早的文言文所用汉字,所表达的意思绝大多数与隶书相吻合。甲骨文只出现于殷商,而殷商的政治中心并不是中华文化的发祥地。
如果以隶书为主要依据(而非以甲骨文为主要依据),那么可以说文言文体始终担当着维护汉字“字出同源”原则的卫道士角色。1899年甲骨文的出土对这个原则形成一定的冲击。在1899年之前,中国的任何典籍都未曾出现甲骨文的概念,也未提及过甲骨文这种文字形态,截至1899年,甲骨文对中国历史的影响几乎为零。1899年之后,受西方理性主义思潮影响较深的一些文人,如康有为、梁启超、胡适、丁文江、傅斯年等人掀起一场建立新史学的运动。当时,他们怀疑五经、怀疑夏朝的存在、怀疑司马迁对三代的描述。自从甲骨文被挖掘出来,关于商朝的历史就不再以《史记》为准,而是以出土的甲骨文与钟鼎等器物上的铭文为准。然而老天并没有给这些无聊文人的面子,当时的考古学对商王的排序与司马迁对殷商王的定名与排序如出一辙!所谓考古学家并没有意外发现,没有得到否定司马迁的有力口实。尽管事实证明了司马迁的正确与伟大,一心想否定中国悠久历史的帮闲文人们仍旧不死心,一百年来他们一直没有放弃对孔子与司马迁的怀疑与批判。康有为率先发难,矛头直指司马迁,提出臭名昭著的孔子托古改制说,将孔子由圣人降格为改革家。康有为在酝酿戊戌变法时喊出“抑古扬今”“废除科举”“全盘西化”等自戕口号,企图将中国用文言文记录的历史推翻,用考古的办法再造中国历史,以赢得殖民主义者的欢心。这股反动思潮至今未泯。后来梁启超与康有为分道扬镳,梁启超回归认同孔子与司马迁的正确道路。
二十世纪初叶形成的考古热持续了数十年,这股逆流的目的是让科学融入史学,引领史学,让史学成为科学的一个分支。用丁文江的话来说就是,史学就如同地质学,性质上没有什么区别。个别所谓考古学家窝藏的祸心,就是推翻华夏历史,证明华夏五千年历史是一种自恋的妄说,以迎合殖民主义者的需要。考古学家手握一个个“证据”,很有蛊惑性,善良的人难免上当受骗。除了证据,个别考古者手中的另一个杀手锏更厉害,那就是以司马迁的某某说得不到出土文物的验证为由否定司马迁。头脑简单的人被带进迷惑阵,以为一个民族的历史,用手写出的不算数,需要实物证据。也不能说这种说法完全没有道理,在西方国家,历史往往要由出土文物为依据,那是因为他们缺乏文字记载。中国有确凿的文字记载,还这样做就不仅是东施效颦,应该换个说法,称其“崇洋媚外、巴结主子”并无不可。
司马迁《史记》的可靠性源于汉字的可靠性,文言文体的可靠性,书写历史的人可靠。司马迁其人毋庸赘言,这里只想说一说文言文体可靠的问题。孔子对诗的论述也适用于文言文,因为中国古代诗文是同体的。孔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记史与写诗一样是不允许有邪念的。中国古代有三种职业是世袭的,第一种是医生,第二种是天文官,第三种是史官。史官自小就从父母那里接受关于历史使命感的教育。没有人否定司马迁的文字造诣,那种功底是伴随道德教育一点点积累起来的。既然当史官就随时准备死职,因屈从于权贵而歪曲历史,良心是得不到宽恕的,不会有史官这样做。还有一个关键因素,司马迁所使用的小篆与隶书与之前的其他文字是相通的,司马迁在追述三代或其前历史时可以参阅各种不同的文字,在文字上基本没有障碍。唯一的障碍是《尚书》中使用语体的那部分文字,不过由于司马迁博学多闻,加之他生活的时代口口相传的传统还没有完全中断,还保持着一些历史记忆。更重要的是,司马迁时代还有极个别读得懂《尚书》的人。《尚书》之外的其他典籍基本都是文言文体的,不怕时间阻隔。这一切合在一起,将《史记》可信度最大化。时至今日,我们未发现司马迁在记述重大人物或事件时失实。
中国的正史用文言文体写成,那些史籍上的文字就是证据,一般不需之外的证据。实物旁证属于锦上添花,有之更好,无亦无妨。有些人怀疑正史,完全是因为他们不懂历史,不懂文言文,不知道文化传统的形成机制不允许治史者弄虚作假,更不知道中国人对名检是持极其认真态度的,就是写当朝史(从隋朝开始,中国人确立了当朝只写实录、后一个朝代写前代正史的规则,但之前司马迁的《史记》并非如此,《史记》涉及到当朝)也绝不为皇帝权贵讳。《佞幸列传》牵扯到的皇帝有汉高祖、汉惠帝、汉文帝、汉武帝四位。其中司马迁对汉武帝的批评与挖苦最甚。“佞幸”的意思乃是以巧言谄媚而得到宠幸。设立《佞幸列传》本身已经含有批评皇帝用人失当的意思,充分说明《史记》是公正客观的,没有避讳权贵。司马迁高度评价孔子,将孔子置于世家,而且篇幅很大。然而文中也不乏批评孔子的文字,有时还揭孔子的伤疤。须知,西汉是崇尚黄老的,司马迁将老子置于列传,且由老子与韩非共分本就不多的篇幅。仅此一端就不知要得罪多少人。事实证明:司马迁对老子与孔子评价虽然有违于时风,却经得起历史考验,历史证明司马迁的评价恰如其分,没有任何不当。人们容易忽视的是,司马迁是一位文言文写作的大高手,中国历史上能与他相提并论的写家不会超过十人。从他的写作态度与写作特点上就能断定他是一个真实的人,一个嫉恶如仇的人,一个十分看重名检的人,一个把一切奉献给自己民族的人。中国有伏羲、仓颉、周公、孔子等先圣,有司马迁这样的伟人,又有文言文这个尤物,实在是太幸运了。
其他国家与民族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人类社会早期产生的文字,包括埃及的圣书文字、苏美尔的楔形文字、墨西哥的图画文字等早就淹没在历史之中不见了踪迹,即使偶尔挖掘出一些残破的庸器,也没有人认得。难怪语言学家们总是将语言文字比喻为一条河,赫拉克利特说一个人不能两次过同一条河。除去汉字,世界上也没有一种文字能够记录相隔千年的两个不同时代的历史。这些国家没有用固定文字记录的历史,只得权将流传下来的神话故事充作历史。有的国家还将《圣经》当做历史启蒙教材,让耶稣充当历史人物,对蒙童说我们民族的文明史始于耶稣。他们煽动中国人重新定义历史,以出土文物为历史的证据,他们自己却从来不去搜寻耶稣的遗物。
综上所述,世界上只有一种文字具有共时性,就是汉字;只有一种文体能够做到古今书同文,那就是文言文。文言文具有共时性,这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人类认识世界无非两个途径,一个是理性的,另一个是实践的。所谓实践就是自己不去建立什么原则,一切跟着自然走,自然怎样人类就怎样,这种认知靠的是持之以恒的观察,支持观察的则是坚定的道德信仰。所以,归根结底文言文的共时性来自于天道的永恒。解释文言文的共时性,必须从永恒的天道着手。
中国古人对道的理解正确吗?不仅外国人打问号,国人的底气亦不足。直至现代物理学逐渐揭示了物质世界的本质,人们才相信:中国古人对道的理解完全正确,中国古人的理解与现代物理学所揭示的完全一致:
物质在未被人为改变的情况下,总是能够保持其稳定与永恒的形态。这个规律被称作穆菲定律。量子物理学的建立并未解除关于物质稳定性来自何方的困惑,反而加深了困惑。自从1927年海德堡提出测不准定理,疑惑更是让人们挥之不去了:世界明明是物质的,而组成物质的基本单位——粒子却不具有物质性,非但不具有物质性,而且人根本捕捉不到其踪影。正如《奥义书》所说:(基本粒子)什么都是,同时什么都不是,因为它飘忽不定,人难以捕捉到它。直到二十一世纪,英国物理学家希格斯发现一种新粒子,神秘面纱才被揭开:当其他粒子进入希格斯粒子的场,两种粒子结合在一起,新的东西才诞生,新的东西的名字叫“物质”。物质具有质量,具有窒碍性与稳定性。穆菲定律描述的是:在物质性未被破坏的场合,物质的形态是稳定的,经过人为破坏,重新归于不稳定(比如埋在地下的铁矿石是稳定的,将它开采出来炼成铁,它就失去稳定性,很快会腐蚀掉)。基本粒子的古怪秉性令爱因斯坦心情不快。他曾经认为等到实验设备更加完备时,也许会证明“粒子不具有物质性”的结论是错误的。但是晚年的爱因斯坦妥协了,他不仅承认了粒子的非物质属性,而且对宏观世界的物质性也产生了怀疑。他曾经说:世界不是物质的,我们称其为物质是一种误会。所谓物质不过是较强的场而已。可惜他未能再往前迈一步。希格斯揭开了让爱因斯坦魂牵梦绕的物质之谜。希格斯因此被授予诺贝尔物理学奖,但他拒绝以他的名字命名新发现的粒子,只是当他知道物理学界准备用“上帝粒子”命名时,才迫不得已接受了用自己名字命名新粒子的建议,因为比起讨厌自我张扬,希格斯先生更讨厌上帝。
我施如此多笔墨叙述希格斯,主要想以此为铺垫,以突显另一位人类伟大贤者的睿智与先见之明。他就是老子。西方近百年的两个重大发现,老子都讲到了。关于世界的非物质性问题老子说“有生于无”;关于世界产生物质性的问题,老子说:“万物负阴抱阳,冲气以为和。”意思是万物无非由阴与阳两个元素构成,两个元素结合在一起万物就具有了稳定性,这才有了大千世界。原来,老子早希格斯两千多年就已经揭示了关于世界本质的惊天秘密。老子所说的“和”指的就是物质的稳定形态,负阴抱阳是关键,是说两个性质相反因素的结合构成了世界秩序。也就是说,世界的一切秩序是阴阳和合所赋予的,就像每一个人都是父母“和合”的产物。至此,一个旷日持久的官司有了结局——中国古代的合二而一“胜诉”,西方的一分为二“败诉”。事实正如此,合二而一的世界是稳定与持恒的,一分为二的世界则是动荡与断裂的。
文言文就是因合二而一获得稳定性的,具体说,文言文是人与自然两个因素合成的。这一点与单方面出于头脑的西方表音文字立异。西方人由人脑进行分析推理,进而揭示自然规律,用罗素的话说就是,不断地分析,直至不能再分的原子。后人称这样的分析方法为逻辑实证主义。这种方法叫做一分为二。
晚年的爱因斯坦与希格斯之所以取得巨大学术成就,与他们回归中国先哲的合二而一思维方式有很大关系。用最简洁的词汇表示希格斯粒子就是“合二而一”。
文言文的规律竟然与物理学规律不谋而合!这实在不可思议。其实并不奇怪,中国的儒家与道家在天人合一这个方针上基本是一致的。这个方针渗透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语言文字当然也不例外。我们可以将每一个汉字视为一个基本粒子,将共时性视为物质的稳定性,将文言文的形式与建立在形式基础之上的规则视为场(相当于希格斯粒子),那么这样一个场景便出现了:汉字进入文言文的场从而获得稳定性,如同基本粒子进入希格斯粒子的场获得物质性。文言文一旦获得稳定性就会一直保持下去,直到人为改变它(如同穆菲定律所描述的那样)。文言文中的自然基因在维持着它的形态,抵御着口语的不断侵蚀。——这就是文言文稳定的奥妙之所在。使用语体的场合,汉字也能够自如地表达事物,表达思想,但表达的文字不具有稳定性,难以传世。这就是为什么古籍中偶尔出现的俚语词汇一直不为后人理解的原因之所在。《晋书》记载过这样一件事情:
王戎问阮瞻孔孟与老庄有没有区别,阮瞻回答说:“将无同”。后人不解其意。原来“将无同”是当时的口语,经过时代变迁,惹来无数误解,以至原意已经不为后人所知,所以译法五花八门,有“差不多相同”、“完全不同”等十数种。台湾作家柏杨将其译为“似相同”,内地语文工作者吕叔湘将其译成“恐怕不同吧”……皆不符合原意。“将无”的原意为“那就……吧”,“将无同”的真正意思为“既然你说相同,那就相同吧”。正话反说,表现出阮瞻对王戎提出小儿科问题的蔑视与嘲笑。为什么普通的一句话导致如此大的误解,以至于连现代“语言学家”都不解其真意呢?因为“将无同”是口语,只有当时当地的人了解。恐怕阮瞻没有想到,他的一个小小的噱头竟然给后人带来如此大的麻烦!可见,规范统一的书面语对于“传世”具有多么大的意义。中国早期的历史文献《尚书》中含有大量记言的文字,时过境迁后人读不懂,只能借助于训诂书《尔雅》了解其仿佛,完全读懂是不可能的。学界曾经为《尚书》中出现的“维维”一词大惑不解,汉字词汇中从未出现过“维”连用的情形。最终有人发现,是因为讲述者口吃,说了两个“维”,史官为了忠实于讲述者原意将两个“维”都记录了下来。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