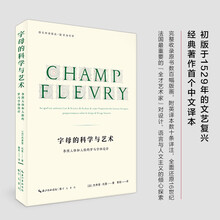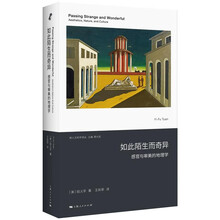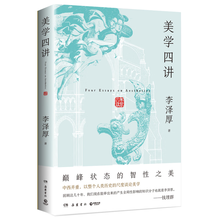《中国古代美学史论》:
三、唐代以来对意象内涵的扩延
在刘勰的“窥意象而运斤”的理论层次里,“意象”尚属于作家艺术家在思维中化实象为意象的想象性的形象存在,是有待“独照之匠”去“运斤”创造的对象。这说明此“意象”还不是已经外化了的艺术对象体。但中国的审美艺术创造的历史和艺术美学理论的历史却又证明,审美意象既是理论范畴,又是实践范畴。它并不仅仅存在于艺术创作主体的审美思维过程之中,在想象阶段实现为“运斤”创造的对象之后,一当被赋予形式载体,它还可以变成外化的直感艺术形象。叶燮所论杜甫之诗,诸如“碧瓦初寒外”、“月傍九霄多”、“晨钟云外湿”、“高城秋自落”等等,皆为意象性的诗句。而以同理视之,中国的诗人中,李白、李贺、李商隐等人,也都有不少特征突出的意象诗。
正是由于创作领域的实践进展,在意象形象创造方面取得了多方面的经验。,在唐代以来的古代美学理论中,则多有对于意象范畴的论析,论列的范围不仅在主体心理想象层面,也扩展到主体实际创造方面,尤其是诗画赏评领域,特别标示意象范畴,几乎成了作品达到至美的一个突出标志。其理论要点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艺术意象创造是艺术超越生活事物的一个标志。唐人司空图的《廿四诗品·缜密》中说:“是有真迹,如不可知;意象欲出,造化亦奇。”这是说,隐迹于形表之内的本真,有迹又似无迹,人们对它不能直观把握,它只有在人的思维中化为审美意象始能悟得,即使此刻之作者“言语道断,思维路绝,然其中之理,至虚而实,至渺而近,灼然心目之间,殆如鸢飞鱼跃之昭著也。”(叶燮《原诗,内篇下》)作者创造出的意象足可以移夺造化,如李贺诗对韩愈诗的赞扬为:“笔补造化天无功”(《高轩过》),这必然使造化也惊奇人的神思意象之妙,自叹实际造物的局限。艺术超越普通的实际存在,使之比自然形态的存在更理想更典型,使艺术更具艺术性,使艺术表现更具合情合理的必然性,而艺术意象的创造是达到这些目的的一个重要条件。
二是艺术意象创造是艺术创作主体化无生为有生,达到艺术想象完美的一个标志。唐代诗人王昌龄在《诗格》中对于诗的品位分为三格:“诗有三格:一日生思,二日感思,三日取思。”生思的关键在于“心偶照境,率然而生。”“感恩”在于“寻味前言,吟讽古制,感而生思”。“取思”在于“搜求于象,心入于境,神会于物,因心而得”。这是要在诗的构思过程中,主体的思维要融物于心,应会感神,通灵化物,造成意境,达到这一境地的主体心理状态必是神思妙运,气倍辞前,想象力充沛丰富;而如果是“久用精思,未契意象,力疲智竭,放安神思”,也就是殚精竭虑,灵感枯萎,不能以艺术想象力使对象转化为意象形象,就不会写出真正“视境于心,莹然掌中”的好诗。对于凭藉审美意象使无灵性的存在变成有形色生命的话体存在,倒是唐代书法理论家张怀瓘讲得十分生动透彻。他认为,书法创作所创制之文字要灵动飞扬,“以筋骨立形,以神情润色。虽迹在尘壤,而志出云霄。灵变无常,务于飞动。或若擒虎豹,有强梁拿榷之形,执蛟螭,见蚴缪盘旋之势。探彼意象,如此规模(《书法要录》卷四《张怀瓘文字论》)。”书法家使自己写的汉字有如此的气势精神,全是作者的意象生成,他使笔下形迹作擒虎执蛟的意象表现,实是“探文墨之妙有,索万物之元精”,达到了艺术创造的极致。
三是艺术意象创造是实现艺术独创的一个重要标志。就艺术表现的对象来说,因为它们的存在对谁都是共相的存在,只是在由人进行表现时,才由构象者之不同而呈现为不同的形象存在。这种构象特殊,主要原因在于人在构象过程中所附着的心理情思的特殊性,这就是刘勰所说的“独照”;独出这种综合的“神用象通”之意象,作为供人观照的艺术形象,也就不能不具有独创的特殊性了。宋代画论家郭若虚的《图画见闻志))评张璪的绘画:“尤于画松,特出意象。”明代李东阳《麓堂诗话》评温庭筠《商山早行》诗“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能道羁愁野况于言意之表”,为“意象具足,始为难得。”明代陆时雍《诗镜总论》评乐府诗《东飞伯劳西飞燕》等诗为“风格浑成,意象独出。”清代刘熙载《艺概·书概》中说:“书与画异形而同品。画之意象变化,不可胜穷,约之,不出神、能、逸、妙四品而已。”这些都是从意象特殊意义上评论作品的,而特殊的原因全在于构象感受上的特殊所致。如张璪画松,是“师造化”而“得心源”,所以他画松之荣枯之枝,才“润含春泽,惨同秋色”。《商山早行》用两句的六个名词,虽是冬晨广具之象,但是非直接以身心体验并又能化为审美意象者,却又不能道出。所以,这画与诗的特殊表现,既是神思化物的特殊,也是艺术表现的特殊。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