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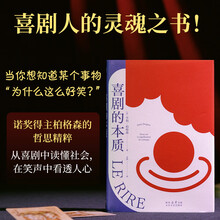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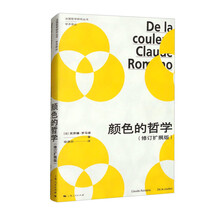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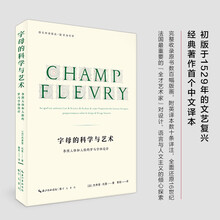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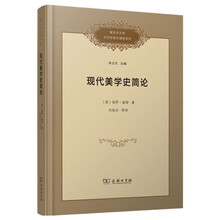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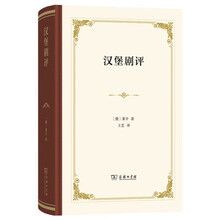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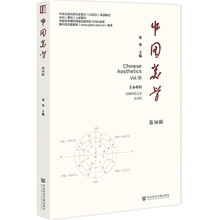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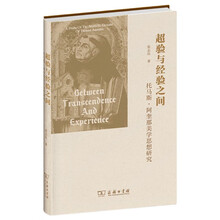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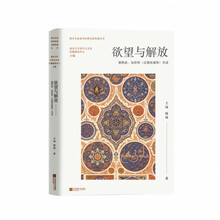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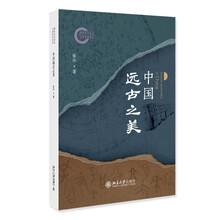

为什么《人间词话》久经不衰?它的现代性奥秘又在哪里?本书中,作者陈建华教授使用实证与历史脉络化方法,在王国维与康德哲学的整体构架中解读《人间词话》,指出它由于西方哲学与本土诗学的融合、碰撞而趣味横生,歧义纷纭,其中的“境界”说核心则是一种新的科学世界观,含有欧洲启蒙思想的个人主义与理性精神。
本书由三篇文章组成,读者可循序渐进体味王国维由叔本华转向康德的经历,进一步了解王国维与康德哲学、时代及清末文论的生产场域的关系,从整体上来观照,深入到尘封的历史断面而发现幽微之处。
“一千个人眼中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不管是谁说的,这句话很能传达当下互联网时代的阅读风尚。这对王国维也适用,至少对现代经典的《人间词话》而言,他的生命的悲剧性也不亚于那位丹麦王子。话虽这么说,阅读的自由有一定的限度,似乎谁也不会把哈姆雷特或是王国维读成喜剧,而且阅读中个人三观与时代风气、教育背景或朋友圈影响等因素息息相关。回想20世纪
80年代,跟现在大不一样,一本书动辄印数上万册,那种大众阅读的狂欢景象,形成某种公共记忆的东西,至今令人神往。在我们的阅读记忆中,印刻着李泽厚先生。他在《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中断言:“王国维在西方文化的熏陶下,浸染了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唯心主义。”或如陈元晖的《王国维与叔本华哲学》一书等,皆流行一时,长期以来几乎主导了《人间词话》的阅读史,王国维的悲剧生命与叔本华的悲观哲学被拧成一个死结,坚不可破。
2019年5月我在《书城》上发表了《〈人间词话〉的现代转向》一文,其实是宋词研究系列的一个迂回插曲。我想在中国韵文抒情传统中彰显宋词的某种纯艺术特点,而《人间词话》对姜夔的批评触及“形式”问题,觉得有必要讨论一下,结果却给自己留 下一个挥之不去的悬念。《人间词话》实在重要,其“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观形塑了我们对文学发展的看法,哲思隽言滋养了我们的审美趣味,其“经典化”过程也是批评史上的一个奇观。
文中说:“王国维在1904年发表《红楼梦评论》,深受叔本华悲剧观的影响。《人间词话》发表于1908年,其中的认识论则渊源于康德。”这表述看似波澜不惊,但标出前后年份蕴含着我的历史化研究取向,即认真看待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里对叔本华的缺乏“客观”的质疑并由此转向康德哲学,其中“认识论”扮演了主角,这对《人间词话》的研究是一个新的起点。以往学者大多阐述王国维“以我观物”“以物观物”及“隔”与“不隔”等美学创见,皆认为主要是受了叔本华的影响。我的文章则从“显象” —康德认识论的基点—出发,专注于“自然”的“写实”主张,并和“隔”与“不隔”以及对南宋词的排斥的观点联系起来,指出整体上这是个“世界观”问题,背后站着欧洲启蒙时代以来的科学实证主义,在反对形式主义与简约传统方面显示出某种“现代性”走向。
在这么思考时,我的记忆库存被激活,思想碎片从各个角落跑了出来,交互产生化学反应。我一向关注晚清文学与图像的“逼真”观念,这涉及文学上“写实主义”模式的近代系谱,《点石斋画报》是个显例。图像基本采用透视法,与照相、石印技术联袂而至,英人美查鼓吹“逼肖”表现外在世界的优越性,可说此是一次西方的科学与文化输入,却前所未有地展示了城市与人的种种奇观。康德的知识论中,经验世界在人心的“显象”是其哲学基点,根源于柏拉图的“摹仿”理论,这一点反而是叔本华强调了康德对西方哲学的贡献。王国维并未解释“再现”概念,而他要求“写实”与“自然”对应,并限于对“情”“景”的描绘,以及基于“隔”与“不隔”的批评对南宋词的排斥,这几点构成他的“境界”说的基本框架,且强调“真”“伪”价值的二元判断。因此我认为这属于一种较为有限的“再现”理论,意识形态上与晚清的“照相写实主义”是殊途同归的。
自序
王国维《人间词话》与康德哲学
一 前言:迟到的康德
二 确立“自然”与科学世界观
三 “境界”的“再现”原则
四 完善人格的主体构建
五 结语
“境界”与“再现”的现代发现—以王国维与梁启超的比较为中心
一 前言
二 “哲学”是另一战场
三 “自然”“显象”与康德哲学
四 梁启超的“境界”与《华严经》
五 王国维的“境界说”与科学性
六 余论:超越生命之光
王国维与视觉中心主义——兼论《人间词话》与《人间词》的理念与创作实践
一 前言
二 “视觉中心”的当代性
三 对“西方视觉中心”的反思之反思
四 王国维之“观”的中西思想渊源
五 康德哲学与文学客观性
六 《人间词》:“天眼”观照下的时空境界
七 余论:背对进步的风暴
征引书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