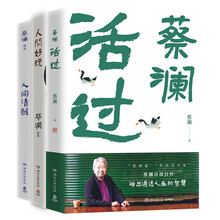热尼娅·柳维尔斯在彼尔姆市出生、长大。后来她对往事的回忆,如 同她当年的玩具船和洋娃娃一样,都沉没在家里到处都是的毛茸茸的熊皮 里。他的父亲是隆耶夫斯基矿山的业务主管,在丘索瓦亚的厂主中间有一 大批客户。别人赠送的毛皮都是深棕色的,软软的。她儿童室里的那张白色母熊 毛皮好像一朵散落的大菊花。它是专门为“小热尼娅的房间”添置的—— 在商店里选中、谈好价钱后买下来,并找人寄回来的。每年夏天,他们都住在卡玛河对岸的别墅里。那时候,热尼娅都是早 早就被大人哄上床睡觉的,她看不见莫达维利哈区的灯火。但是有一次,那只安卡拉猫不知道被什么东西惊吓到了,在睡梦中猛地颤动了一下,把 热尼娅惊醒了。于是她看到大人们都在阳台上。垂在横梁上方的赤杨树枝 叶繁茂,像墨汁一样变幻着颜色。杯子里的茶水是红色的,袖口和纸牌是 黄色的,呢绒桌布是绿色的,这些就像是梦魇,但这梦魇有着热尼娅很熟 悉的名称:他们在打牌。然而很难断定在河对岸发生了什么,它很遥远、很遥远。没有名称,没有清晰的色彩,没有明确的轮廓,它是激动不安、可爱而又亲切的,它 不是梦幻,不是那种在香烟的烟雾里辗转反侧、喃喃低语,把鲜明飘忽的 影子投射在走廊棕红色的木柱上的东西。热妮娅哭了起来。父亲走了进来,向她解释。英国女教师把身子转过去对着墙。父亲的解释非常简短:“那是莫达维利哈,没羞,这么大的姑娘了。睡觉吧!,,小女孩什么都没弄懂,只是满意地把流下来的眼泪咽进嘴里,她本来 就只有这点要求:知道那个未知的东西叫什么——莫达维利哈——邪天夜 里,这个解释就说明了一切,因为在这个夜晚,这个名称对孩子来说还具 有完整的令人安心的意义。但是,第二天早上,她开始提与此相关的问题了:莫达维利哈是什么 地方,那里的人们夜晚都在做什么。她知道了莫达维利哈是家工厂,国营 工厂,那里生产生铁,用生铁又生产……但她已对这些不感兴趣了,她感 兴趣的问题是,那些被称作“工厂”的地方是不是一些特别的地方,谁住 在那里;不过她并没有提出这个问题,不知道为什么,她把这些问题故意 隐藏起来了。这个早晨她就走出了自己的幼年,那个昨天夜里她还生活在其中的幼 年。她平生第一次对某种事物加以怀疑,这种事物或者留给自己,或者,只对下面这种人敞开,他们会大喊大叫和惩罚别人,会抽烟,用门闩把门 插死。就像这个新知道的莫达维利哈一样,她平生第一次没把心里想的事 情都说出来。而最重要的,最需要的,最令人不安的事情都被她独自隐藏 在心里。转眼几年过去了。孩子们自打出生起就习惯了父亲的经常外出,他们 把这种情况看成是父亲身份的特殊之处:很少与子女共用午餐,从来不在 家吃晚饭。他们越来越频繁地在空荡而庄严的房屋里玩耍,吵闹,喝水,吃饭。而英国女教师冷冰冰的说教代替不了母亲的存在,母亲的暴躁和顽 固像一种亲切的电流使家里充满一种沉重的气氛,但这沉重也是甜蜜的。北方的日色静静地透过窗帘涌进来。它没有微笑。橡木餐柜有些发白,银 制餐具笨重、艰难地堆放在里面。英国女教师用熏衣草液洗过的手在餐桌 布上方移来移去,她不会给任何人少分一份饭菜,她拥有取之不尽的耐心 ;她富有高度的正义感,她的房间和她的书籍永远是那样的安静整齐。女 佣端上饭菜后,会很长时间留在饭厅里,直到取下一道菜时才去厨房。一 切都愉快而舒适,但却悲哀得可怕。对于小女孩来说,这是充满疑虑和孤单的年纪,感到自己有罪以及因 无法用“基督教”表达明白,而希冀用法语的“基督主义”来表述某种东 西的时期。有时候她感到,由于她的败坏和顽固不化,一切不可能会好,也不应该好,这都是活该如此。然而,孩子们从来没有意识到这些,恰恰 相反,他们的全部身心都在战栗和徘徊,完全被父母在家时对待他们的态 度给弄糊涂了,那时,父母亲称不上是回家,只是回到这个房子。父亲 偶尔讲讲笑话,但总是不太成功,有时还很不恰当。他能感觉至6这一点,也感觉得到孩子们明白这一点。他的脸上总是浮现出窘迫不安的愁苦表情。但是当他生气的时候,当他失去自控力的那一时刻,完全会变成另外一 个人。一个对任何感情都没有反应的陌生人,孩子们也从来不敢和他顶嘴。但是从某一时刻开始,他对孩子房间里传出来的埋怨以及孩子们眼中 流露出来的批评已经麻木了。他感觉不到批评。这样一个不易被任何事刺 伤、变得让人认不出来的卑微的父亲,同那个发怒的父亲——那个陌生人 截然不同。他抚摸两个孩子,对女儿的爱抚较儿子多些。可母亲常使他们两个感到难为情。母亲尽情地给予他们爱抚,给他们 礼物,一连几个小时和他们共度时光,但偏偏此时的孩子们最不希望这样,此时的一切会使他们感到是在不劳而获,他们幼小的心灵因而受到压抑。母亲本能并且任性地给孩子们起亲昵的外号,在这些昵称中,他们甚至 认不出自己了。当他们心中出现少有的安宁、不觉得自己犯了什么错误时,当内心深 藏的秘密——那种好像出疹子之前的高烧一般遮掩着的东西不再使他们良 心不安,他们常常会感觉母亲是个冷漠的、回避他们并且无缘无故就发火 的人。邮差来了,信是寄给母亲的。她收了信,并没有道谢。“回自己屋 去!”然后砰的一声关上了门。他们沉默地耷拉着头,一种落寞感袭上心 头,长时间陷入沮丧和困惑不解之中。开始发生这种事的时候他们往往是哭一场,后来,在母亲一次猛烈的 发火之后,他们害怕了。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一切演变成深藏在他们心中 的对母亲越来越深的反感。P3-6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