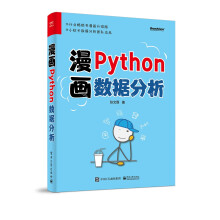对方一上午始终纠缠在大麦品质上,根本没有涉及价格、数量这些合同的具体问题,光是在吊我们的胃口。南澳洲方面本来的立场是,用一天或一天半时间进行谈判,介绍作物的品质,再报个价,只要能从西澳州独占的大麦市场中抢到一些份额,给治下的农民有个交代即可,原本也不指望一次谈判就能达成协议,把货全卖出去。谁也想不到,后来对方却给了我们一个意外惊喜。一顿午饭消解了双方的隔阂,在下午的谈判中,对方开始询问我们的报价和条件,南澳洲方面也松了一口气。M董事长先是问到岸价格(cF),接着又询问海运费和离岸价(FOB)的明细,之后就提出运费也高、离岸价也高,拼命压低价格。他似乎和西澳洲谷物局的O局长是老交情的样子,对价格把握得十分清楚。晚宴时终于迎来了高潮。M董事长说:“台湾今后将是一个越来越大,充满希望的市场我们之前和西澳洲谷物局打了多年交道,但双方之间也存在问题,看情况,把进口量全转到南澳洲也是可以的。这就需要你们拿出个特别的优惠价格来,要是FOB每吨36.5美元,我们就从你这儿买。”南澳洲政府的局长离席,好久之后才回到宴会上。当时可是没有手机,联系不便的时代啊。最后终于下决心,他拿出数字来了。“38美元怎么样?”“那可不行,就是36.5美元。”38美元已经是前所未有的史上最低价了,可即使这样,对方仍然说“不行”。“那就按您说的吧。不过条件是这个价格只给您的R公司。对外要作为绝对机密。对其他成员公司的价格只能是38.5美元。”就这样,该交易立即达成协议,而且还是6万吨数量的大交易。尽管是在宴席上,还是在简单的记录上签了名。这是为了预防第二天改口而引起麻烦。因为当时有过这样一个事件:三井台北支店机械课的一个长年客户违约,尽管在合同上盖着公司总经理的大印,但那位总经理却诡辩道,“盖我的印并不代表公司,只是代表我个人”,因此拒绝履约,最后还逃往海外,潜踪匿影。由于就合同达成一致意见,公司总部的大桥第二天就准备回国了。正当他刚到机场时,R实业把电话打到公司,说希望把三井一直合作的航运公司介绍给他们,把原来的离岸合同改为到岸合同,于是,紧急让大桥暂缓回国。对方可能是觉得,如果以离岸合同方式购货,就需考虑在澳大利亚当地的配货和雇佣装卸工的各种费用等琐事,这些麻烦事与其自己干还不如委托给三井,既安全又便宜,所以想干脆改成到岸合同。对三井来说,到岸方式虽然风险增加,但却能垄断当年台湾的大麦进口市场了。第二天,美国嘉吉(cagill)公司驻日本代表L先生就来到了我的办公室,激动得满脸通红,说道:“台湾市场以前一直做的都是西澳洲的大麦。由三井全部垄断太不像话了,你多少要分给我们嘉吉一点份额吧!”这位L先生是我在东京时的老朋友了,可是合约已经签订,只能拒绝他说:“抱歉,已经不能改约了。”之后由于大麦价格飙升,对契约条件的解释问题发生分歧,导致了与R公司关系的恶化,业务往来也停滞了很长时间。而我再次见到M董事长,已是大约20年后,在一次为调换三井台北分公司负责人举办的酒会上的事了。我拜托新上任的植松修三一定要特邀M董事长来参加,虽然我心中忐忑,但M董事长终于还是来了。尽管只是和他握个手,闲聊几句,对我来讲,也有一种“相逢一笑泯恩仇”的放松感。与R实业出现问题的经过是这样的:签约大概半年以后,台湾当局追加的进口许可权分到了台中的T实业手里。T实业的C先生一直对我们很照顾,这次T实业向我们表示南澳洲的大麦品质良好,希望无论如何也要帮他们购买。可南澳已无法供应足够数量了。谷物的国际交易中装船重量不好准确统计,因此国际惯例商定,在到岸合约条件下,允许所雇用的船只出现±5%以内的误差。也就是说,在到岸合约条件下,如果是1万吨出售合约,那么卖家以5%以内误差的条件雇佣船只,实际的装货量位于9500吨至10500吨之间即视为履行了一万吨的合同。三井与澳大利亚之间签订的是6万吨的离岸分批运输合约,分几次装船后,还有剩余的货物,就作为合同余额留下来了。三井就把这部分作为出售给T实业的部分货源了。而R实业向我们三井反复提出,他们有权要求给他们发货要达到6万吨的上限105%,即6。3万吨,并逼迫我们要放弃与T实业的合同。我们几次向R公司说明,到岸合同是基于国际惯例签订的,合同履行数量的解释应该是如何如何。签订租船合同的对方船运公司就想尽量多拉一点货物来多挣钱。这里,决定载货量的不是三井而是船运公司。事到如今,要让三井放弃与T实业的合同,是无论如何也做不到的。就在双方这样唇枪舌剑的过程中,一天,我们的支店长突然接到R公司的电话,M董事长在电话里威胁道:“三井把我们的大麦偷着卖给我们的竞争对手,你们要是想毁约就得赔偿我们。如果三井不尽早回应的话,那我们就在9月30日的《经济日报》上公开你们的丑闻。”支店长忙把我叫来问是怎么回事。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