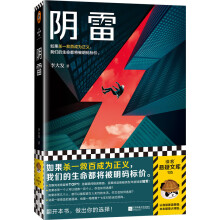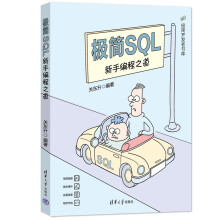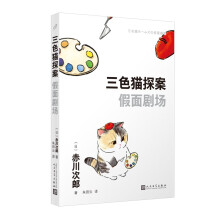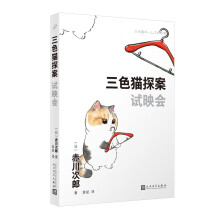在场首先是一种时空关系。就空间来说,在场最早以身势语的直观可视为界限,以眼神、表情、举手投足等这些可以直接为人感知的身体表征为边界。口头语出现后,在场则变为以可以实时互动的语音响应为边界,它克服了视觉的局限,使交流对话的范围得以扩大。文字出现之后,在场的空间限制弱化,时间性得以加强,在场转变为“正在阅读或体验中”这一形式。文本通过被阅读而向我敞开,与我结成了一种亲证关系。阅读不仅仅是一种认知,还是体验与亲历或情景重现,不仅仅是一种精神行为,还是一种身体行为,需要诸多感官的同时参与和配合。就时间而言,在场意味着共时,它是对时间流的一次拦截,即将时间空间化,历史传统的纵深感被压扁成一个共时的平面——“当下”或“此时此刻”。这时的当下不是一个空白的瞬间,而是一个充满价值内涵的“共时”空间,历史、传统、文本以及个人在这里相互作用,形成一个复调性或杂语性的界面。
在场的价值维系在“我”的身上,“我”的亲历亲在是在场的前提与保证。
我们前面说过,“我”是一个自指概念,尽管它不表示任何确定的所指,但它像一条虚线穿过这个世界,像中轴线一样把世界一分为二:即“我”面对的世界与“我”背对的世界,或“我—你”世界与“我—他”世界。“你”是我面对的另一个主体,是我“在场”的确证。作为一个近指概念,“你”是面向“我”且随时准备走向“我”,或吸引“我”走向“你”的“他人之我”,你能与我作情感与理智上的交流;“他”是我背对着的某一客体,构成我的不在场。作为一个远指概念,“他”只是一个背影,以冰冷的客体形象整个地一览无余地进入我的视野,“我”无法打碎“他”形象的坚硬外壳,进入“他”的内心并与之晤谈,我只能谈论“他”,远距离观照“他”,却不能让“他”背转身来,否则,他就不再是“他”而是“你”了。“对人作冷静的、不动声色的分析,是不可能掌握人的内心世界,不可能看清他,理解他的;通过与他融为一体、移情其身,也不可能把握他。这都不行。只有通过与他交际,采用对话方式,才能够接近他,揭示他,准确些说是迫使他自我揭示。”①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