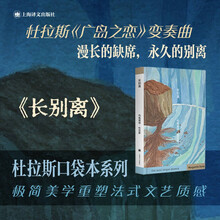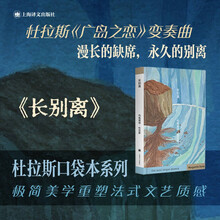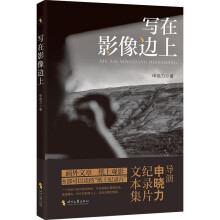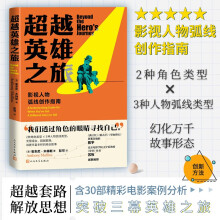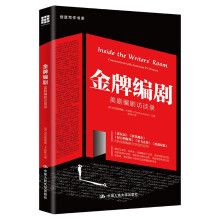首先,那些场面对男人而言无论如何都不会存在,因为它们要求房子中居住的人有一种最基本的沉默——这样称之吧:身体的沉默一一这种活动的延伸(例如她们点火时)与活动所在的时间的延伸相吻合。很难想象男人,两个男人像那些女人一样久久地待在那里,没有缘由,一言不发地在那里点火。
也无法想象男人会和那个推销员长时间待在一起。无论是谁,我敢肯定,面对推销员时都会不耐烦,最好的情况就是来人一进房门,男人没有即刻把他打发走。因为一个男人也许会去听推销员的演讲,但是男人的目光还没有女人目光中的这种功能:在某个他被排除在外、他保持沉默、他不复存在的地方听人演讲。
撕报纸、法国电力公司的信和学生成绩册的场面也不能为一个男人设计:男人会说话、为自己辩解而不会撕掉那些东西。或者,即使要采取行动,也要先把话说完。只有在发疯、发神经时,男人才会采取本能的行动。那些女人很自然就能做到的事情,男人只能在发神经时才能做到。
对观众而言,这种状况就可能超越所有其他可能的方面,而动作的完成必须有这些场面。我们会这样想那个做伊莎贝尔·格朗热才做的事情的男人:他有毛病,因为他撕自己的信件,这会变得比撕毁信件本身还重要。要是人们想——我认为人们会这样想——伊莎贝尔·格朗热的身上有某种神经质的东西的话,也不会吃惊,我们会从她身上看到那种女人通常有的东西——来自时代深处,来自令人难以忘怀的压抑。因此,这种被所有人接受的状况不会妨碍、也不会阻止场景的各个方面展现出来,更不会破坏场景中的任何方面。
女人间的认同,她们的互补性(粗俗的词),会在装扮成她们的模子中——在空间、时间中,在休息、行走、倾听等等时凸起、浇铸,这不但在男人之间不可能发生,就是在女人住所里的男人面前也不可能发生。男人的身体就可能成为女人在房间、花园浇铸的障碍。我在讲我看见的和没有看见的事情:在电影中的那个下午,我根本没有在这个女人的住所里看到过男人。这个封闭的空间应该是摆脱了——清除过——所有意识形态中——从词汇的历史意义讲——压迫性的存在,哪怕在最好的情况下,由“善解人意”的男人承受。
当伊莎贝尔·格朗热行走在花园里时,整个花园都随她而动,花园与女人之间的融合显而易见,非常和谐。一个男人则不会以这种令人信服的方式“入住”花园,他的身体不会如此简单地融人花园的自然之中。我们会这样想:他到花园里想他的事去了。而我们则会这样想伊莎贝尔·格朗热:她在花园里。就这些,人们只会想到这些。
如果说电影里有男人的话,那也只有一个人,推销员。由于他的不幸,这个男人更多地属于自己的童年。十分可笑的男人:其他男人,那些“真正的男人”会这样看他。和推销员一起,我们远离了双亲模式,远离了家长模式。我们正好与此相反。电影里的男人因此就成了其他男人拒绝、而女人接受的人……电影里,女人们摧毁了他与拒绝他的男人一脉相承的一面,摧毁了他的演讲:这个人其实有理论天赋,就是在描绘洗衣机的优点时,当他只是单方面时也是这样。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