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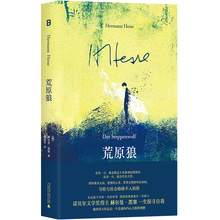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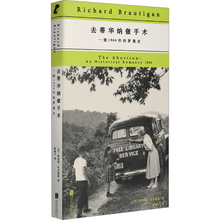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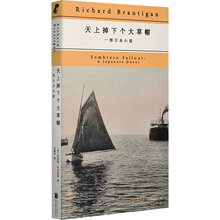

一本很好读的书,一个催人泪下的故事,一段不可忘怀的历史。
1975年4月,红色高棉来了。作者品雅特海和他那一大家子,一共十八口人,像全市二百多万人一样,被强制赶出柬埔寨首都金边,在监管下开荒种地。随后两年,柬埔寨简直成了一个大监狱农场。品雅特海一家人被赶来赶去,最后流落到柬埔寨自然条件十分恶劣的大西北崇山峻岭之中,任由红色高棉凶恶的干部驱使。家人一直吃不饱,贫病交加,备受折磨,至1977年初大多死去。品雅特海决定带着妻子翻山越岭逃往泰国,把六岁的儿子纳娃托付给别人照看。可是妻子因林中失火迷路而亡,品雅特海九死一生,终于活了下来。逃出生天后,他想念失散的儿子,悲恸不已。
《儿子,你要活下去》中记述的是发生在柬埔寨的一个真实的故事,是作者对自己1975-1977年在“红色高棉”统治下一段骇人听闻的非人生活的回忆录。这既是作者个人的回忆录,也是20世纪一段不可忘怀的历史。
第一章 革命
枪炮声把我惊醒了,一颗颗炮弹呼啸而过,哄地一声炸响了。我躺在那儿,能听出来,还有别的响动:有汽车在附近嗡嗡地空转,有牛车在嘎吱嘎吱地走,偶尔还有叫喊声。一看手表,凌晨五点。我翻身下床,走到窗前,惊奇地张望。天刚蒙蒙亮,街上一大群人,还有汽车,慢慢涌过窗前。好像全国都挤进城里来了。这天是1975年4月17日。当时我就明白了,内战终于快结束了。
艾尼(Any)这时已经醒了,静静地躺在黑暗中,说:“阿泰,怎么回事?”她一定是在望着我,等我回答。
“艾尼,快!”我很紧张,但不害怕,知道现在是时候了,该行动了,所以很兴奋。我们得走,打仗了,躲一躲。“终于到头了,红色高棉很快就要来了。”
艾尼马上说:好,一翻身下了床,穿上裙子,套上外套,动作很快,也很优美。她长发及肩,头一甩,把头发甩到一边。“会发生什么事?”她问。
我说“没事”,急忙穿过客厅,拿几件东西。“先要困难一段时间,过去就好了,一切都会正常的。”我们说话的声音把孩子都吵醒了。两个大的,苏达(Sudath)九岁,纳娃(Nawath)五岁,满屋子追跑。我们住在岳父家,住的这套房子有两个房间。“先给孩子穿衣服,赶快到市中心去,趁着军队还没到。”
艾尼叫道:“纳娃!”纳娃正在床上和苏达摔跤呢,像没听见似地。艾尼又叫了一声,声音更大了:“纳娃,叫你来,你就来!”有时,我觉得她对孩子有点太严了,但这两个孩子活蹦乱跳,上蹿下跳的,不严点儿也不行。艾尼一个箭步,一把抓住纳娃,这下纳娃可没跑儿了,一个劲儿抗议,不想穿衣服。艾尼不理,继续给他往身上套。最小的,斯涛(Staud),坐起身来,打了个哈欠,迷迷糊糊地左看看,右看看。我对老大说:“快穿衣服,苏达!没看见我们着急么?”
我们要带的东西很少,很快就装好了。柬埔寨叛军红色高棉,跟郎诺元帅的共和政府,五年来他们双方冲突逐渐升级,越来越激烈。美国人是4月12日撤走的,所以一个星期以来,我们就有了心理准备,知道内战这下快要结束了。现在,问题只是,红色高棉什么时候到来,东南西北从哪个方向来?两天前,听到枪炮声越响越近,好像是在向我们报警,叫我们赶快安排一下,暂时到别处去躲一躲,万一房子挨上炮弹就完了。我已经去看过父母亲了,大家约好了,如果局势坏到了极点,全家就都住到我堂弟欧安(Oan)家里去。他家离市中心很近。我们把汽车都加满了油。现在,剩下要做的,就是装上两个行李箱的衣服,收拾好艾尼的细软,带上我们的积蓄,还有我的外汇:一共三千美元现钞,每张面值一百元。我抓过来一个小收音机(听新闻广播很好用),又拿一个盒式录音机,里面有备用的电池。除此之外,我还放进去几样东西,以应工作上的不时之需:讲灌溉和修梯田的书,一本法-英词典,还有纸笔之类。
艾尼在给纳娃穿鞋,他硬是不穿,乱踢乱闹,艾尼硬是把鞋给他往脚上套。正在这时,艾尼的姐姐,艾尼甬(Anyung),急急忙忙地跑了进来,说她和艾尼的父母都准备好,要走了。斯涛刚换掉尿布,艾尼甬给斯涛穿上短裤,T恤衫,艾尼又拿了些饼干糖果,预备给孩子吃。我检查了一下拿的东西:书,手表,钱,身份证件,收音机,盒式录音机,最后又环顾了一下四周,心想,要是当初把家人送到国外去就好了。不,郎诺这个腐败政权,我最讨厌了。红色高棉,没什么可怕的。
我急忙把家人送到艾尼父母那里。她父母已经坐在奥斯汀车里了。我把行李一件件推进我那辆菲亚特车里。这时,全城乱了套,一片嘈杂,我大声喊,别人才能听见。机关枪声,远处炸弹的爆炸声,马达轰鸣声,响成一片。我们一点儿一点儿往外蹭,终于开了出来,上了路。
金边有很多宽敞的大马路,这条街道是其中之一。街上人潮滚滚,汽车,三轮车,自行车,手推车,摩托车,一辆接一辆往前走,还有几辆牛车,上面站满了人,堆满了东西。这时,天刚刚蒙蒙亮。有些人全家步行,父亲推着自行车,车上满载着各种家当,母亲背着孩子。人人神色惊慌,面容疲惫,奇怪的是,大家都不说话,一声不吭。开车的司机,一反常态,好像都特别有耐性,车速像走路一样慢,谁都没有按喇叭的。几天前,金边还是车水马龙,争先恐后,哪成想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共和国现在已经亡国了,街上甚至还有几伙当兵的,三五成群走在一起,肩上斜挎着枪,他们不害怕,嘻嘻哈哈,彼此开着玩笑。战争结束了,他们很高兴。
人流慢吞吞地往前走,我们往前走了大约一百来米,忽听一声爆炸巨响。在我右边,我家房子旁边转弯处,一个巨大的烟柱冲天而起。不出几分钟,救急车、救火车全到了,又是鸣笛、又是闪灯,冲开一条路,跑到前头去了,我们不得不停下来给他们让路。
尽管周围人群有一种事态紧急的感觉,尽管战场离这里很近,可我觉得没什么大危险。内战都打了好几年了,我父亲也警告过,红色高棉本质不善,但我没在意,觉得一切都会过去,柬埔寨还会恢复正常,回到内战前那样。
我老家在乌登(Oudong),乌登是个小村庄,在金边北边,离金边四十公里。我父亲名叫弛和(Chhor),做小买卖为生,并不富裕。我家的红瓦房只有三个房间,屋地的地面是用土压实的。但是我父母望子成龙,对我寄予了厚望。我妈名叫娄恩(Loan)。我家有五个孩子,我老大。父母把我送到金边,好让我能受到良好的中学教育。我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学生。十七岁那年,全国学年统考,我的数学成绩排全国第一名。
当时,我对政治想都没想过。我的少年时代,安居乐业,和后来相比,真是黄金时代。当时,柬埔寨是中立国家,西哈努克亲王当政,受人民爱戴,国家也蒸蒸日上,没有什么困难。越南战争离我们很遥远,没什么影响。美国卷入东南亚,也没听人谈。
作为优秀学生,我符合条件,可以获得政府奖学金,到国外留学。按照传统,柬埔寨学生都是去法国留学。但是,法国当时已经成为反对西哈努克的反对派聚居之地,所以,我和其他好几个学生就被改派到加拿大留学去了。我在加拿大蒙特利尔理工学院(Polytechnic Institute in Montreal)学习期间,社交活动非常活跃,曾经当选为大学外国留学生联谊会的会长,联谊会取名为“Cosmopolis”(意思是:国际大都会)。
我学的是土木工程专业,1965年毕业后,回到柬埔寨,开始了新的生活。我在公共建设部工作,结了婚,第一任妻子名叫莎莉(Thary)。新婚夫妇通常和妻子的父母住在一起。我们也是,住在莎莉父母家。房子很大,因为他父亲,阚牧(Khem)先生,是财政部的官员,家境殷实。我们的儿子苏达,是1967年出生的。我们全家似乎都有一个锦绣前程。
但是现在回想起来,当时已经露出乱世的端倪。西哈努克自封为国父。没过多久,就开始风传政府任人唯亲,贪污腐败。这时,越南战争正是最激烈的时候。西哈努克急于和强大邻国保持友好关系,和睦相处,于是暗中同意北越借道柬埔寨东部地区,运送人员和军火到南越。这就引起了美国的注意。柬埔寨传统奉行中立政策,这样一来就中立不了了。
这种局面让红色高棉钻了空子,从中渔翁得利。红色高棉的头头大多是法国留学归来的知识分子。这股叛军本来没几杆枪,人数很少。当时,有很多柬埔寨人对社会不满,就源源不断地支持它。
不过,这些对我们的生活并没什么影响。但我也有我的难唱曲。1969年,我的人生遭了难。我们正在盼望下一个孩子出世的时候,我的妻子莎莉得了肝炎,她当时才二十四岁,病一直也没有好。她和孩子都在分娩时死去了。我哀悼她哀悼了一年的时间。我出去上班,儿子苏达就全靠莎莉的两个妹妹帮忙照顾了。这姐妹俩一个叫艾尼甬,当时二十一岁,另一个叫艾尼,十九岁。尤其艾尼帮忙最多。
后来,我就爱上了艾尼,仿佛这是世界上最自然不过的事了。艾尼是个美丽的姑娘,黑发及肩,身材苗条,当时二十岁。她愉快地承担起繁重的家务。她爱苏达,视如己出。我们结婚了。1971年,第一个儿子纳娃出世了,1973年,又生了斯涛。
七十年代初那几年,我升为部里新工程设备处处长。这时候,内战可是越打越激烈了,内战产生的后果有政治的,也有经济的。因为我有这个职位,所以能保护我和家人,免受其害。艾尼一直生活在父母家中,没过过别样的生活,对我的政治判断从未质疑过。我想,我们也像身边的其他人一样,知足了,觉得生活这样就行了。
西哈努克的政策是取悦于所有的人,这样,中立的样子就装不出来了。国内进来这么多北越的部队,据估计,约有四万人。美国总统尼克松下令轰炸北越军队,战争悄然扩大,对他、对我们都是后果严重,伤害极大。轰炸却事与愿违,倒把越共赶到柬埔寨更内地的地方去了。
1970年,大快人心事,西哈努克被首相兼军头郎诺推翻了。郎诺许下诺言,要根除贪腐,驱除越共。西哈努克逃到北京,宣布支持红色高棉游击队。这可是惊人之举,红色高棉以前是他的敌人。这支叛军,农民所占比例越来越大。西哈努克说他们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没什么,不必担心,改口称之为解放者。
起初,我们都对郎诺寄予厚望。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地看清了郎诺那两下子。他定的目标,要做的事,根本没那个能力,干不成。后来,他又中风了,半身不遂。他那军政两界仍然贪污腐败,不思进取。军队即使有美国帮助,对北越和红色高棉还是束手无策,奈何不了人家。红色高棉在国外势力支持下,坐收渔利。全国一败涂地,陷入全面内战。通货膨胀如脱缰野马,迫使我们这样能出国的,都囤积外币,尤其是美元。1970年,1美元能换60瑞尔(Riel,柬埔寨货币单位),到了1975年,1美元能换2,000瑞尔了。
说来怪事,金边因为郎诺明显无能,像我们这样的专业人士、知识分子,往往都相信西哈努克的路线,以为地下分子都是民族主义者,不是共产主义者。西哈努克的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总部在北京,他们的纲领不提共产主义,用词很能宽解人心,如:“柬埔寨人民”,“民族独立”,“中立”,“自由”,“民主”云云。红色高棉通过秘密无线电广播许下诺言,说他们一旦胜利,马上就会恢复和平,只有共和政府的几个最高领导人才会被处决,他们号称“七大卖国贼”。
我也参加了反对郎诺的行列,成立了一个组织。我们给这个组织起了个名,叫“蜜蜂俱乐部”,这是一个给志同道合的专业人士发言的社会论坛:文职公务员,大学教师,军官,还有几个反对派政治家。我们反对极权主义者,反对柬共,也反对郎诺政权,我们也不支持什么特定的个人。我们对美国人看法有好有坏,他们反对柬共,但是也支持声名狼藉,腐败无能的郎诺。我们支持民族和解政府,也就是说,这个政府应该是个联合政府,如果可能的话,也应包括柬共在内。
当时,说柬共不是爱国者,我当然不会相信,因为我认识很多人,他们都支持红色高棉,有的还加入了红色高棉。我是高棉工程师协会秘书长,协会里有几个左派会员就是这样的人。我父亲,1972年举家搬到金边城里来之前,见过无数难民,并且和他们交谈过。父亲总说我的看法不对。我就告诉他,别太悲观了,硬说他是受了郎诺政府的蛊惑宣传。我说,西哈努克毕竟在游击队里有他自己的人。杀害同胞、毁坏佛塔那号人,他是绝不会支持的。我说,那些人里有的可能是柬共,但是他们像我们一样,首先是柬埔寨人。
1975年3月初,大家觉得,可能会改组政府,可能红色高棉会把郎诺撵出去,但是我们以为,这样一来就能有条不紊地建立新政权了。我还设想,不论政治解决怎么个解决法,终究都离不开西哈努克。
确实,很多人都没有收拾行李走人,只有高官显宦才会害怕,他们的官位可都是郎诺政权给的。但是,4月1日,郎诺听从劝告,离职卸任了,从而排出了最后障碍,可以谈判解决国事了,可以在名义上放手让隆波烈执政了(译注:隆波烈,柬埔寨名是Long Boret,1933-1975,柬埔寨政治家,1973年-1975年任柬埔寨总理,曾与红色高棉和谈未果,红色高棉攻占金边后,被立刻逮捕处死)。旧政权名存实亡的时候,我觉得没有什么可害怕的。我只是一个工程师而已,没有必要出国避难。我盼战争尽快结束,盼能在新柬埔寨施展我的才能。
在这人山人海当中,几公里的路竟然走了两个小时,真烦死人了,最后终于到了河滨那边的住宅区萨西莱(Psar Silep)。这里是市中心,金边的黄金地带,街道宽阔,绿树成荫,法国殖民时代风格的一座座别墅,错落有致。这是一个开放的城市,宽敞得很。单调的玻璃混凝土建筑物之间地方很大,有很多树、花园穿插其间。我堂弟欧安(Oan)就住在这儿,住在一所漂亮的二层小楼里,四周有一人多高的围墙,还有一个大铁门,挺安全。大家都到这里来真不错,这个大宅子里只有欧安一个人在家,他妻子和儿子几周前跟着她父母一块儿出国去了。
我岳父岳母和艾尼甬去附近大姨家避难去了,很近,离这里不远。我把我那辆菲亚特车开到欧安住的胡同里。屋里来了一大群亲戚,我吃了一惊:欧安,他两个姐姐,姐姐的家人,我两个妹妹,两个弟弟,弟弟妹妹的家人,还有我父母,一共有三十来口人,大家挤在一起,围着我们,看到我们,显然松了一口气。他们已经来了一个多小时了,正在为我们担心呢。
孩子们跑出去,和堂表兄弟姐妹们到花园里玩去了。女宾开始做饭,大家都动手,忙这忙那,唯独我妹妹莴齐(Vuoch)没参与。她呆在这里和男宾聊天。莴齐二十一岁,是家里的大文人,最有学问。她在上大学,大三了,工程学专业。柬埔寨女孩一般都不选这个专业,偏偏她选了。她渐渐地练就一脸严肃的表情,衣服穿戴很简朴,似乎打定主意要逃离我国传统女性的角色,在男人世界里干出一番名堂来。她和我母亲、艾尼、孩子们说话,像她姐姐肯娥(Keng)一样,总是问寒问暖,但也最容易精神溜号:只要有人稍微一提,说要讨论政治上的事,她就马上放下手上的活去凑趣,笑一笑,说一会儿回来接着再做。不让她插嘴,那可办不到。
靠墙的一张桌子上有一台收音机开着,不过没有新闻,全是军乐,哇啦哇啦响个不停。我弟弟特恒(Theng)朝收音机挥了挥手,叫关掉,问我,依我看城里出了什么事。特恒才比我小两岁,结婚了,有两个男孩,一个女孩,女孩还是个婴儿。但是政治上的事,他听我的,不仅仅是我比他大,而且还因为我在部里任职。他是小学教员,还和我父母住在一起,最感兴趣的是打篮球,对政治不怎么关心。他身材高大,有什么体力活要做,就派上用场了。我故意说,哦,两边的官员可能正在谈判,要拿出个解决办法来,并且…
我妹妹莴齐插嘴说:“那为什么他们不在收音机上宣布呢?”
我故意说:“是啊,有点奇怪。”我避开她的目光,不想直截了当和她说实话。“不管怎么说,没事的,不用担心。很快就会有新政府了,西哈努克亲王又会回来当政了。你就看吧。”
“嗯,他最好别再犯同样的错误啦。”
一时间,大家都没吱声。为了破破这个气氛,有人问道:“你怎么看,萨仑(Sarun)?”
我们大家互相对看了一眼。可怜的萨仑。过去,他一直做教师,两年前坐摩托车出了车祸,头负重伤,从此就不当老师了。出事以后,他好像变了一个人,过去很外向,总好开玩笑,张嘴就来,从那以后总是闷闷不乐,喜怒无常了。他常常像小孩儿似地那么胆小,头脑倒还清楚,只是有时怒气冲天,或者说着说着,突然话题一转,转到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上去了。当然,学校也就没继续聘用他,他自己也没弄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倒有一件事没变:他还是那么爱自己五岁的女儿斯瑞(Srey),爱自己的妻子肯娥。
萨仑还像平常那样,淡淡一笑,回答说:“我怎么看?我也不知道,但是,如果西哈努克回来掌权,说不定我还能把工作找回来。你说呢,特海(Thay)?”
他相信,一定是有人合谋陷害自己,究竟怎么合谋陷害的,现在还说不得。我笑了笑,耸一耸肩。
“你笑什么啊,特海?”厨房传来肯娥的声音,稍微有点责怪的意思。“事情解决之后,萨仑肯定能把工作找回来。萨仑,帮帮忙好么,帮我把斯瑞抱来。饭菜都好了。”
我们都钦佩肯娥。她对萨仑又忠贞,又呵护,萨仑真有福气。
恰好这时传来一阵急刹车的声音,自行车倒了碰到墙上的声音,把我们的谈话打断了,门口站着我年轻魁梧的堂弟西姆(Sim)。他环视一周,张着嘴笑,好像刚从城里兜风回来。
欧安惊叫道:“是西姆啊!你来干什么,没带你爸妈来啊?”
“啊,他们没来么?我还以为……”他没往下说,皱起大眉头。
我爸从小就认识这孩子,说:“没事,没事,别着急。”西姆十八岁,还在上中学,但学习不好,总爱和朋友们逛街,搞恶作剧,亲友们都有点烦了。可是他总能逃过惩罚。他总微笑着,辩解说自己清白无辜,到头来谁都会放过他。
“叔叔,我还以为他们会在这儿呢。有个房子着火了,我去看热闹,然后就找不着他们了,所以就到这儿来了。我还是去找找他们吧。”
“不用找,不用找,傻孩子。他们没事儿的。你就在这呆着,再出去太危险了。”
这事说定了,我们就找地方坐下,艾尼和别人从厨房端来饭,肉,水果,我们就吃起来。胡同口挤满了难民,人声嘈杂,收音机里又传来刺耳的音乐声,我们提高嗓门,又谈起来,猜测局势会怎样发展。我把我的想法又说了一遍,认为会有个政治解决方案。十有八九大家都同意我的意见,不同意的就不吱声。特恒不好说话,我二弟特侯恩(Thoeun)更是寡言少语。他长这么大,大部分时间都不在家,在外边,现在和岳丈一家住在一起,回到家中觉得自己成了客人。我妹妹莴齐说出了自己的看法。艾尼人一多就不说话了,大眼睛东张西望的,谁说话,她就看谁。虽然这是在欧安自己家中,但是欧安话也不多。他家有钱,倒不是因为他伶牙俐齿才有钱的,而是他命好,娶了富家小姐为妻。他岳父有好几家剧院,可是谈起政治来,就不行了,不懂。
但是我父亲很健谈,他很悲观,总是叫大家小心红色高棉,说红色高棉是柬共。父亲身材高大,体格很结实,性格也坚强,还有耐性,说话不多,很有头脑,所以他说什么,大家都很尊重他的意见。但是他把将来说得很吓人,我听了很生气。以前全听他说过,我就一遍一遍对他说,不要杞人忧天。
“爸,那都是谣言,都是宣传,骗人的,”我不耐烦了,但尽量不表现出来。“看看他们的纲领,没有写共产不共产的。那些人里,有的是我朋友。他们不会说假话骗人的。为什么要说谎骗人呢,我们国家是富国。他们不用实行什么苛政就能让人民吃饱饭。”
父亲不说话了。这时,我母亲开口了。她像一阵风就能刮倒似地,比女儿们矮十来厘米呢。母亲一生都在村里度过,把孩子一个个拉扯大。只要母亲一开口讲话,就能听出来,莴齐好斗的劲头是从哪里来的了。
“特海,不可以顶撞你爸爸。”母亲的语调很平静,但很坚定。“我们和逃难的人搭过话,他们家人都被杀害了,房子都被烧了。红色高棉是柬共,要是他们上了台,咱们的宗教就完蛋了,幸福就别指望了。“
我说:“啊呀,妈呀。柬共怎么了?他们有人可能很厉害,但是他们也知道,柬埔寨人民信教得很,太热爱生活了,不会接受他们柬共那套的。他们首先是爱国者,然后才是柬共啊。他们会遵重民意的。”我自以为说得对。我地位优越,联系那么广,信息那么多,别人是接触不到我那些信息的。再说,我还出过国,留过洋,视野比别人宽。我父亲不过是村里做小买卖的,他们夫妇俩能知道什么真情实况?“
我们谈了一个来小时,其间不时有孩子叫喊,远处沉闷的钟声传来,我们才打住话头。突然间,十点钟左右,收音机里的军乐停了,有个尖声尖气的声音开始讲话。这声音是新来的,以前全国广播从来没听见过:“请注意!准备收听重要公告!”大家都发出嘘声,叫别人别做声,注意听,并把亲戚家人从厨房里、花园里叫进屋里来。我招手叫艾尼过来,艾尼看了一眼纳娃,见他正在花园里和堂兄弟姐妹们玩呢,就急忙进屋里来。
鸦雀无声。
收音机里传来佛教长老胡塔特(Huot Tat)那微弱的声音。我们大家都面面相观,放心地笑了。胡塔特不仅是全国最高宗教权威,也是稳定的象征。他也是我们的亲属,是我父亲的舅舅。
我对他很有感情。他非常关心我上学。我敢肯定,正是由于这一层关系,我上学的时候才能从佛教信仰中汲取力量。佛教似乎很适合我的抱负,适合我的性格。佛教教导说,拯救在于自身。上天无能为力,除非你自己主动自救。所有美德,所有恶行,都会影响今生来世的。但是人永远可以祈求佛祖领路,祈求佛祖赐给明亮视野,通过行善,用所获得的优良技能尽量办好事,这样就能自我完善,就能“行善”,就能培养出道义感。由于胡塔特对我的深远影响,我肯定是尽我所能了。
这位令人高山仰止的长者,其地位是毋庸置疑的,他的指导,他的保佑,新政权也一定是求之不得的。我渴望在他的话语里找到慰藉,我的渴望可能比别人更加强烈。
他说:“不要惊慌,不要打仗了,和平现在就要降临。困难时期,我国已经熬过去了。我们必须要重建。”他就说这几句话,这几句话就够了。
然后,另一个人开始发表广播讲话,是共和军参谋长梅斯臣(Mey Sichen)将军。他说:“我们正在和兄弟们进行谈判,全体军人都要放下武器,避免流血牺牲。”
我当时想,一切都结束了。我拥抱了一下艾尼,对她小声说:“太好了!”我们俩都笑了,这下放心了。
但是,不一会儿,不知谁在说什么,把将军的话压下去了。这时,另外一个声音插了进来,声调很横,好像有人把麦克风抢了过去:“战争是靠枪杆子打赢的,不是谈判谈赢的!政府军已经投降了!地下部队已经胜利了!现在,战争结束了!”
然后突然就没声了,令人惊恐不安。没有音乐,只有静电干扰的声音。我们的笑容消失了。有人把收音机关掉,然后又打开,看看是怎么回事。什么节目也没有。我们睁大眼睛,你看我,我看你。
大家一言不发,我忽然听到街上叽叽喳喳有人说话,但听不清楚说什么,还听到街上马达轰鸣。我们和邻居都被牢牢地锁在了屋内,但是外面成千上万的人正在涌进金边市中心来。他们要去哪里?可能他们是想进佛塔,进大学,进公共建筑物,到那里去安营扎寨,等打完仗再撤出去吧?
一个小时过去了。孩子们还在玩耍,成年人彼此之间在低声谈论着。这是,忽听远方传来欢呼声。西姆跳到外面,看是怎么回事。顷刻间又急忙跑回来,喊道:“是红色高棉!”
原来真地结束了。大家赶快跑到外面,打开大门看。
街上家家户户,房子上,窗户上,都装点上白色的东西。人们把衬衫,床单,毛巾,反正凡是白色的东西全都挂了出去。这时,人潮滚滚,顺着大街,往远处涌去了。显然,人群是去看什么队伍行进去了。队伍要在柏莫尼翁(Preah Monivong)这条主要大街上经过。这条大马路是从南边延伸过来的,离我们有三十多米远,与我们住的这个小胡同相交。我招手叫艾尼和孩子呆在一起,我和几个人挤过人群,挤到前面去看。此时此地,我生平第一次看到了红色高棉的军队。
路面已经让出来了,人群都挤到两边人行道上去了。路中央,红色高棉士兵排成一列纵队,分成小分队,每队五十来个人,鱼贯而进。这样的兵,我可是以前从来没见过。这种场景通过电影、照片,很快就将传遍全世界。可是,他们这种形象,事先谁都没给我们讲过。红色高棉军都穿黑衣服,军装很简单,像睡衣的模样,什么肩章帽徽都没有,但是纽扣都扣得很整齐。这些兵头戴中式黑帽,脚穿胡志明凉鞋。鞋是汽车轮胎作鞋底,用内胎条条系到脚上的。有人拿着AK47型步枪,有人扛着火箭发射筒。人人都有一条方格围巾,有的罩在帽子上,有的系在脖子上。他们走的倒不是正步,不过并不拖沓。人人双目前视,没有笑容。没一个像是十八岁以上的。我事先没有期待,所以现在也就不觉得意外,当然更没有大祸临头的感觉,只是这些少年兵,个个板着脸,面无表情,有点让人不安。后来见到红色高棉军队受到欢迎的场面,更加忐忑不安了。市民跟在军队后面,鼓掌欢呼,大有解放的感觉,什么恐惧都没了。但是尽管群众热情欢呼,那些冷酷的少年兵可是无动于衷,还是两眼朝前直视,目光空茫,一点表情都没有,好像机器人一般。
我们大家都松了一口气,都没有看出来他们的行为举止有什么深意。战争结束了。我们大家还都健在,没受什么伤害。难怪年轻人互相拥抱,挥动着白布庆祝。我和大家一样,没觉得有什么恐惧感,倒是看到红色高棉军并不嚣张,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战事说停一下子就停了,也够惊人的,万万没有想到,红色高棉军进城并不是杀开一条血路杀进来的。
只有一次,我吓得心里一揪。便道上突然开出来一辆军用卡车,开车的是一个共和军士兵,或许是回家吧,再也不打仗了,非常高兴。一个红色高棉士兵抬起手来,示意叫他下车。那人没带武器,跳下车来就跑。一个红色高棉兵,抓起枪来,飞快追了上去,把那人抓住了。红色高棉士兵令那人贴墙站着,端起枪,对着他。过了好一会儿,红色高棉平静地命令那个士兵把军装上衣脱掉,把汽车扔下,走人。那人遵命而行,于是红色高棉兵转身走了。我的心又放了下来,觉得完全不必担心了,将来肯定没事儿。
我们回到欧安家,高兴极了,有说有笑,计划着未来。我说,我要把家人接回家来。有人说要去海边玩玩,庆祝庆祝。似乎一切即将恢复正常。艾尼的父母,开着他们的奥斯汀汽车回家,途中到这里来看看。我们正要走,忽然欧安说:“干嘛不吃完午饭再走呢?”是啊,干嘛不吃完再走呢?家里有岳父岳母看家,我们回去,他们才能走呢。孩子们正在花园里玩。才上午十一点。不急。我们留了下来,和大家谈天说地,笑声不断。
大家正在吃午饭,我已经在寻思,明天是不是照常上班,忽然,进来一个人,上气不接下气。这人是给欧安岳丈家看家的,住的地方离这里大约两公里半,就在红色高棉进军的那条路上。几个星期之前,欧安岳父岳母带着欧安妻子和孩子出国了,托这人帮忙看家。这人站在门口,衣冠不整,很害怕的样子。“红色高棉把我们赶出家门了!叫我们到农村去,不准住在市内!所有人都得走!” 看得出来,他愁坏了。“我该怎么办啊?”
气氛顿时大变,心沉了下去。我们不吃了,七嘴八舌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
“肯定么?”
“为什么?”
“你一定是弄错了吧?”
“以前没听他们说过这样的话啊。”
难道是他在开玩笑么?疏散出城,城里不许住人,这是谁的主意,这还了得!
我们得打听打听,弄个明白,于是去问邻居,这是怎么回事。他们也听说了,是要搬走,市里不许住。但是收音机里没广播啊。官方没表态,这说明,还是应该继续往好的方向想。
我们乱了方寸,不知道怎么办好了。难道我们都走,不在欧安家住了吗?必须打听明白,也好做打算。我建议去问问我们的舅爷,胡塔特长老(Patriarch Huot Tat)。他住在欧娜龙佛塔(Onalom Pagoda)那里,离这里三公里多的路,就在河边。他一定会知道情况的。咱们问问他该怎么办,对我们也能有个保护。
别的办法是想不出来了。大家全都挤进汽车里来了:我的菲亚特,我弟弟的别致,欧安的奔驰。我们又一次加入了逃难人群那缓慢行进的队列。街上还是塞车。不仅有从郊外往市中心去的,现在又多出了被逐出家门的人群。大家神色慌张,但是不乱,也不嘈杂,只是人山人海,缓慢向前移动,步行的,骑自行车的,推三轮的,开车的,人流滚滚。远处时而传来一声枪响,我们又想起了战争,警觉起来,不知道谁向谁开枪。突然之间,大家都非常守法,有礼貌,认真遵守交通规则,好像是害怕造成交通事故,害怕被人注意到。
过了一个多小时,我才见到红色高棉。只见三十来个红色高棉从临近一条街上走出来,站成一排,一声不吭地走在马路中央,假装没看见四周的人群。汽车和行人都靠边给他们让路。他们迈着正步,从我们身边走过,对我们理也不理,好像怕被我们传染上什么病似的。
长老的佛塔坐落在佛寺地界之内,寺庙两层,黄瓦屋顶又高又陡,拱柱回廊,顶盖不高,像眉毛似地盖在上面。佛塔离河岸不远,居高临下,俯瞰着这一片汪洋。湄公河与洞里萨湖(Tonle Sap)从北边蜿蜒而来,在此汇合后,左拐右弯,又分成两大支流,向南流去,一个是湄公河,一个是巴萨河(the Bassac River)。紫袍僧侣的居所,周围绿树成荫,百花争艳。
我们把车停好,领着孩子,走向高僧的寓所。我们走进巨大的门厅,门厅上有顶盖,四面无墙,厅里已经挤满了人,可能有一百来人。别人等在外面,我父母,我,欧安,还有我弟弟,走进高僧的待客室。
长老八十五岁了,身子骨还那么硬朗。他坐在凳子上,高高地昂着那剃光的头,看面容,可不像是八十多岁的人,要年轻许多。他身穿黄袍,一肩袒露在外,身边围着一大群人,有僧侣,也有平民。一来就看出来了,很多人都像我们一样,来这里想问个究竟,并且寻求高僧的保护。我立刻认出来两个人,一个是秦春(Chhim Chhuon)将军,曾任郎诺元帅的副官,一个是毛孙坤(Mao Sum Khem)将军,共和国武装部队作战协调总长。这两个人,以前张牙舞爪,现在唯唯诺诺,心里没底的样子。其他穿便衣的,显然是他俩的保镖。我们和别人一起跪在地上,举手合十,举过头顶,三拜行礼。礼毕,我们回原位盘腿而坐,听他们谈话。
我们一听,基本上谈的是两大问题:共和军军官应该怎样应对红色高棉这个胜利者?为什么要把平民百姓赶出住宅,驱离家园?据报道,好像红色高棉正在把全市居民往外赶,要把全市变成空城。高僧敦促大家保持镇静,不要惊慌。他说,可能不是全城都要撤离。红色高棉的纲领上从来没有说要大规模流放百姓。我还听他说:“把人赶出城市,这是不合逻辑的。保持镇静,等候命令吧。”
长老吩咐一位僧人先给柬埔寨红十字会会长打个电话,然后再给民主反对党总书记曹騒(Chau Sau)打个电话。这两个人总能提供一些信息吧。可是,他俩好像什么都不知道,只听说,红十字会已经指定,乐金酒店(Hotel Le Phnom)和法国大使馆为中立区域。
有人指着住持身边桌上一台半导体收音机,叫大家肃静,不要说话。政府电台又播音了,播了一条简短消息。所有部长,武装部队所有高级军官,那天下午四点,都要到信息部报到。长老说:“现在你们知道该怎么做了吧,我也要派代表到那里去。”
那两个将领和一个僧人走了以后,我们就走来走去,互相询问,刚才的广播是什么意思,心中在想,是呆在这个地方呢,还是去法国大使馆或者乐金酒店呢。长老仍然盘腿坐在座位上,静静地等待。
这一下午过得很慢,等得大家坐立不安。我苦苦思索,不知道我们这些人是该走还是不该走。看样子,不是好兆头,心里一点底也没有,万一出去被抓住,强迫出城,那可怎么办,有什么打算也白搭,实行不了。我疑虑重重,所以就没叫大家走。过了一阵子,为了缓解一下紧张的气氛,我就请长老允许我给法国大使馆打个电话。电话通了,我说我们现在长老这里暂避一时,想要申请到法国大使馆避难。电话那头说,凡是柬埔寨人,法国大使馆一律禁止入内。大门是红色高棉在把守。那人还说:“就是长老本人来叫门,红色高棉也不会让他进去。”我放下电话,非常震惊,居然会有柬埔寨人不承认长老的权威。我第一次意识到,糟了,我们陷入绝境,出不去了。
我给岳父岳母、艾尼甬家打电话。没人接。没办法,等着吧。我走来走去,安慰艾尼,让她放心,告诉她打电话的情况,又和孩子们说了说话。孩子们很高兴,正在跟同龄的小孩玩呢,跑进跑出。
天要黑了,六点左右,长老的代表回来了。他穿过人群,向长老走去,我跟在后面。长老举起手来,示意大家肃静。我仔细观看那位信使,想在他脸上看出点好消息来。可他面无表情。
他说,有很多共和军高级军官和各部部长到会,总理隆波烈(Long Boret)也来了。那位僧侣当时坐在一个红色高棉军官旁边,那军官和他说话时毕恭毕敬。那军官还赞颂了红色高棉的种种美德,说是有了前政府官员、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的帮助,现在可以搞建设了。僧人问起强迫出城的事,那军官摇摇头。这样的命令是胡说八道。现在正是要让经济走上正轨的时候,为什么偏偏在这时候要把身强力壮的男子赶出去呢?“他对我说:我用我的名誉向您保证,我从没听说过有这样的命令。这是帝国主义的阴谋诡计。他们的特务想要在人民当中制造恐慌。“
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我出去告诉艾尼,让她放心,强迫出城的事是谣言,不是真的。可是这时候还是不断有难民涌进塔区,说外面正在把人赶出家园,往城外赶呢。我越来越纳闷了,害怕起来。那军官,若不是被人误导,就是他在说谎。欧安盘问那僧人,僧人忙说,不会,不会,那军官不可能骗人。或许,他说得不太准确,不太知情吧。
夜幕降临了。我又一次给岳父家打电话。还是没人接。难道他们已经被强迫出城了么?我把最坏的情况设想了出来:艾尼的父母和姐姐艾尼甬被扔进难民潮里,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哪也去不了。我和艾尼对视了一下,不知她是否也像我一样在担心,于是对她笑了笑,让她放心。
这漫长的一天愁死我们了,累得很,晚上在塔区砖地上席地而卧。我们一共三十个人,每家睡在一块儿。没见过这样的气氛,有点慌张,孩子们个个听话,连纳娃都很乖。我把收音机藏在衣服下面,收听美国之音的柬埔寨语广播,看有没有什么消息。什么消息都没有。我把收音机关了,可是睡不着。新来的人来来往往不断,找地方躺下。每个新来的人都说,外边正在把人赶出家门,逐出市区,不许在市内住了。指证越来越多。好几百人涌进塔区来,更有成千上万的人正经过门口,被迫出城去了。
大家睡着以后不久,大约九点半左右,大厅里进来一个红色高棉军官,手里握着手枪,年纪和我相仿,也是三十刚出头的样子。在刺眼的灯光下,他审视着四周,手枪直对着地上睡眼惺忪的人们,看他那样子就好像他早就料到,里面肯定有人反对他似的。然后,他盯上了放在门口的那六辆自行车,三台摩托车。
“这三台摩托车是谁的?”他喊道。没人吭声。他把手枪放进枪套里,走过去,抓起一辆崭新的蓝色本田摩托车。那车用锁链锁在另外两台车上了。他重复问了两遍:“这摩托是谁的?”又说:“安卡需要!”
“安卡”(柬埔寨语,意思是“组织上”):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词这么个用法。
还是没人回答。那军官把摩托车推倒在地,掏出枪来,枪口对着走廊方向,对锁链连开两枪。锁链打断了。大厅本来鸦雀无声,挤满了人,地上到处都有小孩在睡觉,枪声把大家吓了一跳,很害怕。孩子惊醒了,迷迷糊糊地四处张望。那军官马上就骑上摩托车走了,我们感到震惊,一言未发。艾尼看了看我。我挥了挥手,示意她别做声。
过了一会儿,艾尼小声对我说:“那家伙怎么能干出这样的事呢?”
“如之奈何?”我答道。
我父亲意味深长地看了看我。
“也许,不都像他那样吧。”我对父亲小声说,好像是在辩护。
过了十五分钟,又进来两个当兵的,不由分说,把另外两台摩托车也抄去了。
我明白,大家也都明白,这行为远远不止是盗窃,也不只是侵占。长老的重要作用远远超过宗教范畴。在柬埔寨,即使最穷乡僻壤的村寨,人们都敬重他。可是,在我们眼皮底下接二连三来的这几个人,他们显然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至于对长老本人不敬,那就更不用说了。数百年的道义价值观就要被推翻了。这才刚刚露出个苗头。
大儿子苏达刚才惊醒了,这会儿又要睡着了,问道:“爸,什么时候回家?”我无言。还是艾尼答道:“睡吧,孩儿啊。明天就回家。”我不信回得了家,肯定艾尼也不信了。
……
前言
序言
英文原版鸣谢
第一章 “革命”
第二章 被赶出家园
第三章 “解放区”
第四章 “肃清”开始了
第五章 鬼城
第六章 死亡丛林
第七章 “安卡”这个祸害
第八章 逃出东埃
第九章 煽旺仇恨的火焰
第十章 逃进森林
第十一章 孤身一人
第十二章 自由
尾声
★1975年,柬埔寨共和国被波尔布特的部队扯得粉碎。在公共建设部工作的工程师品雅特海是这个悲剧的见证人……他所有的家人,他无数的朋友都被害死了……整个一个社会体系被红色高棉干部的偏执狂政策摧毁了。这是一本令人心碎的回忆录。
——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书评
★柬埔寨革命疯狂时期,所有的城市居民都被赶到农村干活,制造出一个个新的农民村落,按照严厉的、教条的路线运作……品雅特海当时出逃,怕孩子累赘逃不出去,就把孩子扔下了没有带走,又因为一时糊涂,没把妻子看护好,她迷失在原始森林中,葬身林海了。这个愧罪感将永远折磨着他:他的叙述揭示出人类良知的史前力量无比强大,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
——英国“泰晤士报文学副刊”书评
★1975年4月17日,红色高棉进入金边。在48小时内,金边全市的居民都被赶出城外,强制劳动。接着马上开始大屠杀,专杀知识分子,中产阶级,旧社会的管理人员,所有敢于抗拒的人都格杀勿论。这个国家的边界关闭了四年。全国人口原有八百万左右,被害死的人数在一百七十万到二百二十万之间:波尔布特及其“安卡”(红色高棉组织)狂热盲从的暴徒杀害了约四分之一的国人。
——法国“费加罗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