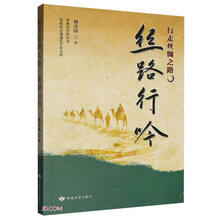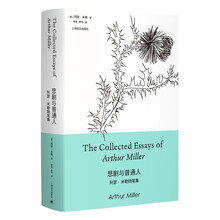扬州,一直是我向往的地方。四十多年前,我读中学,看到了诗人闻捷写的一首题为《史可法衣冠冢》的短诗,很为诗和诗中所讴歌的史可法感佩,对扬州充满想象。后来,读到清经史学家全祖望那篇著名的《梅花岭记》,看到他记述的史可法壮烈殉国的场面:大兵如林而至之际,忠烈乃瞠目日:“我史阁部也!”劝之降,忠烈大骂而死。死前,他留下遗言:“我死当葬梅花岭下。”少年的心,被一腔壮怀激烈所燃烧。对扬州更是无比向往。扬州,在我的心里,是史可法的扬州,是一地梅花怒放的扬州。
真的来到扬州,已经是十多年之后,上个世纪的七十年代末,那时,我正在北京的中央戏剧学院上学,写了一篇文章,投稿给南京的《雨花》杂志,当时的主编顾尔镡先生打电报要我去南京改稿。暑假里,我到南京改完稿,心想离扬州很近,便乘长途汽车专程来到了扬州,直奔城北,出天宁门,拜谒史可法墓。那时的扬州,没有如今那样多的高楼大厦,史可法墓前的护城河那样的清澈,河边的杨柳在夏日里浓荫四射,为史可法祠堂遮挡着骄阳的炙烤,祠堂前的小路,水洗过一样干净而幽静,悠长得犹如一个充满感情的叹号。
和我想象中的扬州一样吗?和我想象中的史可法墓一样吗?我无法断定,祠堂里空无一人,只有我一个人在徜徉,冥冥中总感到祠堂深处、梅花岭下,或许有史可法的幽灵,灵光一闪,和我相会。一个你曾经从心底里敬重并向往的人,总会在某一个契机或某一个场所,和你相会的,所谓神交,就是这样的一种心灵深处的震颤吧?那一刻,我的眼泪竟然流了出来,幸亏祠堂里没有一个人。
只可惜,我来的季节不对,梅岭没有一朵梅花。
第二次来到扬州,是二十年过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未了。那是一次会议结束之后游览瘦西湖和个园,在参观个园的时候,我独自一个人悄悄地溜了出来。记忆中史可法墓应该离个园不远,果然,往北一走,很快就到了护城河边,依然是杨柳依依,依然是小路幽幽,更奇持的是,祠堂里。梅岭下,依然只有我一个人。这样更好,可以独自一人和忠烈喁喁独语,与君一别,烟波千里,来如春梦,去似朝云,正可以彼此检点一下岁月留在心上的落花浮尘。和瘦西湖的游人若织相比,这里的空旷和幽静,也许正适合史可法。如果说瘦西湖像是一个漂亮女人一头飘逸的长发,这里恰如一个男人一双坚毅的眼睛,它应该就是这样无言自威,沉静如山。它将自己眼神深邃的一瞥,留给那些想和他注视的人们。
还是没有看得到梅岭的梅花,不过,没关系,好的风景,杰出的人物。遥远的历史,永远都在想象之中。
2009年的三月初春,我第三次来到了扬州。我当然还要看史可法墓。人生如梦,流年似水,让我遗忘的人和事已经很多,但怎么可以忘记史可法呢?人生如寄,漂泊羁旅,到过的地方很多,真正能够让你难以忘怀并还想旧地重游的,并不很多。一提起扬州,便让我想起史可法,便让我有一种心头一颤的想念,充满自以为是的牵挂,仿佛扬州真的和我沾亲带故。
真的是和史可法和扬州有缘,来扬州前不久,还曾经在国家大剧院看过昆曲《桃花扇》,那里面有史可法率兵于梅花岭下“誓师”一段——史阁部言道:众位请起,听俺号令:你们三千人马,一千迎敌,一千内守。一千外巡。上阵不利,守城;守城不利,巷战;巷战不利,短接;短接不利,自尽。简洁有力的台词,视死如归的气概,演员演得热血沸腾,观众看得荡气回肠。面对清兵的入侵,史可法表现出的民族气节,让今人叹为观止,甚至汗颜。是他让扬州这座城市充满血性,荡漾着历史流淌至今响有回声的波纹涟漪。
我一直以为,扬州区别于一般的南方城市,区别于那种小桥流水,私家园林的婀娜多姿。由于地理的关系,它地处江苏的北大门,照史可法说是“江南北门的锁钥”。所以,扬州不仅具有江南一般小城女性的妩媚,同时具有江南一般小城没有的男性的雄伟。无疑,史可法为扬州注入了这样雄性的激素,壮烈的舍生取义,惨烈的扬州十日,让这座城市势趋粉黛,气吞吴越,拒绝后庭花和脂粉气,让扬州不仅只有精致的扬州炒饭、扬州灌汤包子和扬州八怪,而有了可触可摸的历史惊心动魄的那种律动的感觉,有了能够遥想当年铁马秋风可以把栏杆拍遍的想象的空间,有了可以反复吟唱的英雄诗篇的清澈韵脚。
没错,是史可法让扬州不仅是一幅画,而且是一首诗。
这次来因有朋友的陪伴和解说,看得更明白一些。飨堂前的一幅清人的抱柱联:数点梅花亡国泪,二分明月故臣心,明月梅花的比兴与对仗,古风盈袖,很是沉郁。梅花仙馆外另一幅今人的抱柱联:万年青史可法,三分明月长存,嵌入史可法的名字,互为镜像,做今古的借鉴,令人遐思。飨堂里梅花照阁前有史可法的塑像,上悬有何应钦将军题写“气壮山河”的匾额;飨堂后是史可法墓,墓前有石碑和牌坊,墓顶有草覆盖,被人们称之为“忠臣草”,据说应该是四季常青,不知为什么现在却是有些草色枯黄。
飨堂西侧有晴雪轩,轩前有扬州年龄最老的梅树,里面有史可法珍贵的遗墨,老梅古砚,花影墨迹,两相辉映,最值得一观。史可法是一官员,他的书法却是真正的书法,草书行书都有,气遏行云,韵击流水,特别是书写的内容,古韵猎猎,心事茫茫,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高贵和如今一些官员半吊子的书法不可同日而语。“涧雪压多松偃蹇,崖泉滴久石玲珑”、“琴书游戏六千里,诗酒轻狂四十年”、“斗酒纵观廿一史,炉香静对十三经”、 “忠孝立身真富贵。文章行世大神仙”、“自学古贤修静气,唯应野鹤供高情”、 “千里遇师从枕喜,一生报国托文章”……一副副对联,确实不凡,笔下风雨,心底湖海,一起兜在堂前,扑面生风。特别是他写给多尔衮的《复摄政王书》,深表春秋大义,社稷之情,一气呵成,秋高气爽,酣畅淋漓。让人会想起文天祥的那首《正气歌》。
他的遗书更是让我心动,他的第三封遗书,仅仅三句:可法死矣!前与夫人有定约,当于泉下相候也!四月十九日,可法手书。可以说是史可法44岁短促一生中最精彩的绝句。如此慷慨赴义,墨迹点点,也是血迹斑斑,几百年色泽如润,依然鲜活如昨。六天后,这一年,即1615年的4月25日,史可法殉国。次年清明前一日,他的副将,也是他的义子史德威,在他誓师和血战的梅花岭下,为他立碑立墓。但是,那只是史可法的衣冠冢,因为战后史德威找史可法的尸体时,已经找不到了。《明史》里记载:“可法死,觅其遗骸。天暑。众尸蒸变,不可辨识。”
走出晴雪轩,来到梅岭下,春梅未开,冬梅正残,断红点点。飘落枝头,有一种哀婉的气氛,袭上心头。想起全祖望的《梅花岭记》中写道的:“百年而后,予登岭上,与客述忠烈遗言,无不泪下如雨。”那是全祖望1746年写的,而今,两百六十多年过去了,谁还会登临会意而泪如雨下呢?也许,不是无端的猜想,在报纸上曾看到一则短文,说扬州一三轮车夫拉一外地客人去史可法墓,拉到门前,指指祠堂,对客人说:这人是被国民党杀死的!
朋友为打消我心头的郁结,安慰对我说:祠堂东侧桂花厅前,有紫藤和木香各一架,过些日子就会次第开花,一紫一黄,分外好看。到了秋天。祠堂大门前那两株古银杏树金黄色的落叶,会落满一地,落满祠堂的瓦顶,更是壮观。祠堂一年四季花开不断,都在怀念先烈的!朋友的话是不错的,大多数扬州人怎么会忘了史可法呢?石不可言,花能解语,如果说梅花是史可法的灵魂,满祠堂后种植的紫藤、木香、银杏、桂花、芍药、葱兰、书带草等等。都是扬州人的怀念和心情。在扬州,史可法配有这样花开花落不间断的鲜花簇拥下的魂归之处。
更何况,扬州还留下了这样特殊而别具情感的地名:史可法路、螺丝及顶(摞尸及顶的谐音,当年史可法抗敌,巷战血拼时尸体一个摞一个到城墙顶),以及史可法曾经居住过的辕门桥。扬州人把对史可法的纪念渗透进他们的生活,刻印在他们走的路上和过的日子里,那是扬州人心底里为史可法吟唱的安魂曲。
扬州,不管到什么时候,真的都是史可法的扬州。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