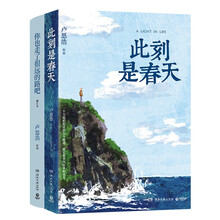北方的榆树
我是沐浴着泰山的风雨、喝着黄河的流水长大的。但在童年,我就知道了关外、口北、东三省这些名称,这是因为我有许多贫苦的父老乡亲,为找一条活路到关外,将血汗洒在了东北大地。所以,多年以来,我一直渴望着能到东北造访。
今年初夏,幸福地实现了我多年的心愿,来到了东北名城哈尔滨。这儿秀丽的江水、典雅的建筑、动人的雕塑等都给我以美好印象。当然,我也结识了许多热情的山东老乡以及他们的后代。出乎意料的是这次东北之行中那极为普通的榆树,却给了我十分深刻的印象。
据我所知,榆树主要是生长在黄河与长江流域广阔的平原上的。在我们山东农村,它是最常见的树木之一。在长江三角洲上也有榆树。上海阀门厂的古树园内,一棵榆树就已有300年以上的树龄。我没想到,在东北广阔的松辽平原上,特别是哈尔滨市内和郊区,也处处都有榆树。
下车伊始,走在大街上,就看到有许多榆树,大者干粗环抱,多数也都处于青壮年时期,一棵棵伫立路旁,以它绿云般的树冠,给夏日行人以清爽与阴凉。待接洽完工作后,有机会在市内走走,发现不仅是大街上、庭院里多有榆树,就是在一座座公园里,在可爱的松花江畔,在美丽的太阳岛上,也无处不有或高人云天,或枝干似龙,或古老苍劲,或风华正茂的榆树,给这些地方增添了富有生机的朴素美。
我来到哈尔滨,这祖国北疆的繁华城市,为什么很快就注意到了这里的榆树呢?我想,这大概也是远方遇故友,相见格外亲吧!这不仅因为榆树是我故乡最常见的树,还因为它同我故乡的人民同舟共济,一道度过了那漫长的苦难岁月。
天灾人祸,像恶魔纠缠着我的故乡。人们连年处于饥馑之中。那时,榆树便成了“救命恩人”。初春,冰雪还未融尽,饥肠辘辘的乡亲们就如大旱之望云霓,瞪着干涩、渴望的眼睛,不时地凝视着尚在残梦中的榆树,盼它早日返青。
暖风吹过,榆树便携带着几缕苦难中的喜庆味儿,结下了榆钱。白凌凌、绿微微的小榆钱,一串串挂满树枝。它是榆树的花,所以又名榆英。它既好看,又好吃,很受人们欢迎。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欧阳修,就曾写有“杯盘饧粥春风冷,池馆榆钱夜雨新”的诗句。且不说将榆钱同粗粮面和在一起,捏窝窝头,贴饼子,那松软而馋人的劲儿,就连从枝条上采一把鲜嫩的榆钱,放到嘴里吃起来也面嘟嘟、甜丝丝的,大可充饥。待榆钱成熟,变成翅果凭风飞翔,到四面八方去传宗接代的时候,椭圆、嫩绿、卵形的榆叶又萌生了。它同榆钱一样,稍加粗粮面做成干粮或榆叶粥,就是过灾年的佳品。所以,老大娘臂挎小筐,围着榆树丛采个不停;闺女、媳妇、小伙子,腰里扎一根长绳,带着筐子爬上高高的大榆树,’不顾危险去采榆叶。这是我童年十分熟悉的景象。
更可贵的,榆树可说全身是宝。除了榆钱、榆叶可吃外,就连榆树皮刮去粗老的外层,里面的嫩皮既可做糊料,又可晒干后磨成榆面,掺粗粮面烙饼、擀面条、压饴铬(类似米粉的粗糙食品),在那艰难岁月里,是一年难得吃上几顿白面的乡亲们,用以改善生活的稀罕物。至于榆树的茎干,坚实、有力,早已有“榆木梁,柳木檩”的定评。在众多的木材中,农民修盖房屋,榆木都是扛大梁的角色。就是在那“他真是个榆木疙瘩”这带有明显贬义的话语中,不也含有某种执着与坚贞吗?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