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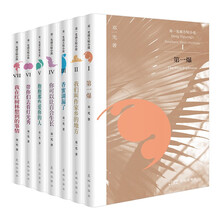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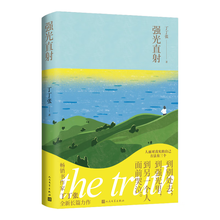




一个上海少女的自我救赎。
一场跨越种族的爱情冒险。
一段风雨飘摇的“海上”传奇。
严歌苓用一贯的女性视角,讲述了一个充满戏剧张力、令人唏嘘不已的爱情故事。故事中的上海被战火包围,不同国家、信仰、贫富的人群在这里汇集,犹太人、日本人、“上海老克拉”为了生存寄居于此。这里既有纸醉金迷的上层生活,亦有破败不堪的贫民区。“上海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不古板的地方,全世界的人想在道德上给自己放放假就来上海”,严歌苓这样写道。
男女主人公随时局沉浮,小人物们通过各种方式与命运抗争,力求在乱世中求得一片寄居地,甚至不惜毁掉对爱情的原始理解,去实现爱情。大上海,小世界——爱情与信仰,忠诚与背叛,对自我的追寻与迷失,都在其中。
逝者如斯,岁月成碑。今天的我们,又何尝不是“寄居者”。
《寄居者》的故事发生在1942年的上海,会让人忍不住将严歌苓与善于描写上海的张爱玲进行比较,然而“我怎么可能和张爱玲像呢?她的上海也不是我的上海。我的上海比较脏、臭,比较像地狱,特别是在我写的那个时期。”
为了创作《寄居者》,严歌苓读了十多本有关那个年代犹太人在上海的作品,还专门从老一代人那里了解细节,比如什么牌子的香水,什么裁缝店,什么舞厅,什么牌子的风衣大衣等等。严歌苓说:“做史料研究是小说家的日常工作。我总是在为下一部作品或者可能写的作品查资料,做采访。一部这样的小说需要的准备时间往往是几年。”
《寄居者》的故事发生在1939年抗战时期的上海,大小姐枚爱上一位从欧洲逃难而来的犹太男子。为了能让爱人去到大洋彼岸的美国,躲避纳粹对犹太人实施的“解决方案”,枚成为了另一位美国犹太青年的未婚妻,以偷取他的身份。中国人与犹太人、大上海与小世界,没有人能逃脱寄居者的命运;爱情与信仰、忠诚与背叛——在这战火纷飞、时局动荡的乱世里,三人的命运就此展开。这部作品是严歌苓在题材、写作手法和女性角色塑造上又一次新鲜成功的尝试。同时,小说延续了作者独特的自述式与视觉化的叙事风格。
接下去的一个月,始终没等来彼得。我给自己大限,在一个星期内找到另一个男人,开始新的罗曼史。新的罗曼史是否进行得下去并不重要,它的功效是使我忘掉彼得。不管是彼得负心,还是他遭遇不测,对于他的记忆让我好痛。
你还年轻,肯定记得自己犯过这种毛病:某人的缺席反而使他在你心里完美无缺。尤其对二十岁的年轻女人,缺席的恋人变得越来越好,越来越俊气,离那种搭帮过日子的未来越来越远。彼得在现实中缺席,所以在我印象里就无懈可击的美好。所以你能想象,等我真的再见到他,觉得他其实并不那么漂亮。当然,犹太大营房那场传染病,也要对他的愁苦模样和紧张神色负责。
我什么都想到了,恰恰没想到这种大宿舍生活常常发生的事:传染病。猩红热打倒了百分之四十的难民,尤其是孩子们。住在虹口的日本居民很多,他们怕传染病蔓延到大宿舍外面,就让日本军医把难民大宿舍封锁起来,划定成隔离区,有宪兵把守,不准人出入。二百多人的大宿舍(原先是仓库,漏风漏雨,却照不进阳光,家家户户只有一张桌布或床单作为墙壁,声息相闻,能隔开的只有最低程度的廉耻),不只流行一两种传染病,有时一个没有亲属的人病死了多天,都没人报告,因为其他人需要他分内的那顿晚餐。幸而天不热,病死的人在发出气味前可以让人们分享若干顿面包和汤,同时也让人们分摊了病毒。
彼得又卷又长的头发由于肮脏打成绺,沉甸甸地耷拉着,有些地方露出结着污痂的头皮。他原先的天蓝衬衫泛出一层茶色,那是汗水一再浸泡,又一再被高烧的体温烘干的缘故。尽管如此,他严谨地扣着每一颗纽扣。你该闻闻那气味!一个人没死就开始腐朽的气味!
彼得见了我就笑笑说:对不起,我不能拥抱你。
他大概喷了半瓶古龙香水,不仅无济于事,那坏气味更加丰盛。
我还是不顾一切地抱住了他。
一旦我们的身体紧贴,什么都不重要了。我苦苦等了他六个星期,等不及他去清洗掉污秽和气味,以及致命的病毒,就把嘴唇贴在他嘴上。当然,这也是痴傻恋人的一种表白:你看,我不嫌弃你;你的病毒、死亡我都想要一份儿!我的举动让莫里埃餐厅的客人们隔着门玻璃错愕,随即讥笑。
我顾不上那些。天涯沦落人的感觉特别好。
他这副模样是进不了莫里埃餐厅的。我对他说:叫部黄包车,去我那里。我会打电话给房东太太的。请房东家的娘姨到弄堂口的老虎灶去,给你叫一担开水,兑上冷水就可以洗澡了。我房间里有一个盥洗池,那个水龙头可以接冷水。
我把一张钞票塞在他手里。看他上了一部黄包车,我又想到洗澡远没有那么简单,跑上去,跟他说:不对,你听我从头讲——我床下有一个椭圆的大木盆,冷水必须用一根橡皮管从盥洗池接到盆里,再掺上从老虎灶叫来的开水。洗完第一盆,用那个铁皮桶把脏水盛进去,倒进马桶,再洗第二次。我就是这样洗澡的。房东太太人很好,就是不准房客用她的浴室。
彼得走后,我回去接着弹琴。十点以后,老板的新节目开始了:挪开了前面的几张餐桌,让半醉或全醉的各国鬼子们跳舞。这时我的弹奏更马虎,坐得腰也僵了,人也乏了,不时架起二郎腿,打个哈欠。我满脑子想的是彼得可别让开水烫了,可别傻乎乎地去端整个木澡盆倒水——我忘了一个细节,澡盆里的脏水得用那个瓢一瓢瓢舀进铁桶。自从我离开父亲的洋房,花了两个月才习惯这种麻烦百出的盥洗方法。
我一边弹琴一边还在想彼得告诉我的话。被隔离的日子他想到过自杀。后来他的父母弟妹全都病倒了,他更加看不出活下去等的是什么。大宿舍里一个年轻女人在孩子病死后自杀了。当时他没有自杀,是因为家里其他人没流露这个愿望。他不愿孤单单一人去死。
我瞥了一眼窄小的舞池里的人。弹奏变得恶狠狠的:我让你们跳!让你们醉生梦死!
……
她总能在这样一个全新的故事中,给我们一份全新的见解,一份全新的人生发现。
——陈冲评论《寄居者》
我以为中国文坛要非常认真地对待严歌苓的写作,这是汉语写作难得的精彩。她的小说艺术实在炉火纯青,那种内在节奏感控制得如此精湛。她的作品思想丰厚,她笔下的二战,写出战争暴力对人的伤害,生命经历的磨砺被她写得如此深切而又纯净。
——北京大学文学系教授陈晓明
严歌苓的作品是近年来艺术性非常讲究的作品,她叙述的魅力在于“瞬间的容量和浓度”,小说有一种扩张力,充满了嗅觉、听觉、视觉和高度的敏感。
——著名评论家雷达
与我们的一些作家经验式的写作不同,严歌苓的语言里有一种“脱口秀”,是对语言的天生的灵气。
——著名作家梁晓声
严歌苓为人物设计了基调,后来他们有了自己的生命和意志,走了自己的路,这种未知是阅读中有魅力的。
——著名评论家贺绍俊
严歌苓的文字美得像诗,在她笔下,无论是食物或水故事里的主人公都有了生命。她生动的描述和精彩的故事是非常美妙的组合。
——Boey Ping Ping
借着平易但有力的文章,严歌苓描绘了令人震惊的暴行与感官欲望。
——《旧金山纪事报》
她的小说是含情脉脉的,又是笔墨张扬的。她的小说中潜在或是隐形的一个关于自由的概念特别引人注目,那就是个人自由。
——陈凯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