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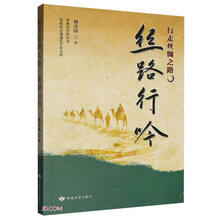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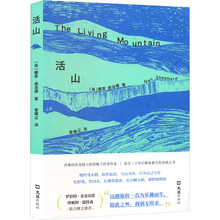




冯唐说:
→每个NB的人都要有个笃定的核,这样在宇宙间才不易被风吹散。
→世界这么多凶狠,他人心里那么多地狱,内心没有一点混蛋,如何走得下去?
→因为人是要死的,所以,一个人能支配的有效时间非常有限,所以,要非常珍惜,每一餐、每一天都不要轻易给无聊的人或事。
→我会寻找两到三个一生的朋友。和他们在一起就能放松,做不掩饰的自己,见到也没啥特别的,但是不见到就会想念。
→在树下支张桌子,摆简单的酒菜,开顺口的酒,看繁花在风里、在暮色里、在月光里动,也值了。
→一生中,除了做自己喜欢的事儿,剩下极重要的就是和相看两不厌的人待在一起。
→与其一起撮饭,不如一起流汗。也见过了风雨,俗事已经懒得分析,不如一起一边慢跑,一边咒骂彼此生活中奇葩一样摇曳的傻逼。
我们通过身体和心灵,透过接触到的事物了解自己和这个世界。
人慢慢长大,喜欢略过本质看现象,一日茶,一夜酒,一部毫不掩饰的小说,一次没有目的的见面,一群不谈正经事的朋友,用美好的器物消磨必定留不住的时间。所谓本质一直就在那里,本一不二。
情调、趣味、审美、态度……总有什么让你与众不同,成为自己。
“我想,再晚一点,我会停止用手表。我会老到有一天,不需要手表告诉我,时间是如何自己消失,也不需要靠高档手表告诉周围人类我的品味、格调、富裕程度和牛逼等级。我会根据四季里光线的变化大致推断现在是几点了,根据肠胃的叫声决定是否该去街口的小馆儿了。”
《在宇宙间不易被风吹散》有一点美学、有一丝禅意、有一抹世俗却更有一份浓情,料已调好,等你来品。
房子
我的理想小房子
老舍先生快到四十岁的时候,在《论语》第一百期发了一篇文章,讲他的理想家庭。家庭太复杂,涉及太多硬件和软件、生理和心理、现在和未来,一篇文章不容易讲透。这篇文章,我只想聊聊我理想的房子。组个理想家庭的重要前提之一,是有个理想的房子。
多数人类包括不少禽兽都有筑巢的冲动,尽管生没带来一物、死带不走一物,生死之间,总想有块自己私有的窝儿。人都有个妈,我也有一个。我妈是纯种蒙古人,我的理解,蒙古人居无定所,骑上马就带着全部家当走,下了马放下家当,就是家。但是我妈到了城市,很快就开始念叨,她想要有个大房子,我说和蒙古习俗不符啊,她说她也不知道,但是她就是想要。我想,这些说不清楚但是一定想要的,往往根深蒂固地编码在人类基因里。
我心目中理想的房子要有十个要素。
第一,房间面积要小。
一卧,最多两卧。多出来的一个卧房当客房或者等小孩儿长到青春期为了自摸方便坚持要求自己睡或者偶尔夫妻吵架需要分房睡。每个卧房不超过十平方米——乾隆帝的卧房也不过十来平方米,平常人王气更弱,不僭越。卧室里最好有大些的衣橱,常穿的衣服可以挂起来,旅行箱也可以藏到视线之外。
一厨。如今的女性喜欢平等,做完饭不洗碗,所以要有洗碗机;要有烤箱,没女人做饭的时候可以烤鸡翅和羊肉。
一起居室。一桌,六到十把椅子,吃饭、喝茶、看书、写作都有地方了。最好有个真壁炉,天冷的时候点起一把火,心里就踏实了。最好有个宽大的单人真皮沙发,中饭之后,瘫在里面看书,被书困倒,被夕阳晒醒,午睡前的书都记到脑子里了。
这样算下来,一百平方米足够了。如果嫌小,想想,多出来的面积和房间你一年也去不了几次;想想,面积小,好打扫。如果还嫌小,想想减东西,一年以上没碰过的东西,理论上讲都可以扔了。不用参“断舍离”,只参一个“扔”字,就好。
第二,要有个大点儿的院子。
有树。最好是果树或者花树或者又开花又结果。自家的果子长得再难看也甜;哪怕花期再短、平时打理再烦,每年花树开花的那几天,在树下支张桌子,摆简单的酒菜,开顺口的酒,看繁花在风里、在暮色里、在月光里动,也值了。
有禽兽。大大小小的鸟用不同方言叫,松鼠、野猫、鹿不定时地来看看你在读什么书,知道你没有杀心,见你靠近也不躲避,稍稍侧身,让你走过去而已。
第三,要有好天气。不要太干燥,不要太潮湿,冬天不要太长,夏天早晚不要太热。
第四,要有景色。尽管你天天看,但是景色依旧重要,或许也正是因为你会天天看到。如果你的眼睛足够尖,你会发现,尽管你天天看,景色每天都不一样。上天下地,背山面海,每天看看不一样的云,想想昨晚的梦,和自己聊一会儿天,日子容易丰盛起来。
第五,附近要有公园。越近越好,走路三五分钟能到最好。如果开车才能到,不能算房子附近有公园。公园不用很大,简单的草坪,一圈二三百米,能跑步就好。人过四十,一身不再是使不完的力气,反而有总拉不开的筋骨,跑步是解药。每天跑跑,三五千米,汗出透,整个人都好了。
第六,附近要有大学。最好走路能到,最好是所像样的好大学。有大学就有图书馆,有看不完的书可以蹭看。有大学就有苍蝇馆儿,而且开得晚,一年到头都有便宜的好吃的。有大学就有教授,要张课程表,去蹭大课听。有大学就有女生,花树的花落了,还可以在校园里看女生。
第七,附近要有足够好的生活设施。最好能有几家好餐馆,开了几十年,食材新鲜,厨师踏实,菜好到你常吃不厌,懒得做饭了,就能不做。最好能有几家好咖啡馆,豆子现磨,闻香进门,早餐和糕点都让人惦念。最好能有一两家走路能到的独立书店,时常能翻翻新书,每次能买到一两本过去一直想读但是没机会读的旧书。小学和中学都在走路范围内,否则接送小孩儿上下学就会消耗掉你不多的自由时间。多数病都是年纪大了之后得的,老了之后,医院是必需的。医院最好走路能到,不必雕梁画栋,等候时间不长就好,医生能不乱开药、能多和你解释病情、能体会到你的痛苦就好。
第八,城市要有历史。最好百年以上,连续不断。有很多古董店,家具、瓷器、餐具,买了就用在日常的生活里,一年下来,在古董店买的东西比网购还多。有不少博物馆,一些古迹,偶尔逛逛,觉得祖先并不遥远。
第九,一个小时车程之内有国际机场。人偶尔还是要出去走走,度假、会友、凑热闹。
第十,附近要有朋友。最好有很多朋友。朋友们就散住在附近几个街区,不用提前约,菜香升起时,几个电话就能聚起几个人,酒量不同,酒品接近,术业不同,三观接近。菜一般,就多喝点酒;酒不好,就再多喝点,很快就能高兴起来。
一生中,除了做自己喜欢的事儿,剩下最重要的就是和相看两不厌的人待在一起。从这个角度看,这第十点是最重要的一点。所以如果看上一处房子,买了下来,让房子变得更理想的捷径是鼓动好朋友也买在附近,共我山头住。
当然,这十点之前,有些更基本的要求:空气是干净的,水是能喝的,食品是能吃的,无论什么时候在街上走是安全的,没有什么组织是能不依法就把你从你的房子里带走的。有时候,这些要求看上去是如此基本,但是有时候,又似乎是那么遥不可及。
老舍先生写这篇《我的理想家庭》是1936年,他在文章结尾的时候说:“这个家庭顶好是在北平,其次是成都或青岛,至坏也得在苏州。无论怎样吧,反正必须在中国,因为中国是顶文明顶平安的国家;理想的家庭必在理想的国内也。”如果老舍先生还健在,他在哪里,北平就在哪里,哪里就是北平。
我理解他在那时的无奈,佩服他在那时的乐观。希望我们都有他的乐观,希望一切无奈落去,希望一切理想成真。
大学教育
我在协和学到的十件事
三十岁后,什么时候退休,是个大问题。回答这个问题的方式有很多种。比如,国家规定,现行是男性六十岁退休、女性五十五岁退休,听说因为社会老龄化日趋严重,有关部门要无耻地延长退休年限,男性六十五岁、女性六十岁。再比如,挣到够花,马上回家。当然,现在够花是否将来够花,需要充分考虑通货膨胀和欲望膨胀。
我还有一种针对自己的算法:我的工作年限至少要等同我的上学年限,否则觉得愧对社会,内心不安。我小学、中学义务教育十二年,协和医科大学义务教育八年,美国MBA教育两年,也是拿了美国提供的奖学金。
2014年春夏之交,我受协和邀请,去协和医大近百年历史的小礼堂,给小我二十岁的师弟师妹讲协和传统。我使劲儿想,协和八年大学教育,我学到了什么。我觉得我在协和学到了十件东西。
第一,系统的关于天、地、人的知识。
在北大上医学预科,学了六门化学,和北大生物系生物化学专业学得一样多。学了两门动物学,无脊椎动物学和有脊椎动物学,第一次知道了鲍鱼的学名叫作石决明,石头、明快、决断。学了一门被子植物学。还学了各种和医学似乎毫不相关的东西,包括微积分。在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所学基础医学,当时学了大体解剖、神经解剖、病理、药理等,从大体到组织到基因,从宏观到微观都过了一遍。在协和医院学临床,内、外、妇、儿、神都过了一遍。
去北大之前,我们还去了信阳陆军学院军训一年。当时学了如何带领一个十人左右的班级、如何攻占一个山头、如何利用一个墙角射击、如何使用三种枪支等。军校期间,我看了十一本英文小说,其中一本是劳伦斯的Lady Chatterley’s Lover。
现在回想起军训、北大、基础、临床,我常常问一个问题:学这些东西有?用啊?第一点用途,在大尺度上了解人类,了解我们人类并不孤单,其实我们跟鱼、植物甚至草履虫有很多相近的地方,人或如草木,人可以甚至应该偶尔禽兽。第二点用途,所有学过的知识,哪怕基本都忘了,如果需要,我们知道去哪里找。因为我们学过,我们知道这些知识存在,我们不容易狭隘,不狭隘往往意味着不傻逼。第三点用途,是知道不一定所有东西都需要有用。比如当时学“植物”,我还记得汪劲武教授带着我们上蹿下跳,在燕园里面看所有的植物物种,后来我读过一句诗,“在一个春天的早上,第一件美好的事是,一朵小花告诉我它的名字”。
第二,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求真务实的态度。
首先要承认自己的无知和无能。学西医内科的时候,老师反复强调,80%的病不用管它,自然会好,nature cures。这反而映衬了我们对很多疾病并不彻底知道成因,并不确定什么治疗方法如何有效,比如SARS,到现在也不清楚为什么会出现、为什么消失,也不确知明年会不会再次出现。
其次,面对这么多的未知,我们还是要给病人相对笃定的建议。我们要给病人列出几个可选方案,要跟病人讲清楚不同方案的优劣,要给出我们推荐的优选方案。
再次,不作假。不能说假话,不能做假数据。我一直坚信,如果没有真的存在,所谓的善只能是伪善,所谓的美也只能是妄美。我记得在协和教过这句话,说哪怕再难听的真话,也比假话强。
最后,要有天然的谦虚。因为你不知道、你做不到的太多了,你要永远保持谦和。导师郎景和讲过一个故事,有位妇科大夫曾对他说:“郎大夫,我做过很多妇科手术,我从来没有下不来台,没有一个病人死在我的手术台上。”郎大夫停了停,说:“尽管有些残忍,我还是要告诉你人生的真相。人生的真相是,你手术做得还不够多。”
第三,以苦为乐的精神。
学医很苦,有位协和老教授说,原来的协和校训是“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后来新中国成立了,新社会了,校训只剩前半句,“吃得苦中苦”。我做医学生的时候,那些大我三四十岁的老教授,早上七点之前,穿戴整齐站在病房里查房,我再贪酒、再好睡,都不好意思七点之后才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协和门诊夏天没空调,教授们也是西装、领带、衬衫,从早上八点到下午三点,不吃饭,几乎不上厕所、不喝水,汗从脖子上流下来,流进衬衫。当时的协和不熄灯,教室在七、八楼,住宿在六楼,食堂在地下室,晚饭四点半开,我从五点多开始看书,一直到深夜。从那时候起到四十多岁的现在,我没有在晚上十二点之前睡过。
第四,快速学习一切陌生学科的能力。
最开始学神经解剖的时候,协和内科主任以过来人的身份去给我们鼓劲儿,我问,颅底十个大孔,您还记得哪个是哪个吗?哪个都有哪根神经、哪根血管穿过吗?我估计当时那个内科主任心里非常恨我。他当时的回答是:我虽然忘记了一切,但是我学习过,我清楚地知道怎么学习。
第五,热爱实操。
实操就是落实到底,把事儿办了。什么是临床?协和老教授讲,临床就是要临、床,就是医生要走到病人床边去,视、触、扣、听。书本永远是起点而已,永远难免苍白无力;一手资料永远、远远大于二手资料。
第六,追求第一。
协和在东单三条方圆这几十亩地,每年几十个毕业生,最初的两百多床位,至今的近百年历史,就是一部中国现代医学史。没有协和,就没有中国现代医学。如果问协和门口的病人:为什么非要来协和?病人常常会说:来协和就死心了。病人和死亡之间,协和是最后一关和唯一一关,所以这一关必须是最好的、最牢固的。这是荣耀,也是责任和压力。
第七,项目管理。
所谓项目管理,就是在有限的时间、人力、物力下,把事情做成。协和八年,尽管功课很忙,又忍不住看小说,我还是做了北大生物系的学生会副主席和协和的学生会主席。寒暑假基本没闲着,看小说之外,都用来完成一个个“项目”。比如,在北大的第一个暑假,同四个同学一起,和植物学汪劲武教授去四川和甘肃,寻找一种非常少见的山竹。我完全忘了那种山竹的重要性在哪儿,似乎找到之后可以改写被子植物史或者呼唤神龙。我记得的是,师徒五人,漫游二十天,每天住旅店,每顿有荤有素,最后在有限的预算之内,找到了那种山竹。
第八,与人相处,与人分利。
当时协和,一间宿舍,十平方米,放三张上下铺的床,住六个人。当时协和,一届一个班,一个班三十人,一个班只有一个班花。这种环境,教给我如何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与人相处,与人分利。
第九,抓紧时间恋爱。
大学期间,二十多岁,你会觉得时间永远静止,人永远不老。但是,这是幻觉。这段时间过得再慢,也会过去。男生小腹再平坦,也会渐渐隆起或者松弛,女生面庞再粉白细嫩,也会渐渐残败。大学的时候,班上的妇女是很美好的。奉劝各位男生,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协和往西不远,有东华门、筒子河、角楼、午门,傍晚牵了手走走,很好的清风朗月,从来不用一钱买。协和往西不远,有三联书店可以乱翻书;往北不远,有中国书店可以乱翻书。往任意方向,都有大量的马路牙子可以坐着喝雪花啤酒,乱看姑娘。这些,都不太费钱。
第十,人都是要死的。
协和八年,集中见了生老病死,深刻意识到:人终有一死。这似乎是句废话,但是,很少人在盛年认识到这点,更少人能够基于这个认识构建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因为人是要死的,所以,一个人能支配的有效时间非常有限,所以,要非常珍惜,每一餐、每一天都不要轻易给无聊的人或事。因为人是要死的,所以,人不要买自己用不上的房子,不必挣自己花不了的钱。像协和很多老教授一样,早上在医院食堂吃碗馄饨,上午救救人,下午泡泡图书馆,也很好,甚至更好。因为人是要死的,所以要常常叨念冯唐说的九字箴言:不着急,不害怕,不要脸。
目录
序分 用美器消磨时间
一日茶,一夜酒,一部毫不掩饰的小说,一次没有目的的见面,一群不谈正经事的朋友,用美好的器物消磨必定留不住的时间。所谓本质一直就在那里,本一不二。
第一品 眼·耳之器
相机/抓到妇女的性感和诗意
街上像草木一样美好的姑娘,忽然无意识地开放,你忽然看到了,忽然想到了些什么,想说点什么。
春宫/纯美而丰腴的黄光
为什么人就不能像看待一只绣花鞋一样看待一只女阴?为什么人就不能像看待一匹马一样看待一只阴茎?
AV/像极初恋,像极女神
你们七〇后男生是怎么回事儿?怎么总是不主动?
纸书/几床悍妇几墙书
借着简单文字,魂魄渐渐抽离。周围草木一寸一尺地消失,时间没有方向感,四处流淌。
附录一:Kindle:硬硬的,一直在
开始目睹器物被电子取代的过程。
附录二:2013年的十本书
所有春天的所有早上,第一件幸福的事儿,是一朵野花告诉我它的名字。
旧书店/笃定的核
每个伟大的街区都要有家旧书店
人籁/耳朵听了会怀孕
和其他领域一样,诗歌似乎也有个若隐若现的江湖,二三十个名字总在那里低空飞行,嗡嗡作响,他们完全忽略我的诗歌已经开始被时间写在楼盘上、大地上、人民心海的水波上。
第二品 鼻?舌之器
鼻毛剪/鼻毛丰满,飘飘进京
鼻毛也不是全无是处。北京的空气越来越差,戴口罩,特别是N95之类的重型口罩,有装逼和贪生怕死之嫌。
天目盏/为什么曜变都在日本
从一只盏里能看到整个宇宙的真相,这真相美得让人流泪。
日本铁壶/我和伟大茶人之间的区别
的确有好茶,骨秀肉俊,十几泡、二十几泡之后,还是迷死人不偿命,就像姑娘和姑娘还是有区别。
茉莉花茶/茶缸在右手一臂之遥
因为喝惯了茉莉花茶,青春期刚开始的时候,刚刚体会男女,喜欢的女生也都是茉莉花一样,爱穿青绿裙子、白汗衫,适应北方,不爱热闹,不停闷骚。
火炉/小时候的北京冬天
每到冷天,每到夜晚,每到想喝口小酒,我每每闭着眼听到老爸像老猫一样爬起来,去照看那早已经不存在了的炉火。
酒庄/后半生靠谱与不靠谱的事儿
一辈子都有和朋友喝酒的地儿了,而且是很美好很僻静的地儿。有山,有水,有树,有竹,有天,有月,有四季,有葡萄,有果实和花朵。
第三品 身之器
玉/君子无故,玉不去身
古龙小说里……这些美丽妇人干坏事都是为了能得到美丽珠宝。我就不懂了,为什么啊?为什么能为珠宝干出这么多坏事啊?
机械手表/不要降低公司的品位和格调
一个女领导终于忍不住对我说,这样不好,每次我看手机,她都觉得我品位和格调很低,因为她和我一个公司,我看手机连带着她和公司的品位与格调都很低。
风衣/男人四十少说话
男人过了四十,千万少说些话,拉长脸,闭紧嘴,买件立领风衣,浓个眉大个眼,一直走,不要往两边看,还能再混几十年。
房子/我的理想小房子
一生中,除了做自己喜欢的事儿,剩下最重要的就是和相看两不厌的人待在一起。
跑步/让自己和身体尽人力
跑步能让脑子暂时停止思考,脑子的闪存清空,绝大多数的纠结抹平。如果还放不下,就再跑五公里。放下之后再拿起,心神中会多出很多新意。
附录:北京的三条散步径
春天,北京刚绿之后,杨花滚地之前,屁股再沉,不出屋子走走也说不过去。
中医/我的先人不是来自中药星球
在现世,比较稳妥的建议是:西医定义未病时,用中医;西医定义绝症时,用中医。
第四品 意之器
大学教育/我在协和学到的十件事
所有学过的知识,哪怕基本都忘了,如果需要,我们知道去哪里找。因为我们学过,我们知道这些知识存在,我们不容易狭隘,不狭隘往往意味着不傻逼。
财富观/富二代的自我修养
如果我只能追求一种名牌,我一定追求教育上的名牌:上最好的大学,读最有名的名著。
名声/从高冷到贱萌
师弟说:“你不该这样娱乐化!那个真人秀主持人的事儿就完全不该做!我们不忍这么看着你由高冷堕落到贱萌!”
自恋/实事求是地自恋,让别人闹心去吧
能做到实事求是地自恋其实是自信和自尊。任何领域做到最好之后,人只能相信自己的判断,只能自恋。
随身佛/和所有美好的未知一起存在
那一瞬间,我完全看不到她的脸,但是我深深感到,她是高级太多的物种,创造她的不是她爸妈而是一种强大而神秘的力量,如果没有外星人,那么或许有神。
唐卡/简单下去,再简单下去
人微如草芥,但是不妨碍心细如丝,志坚如屌。平时如丝,让世界基本过得去;不平时如屌,让世界不能永远过得去。
第五品 阿赖耶之器
圆寂/老天的程序编码
那种控制,说到底是老天安排好的控制,没有哪个细胞能自己控制自己的生死。程序之下,众细胞渺小。
诗/作为无用之器的三种用途
那些不朽的文人,被记住的不是长篇小说、短篇小说、杂文,而是“床前明月光”“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春林渐盛,春水初生,春风十里,不如你”。
赞曰 如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