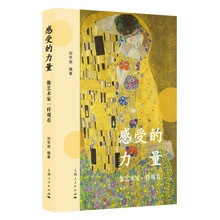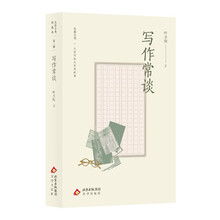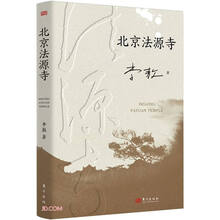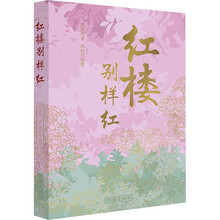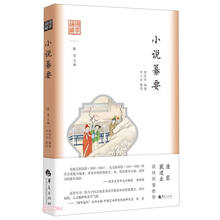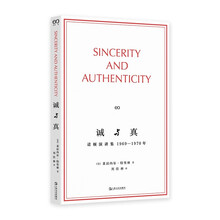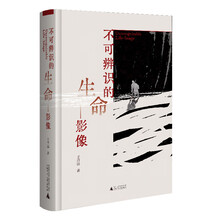二“过渡”的政治诗学与文化面孔
“过渡期”作为一个政治概念正式出现在中葡两国关系的表述中,始于《中葡联合声明》(1987年3月26日草签,1988年1月15日正式生效);但在社会政治、文化、意识、观念等层面,“过渡”早已开始。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不论是文化界人±还是澳门本地居民,都已意识到澳门历史将翻开新的一页,因此,文化、文学意义上的“过渡”显然不止1988~1999年这段时间。过渡期的文学创作表现为两个方面的基本内容:一是本土身份认同,即“澳门性”;二是民族身份认同,即“中国性”。后者是澳门过渡期政治诗学的核心,“澳门性”植基于“中国性”之中。
与香港相比,澳门文学的本土自觉起步较晚。这与澳门在周边的历史变迁中成为移民中转站的地缘政治处境相关。澳门新生代诗人懿灵将澳门定位为一个“流动岛”:“澳门从不留人。因为澳门有出入境自由,也因此而流失人才。澳门人是流离的,这里多的是过客;澳门政治是流离的,一时偏左一时又偏右;而整个岛是流动的,流动的岛不但向外流,还有以内圆心为目标的不断向内倒流的特性。”①与之相应,澳门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没有形成完整的文学平台,如纯文学刊物、纯文学媒体、纯文学出版机制等。澳门文学的本土意识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社会经济大发展时期方始萌芽,经创作与批评的双向互动,逐渐自觉。
澳门的民族意识在诗学领域的折射,与香港等其他殖民地既同又异。其共性在于对政治一民族身份认同的焦虑,虽然认同诉求到“过渡期”已不是问题,但百年以来“事实属于”西方“宗主国”的历史遭际已深植于澳门的集体记忆,一旦遇到突破口便可能爆发;特殊性在于它是以更温和、更折中、更少对抗性和二元对立性的方式生成的,关于这一点,澳门文学叙事可资佐证。澳门重要的华文媒体《澳门日报》从创刊起即肩负神圣的文化使命,在“中国性”问题上一直政治立场鲜明,50~60年代甚至受内地影响而出现过“红色”倾向②。70年代以后延续到过渡期,由于华人与葡萄牙当局矛盾的缓和,“红色”倾向消失了,作品更加贴近现实、更加生活化,但其中的地域意识、民族意识并没有改变。例如那些生活类专栏散文,它们或描绘澳门的风物人情,或寄托故乡、故国之思,诸如《十六的月亮》(沈尚青)、《澳门新八景随想》(徐敏)、《澳门的秋天红叶》(张裕),这类作品几乎统领报端,单从题目即已见其旨趣。“过渡期”的历史契机唤起澳门对“中国性”的强调。缘源指出,“随着澳门回归祖国日近,作家们自觉地赋予作品爱澳门爱祖国的文学主题”①,当然也包括被这一特殊历史契机所重新唤起的东方身份焦虑。如余行心的《丝士咖啡室》、鲁茂的《白狼》,反映出华人、土生葡人与葡人三大族群的冲突,其中有着格式化了的殖民与反殖民、西方与东方的权力关系模式。江思扬写于1992年的新诗《向晚的感觉》之(二),民族和历史意识更为直白:“亚美打庐大马路奏着四十年代的慢板/它西端的大钟仍指着一九四八年十二点/要焦急的行人驻足、回忆/西洋水手的趾高气扬。”②在这里,西方被反定义为与自身对立的“他者”,是东方殖民地普遍出现过的表达身份焦虑的政治诗学。
以西方为他者的身份焦虑并非过渡期澳门政治诗学的全部基调。无论创作还是批评领域都出现了“温和性”,曾有学者就一本澳门文学评论集指出其整体倾向:“《濠海丛刊》之《澳门文学评论选》上篇收录了21篇文章,全部是澳门作家论澳门文学特点及发展方向之作。这些文章所指出的澳门文学的特点主要有三,其一是采用现实主义表现手法为主,现代、后现代派的作品很少;其二是作品主题大多基于作者个人生活体会和遐想,具有深厚社会体验和广阔历史背景的很少。其三是抒情性的作品多,批判性的作品少。”③不仅如此,20世纪70年代后出现的散文,地域意识、民族意识多表现为描绘澳门奇丽的景色、宁静的生活、温暖的人情等美好的一面,或者寄托对故国、故乡、故人之怀思,“写事抒怀”“怡情益智”的倾向较为突出。
……
展开